第五节 自然哲学作为新神话的质料
与此衔接,笔者在这里讨论谢林关于自然哲学与新的神话的关系的那些陈述,它们是谢林自己在接续对近代艺术规定的建构时直接引入的。这个问题是谢林研究长期未做深入讨论,反而搁置而未做处理的。笔者认为,这些陈述相当典型地反映出谢林与早期浪漫派的作为艺术理论和诗艺实践的新神话纲要的激烈理论商榷。不过,笔者以此并不能深入到对谢林本人的浪漫派吸收史的研究那里,也不打算直接处理F.施莱格尔的《关于神话的谈话》与谢林的PdK中神话论题之间的特定亲缘性。[23]笔者在这里首先仅限于追踪谢林对自然哲学与新神话的关系从概念方面作出的澄清工作,这是哲学家面对浪漫派的艺术理论从唯理念主义立场出发重点宣布的。笔者还要强调,这个澄清工作的前提是谢林按照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提出的那整个的同一性哲学和存在论神话学的构想。
谢林提到“自然哲学作为新神话的质料”这个话题,仅在PdK和System 1804两个文本当中,并且在两文本的语境中,其目的都是直接批评近代的“诗之匮乏”。在此我们必须提到,在这个问题上,谢林与他的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和艺术家们一样,对近代持有一种批判的观点。也就是说,在艺术发展和艺术生存这方面,把近代直接指为古代的对立面;就此而言,在文化的古今对立中,近代处于不利的一方。这是因为艺术在近代面对着生存困境,并且这种情况根本来自时代的进程本身。所以“诗之匮乏”这样的问题必须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来处理,这是克服分裂,重新赢得整体性的重要一步。
必须注意,在PdK的整个总体关联中,着眼于艺术创造活动的人类自由问题,仅仅是内在地包含在内而并没有直接成为讨论题目,因为PdK必须坚持同一性哲学的前提条件即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性,以此在这里不会提出创作自由的问题。在PdK这里,谢林仅在研究近代诗歌的“普遍性”时顺带讨论了人类自由(SW.IV,S.444)。如果说自由与必然的无差别曾实现在希腊神话和古典艺术那里,也即同时通过主体那里的自由的胜利和作为客观必然性的必然性的胜利,它们两者同时以战胜和被战胜的姿态显现在完全的“无差别”中(SW.V,S.693),那么谢林还提示我们,对现代来说,这样的进程仅能发生在审美的领域中。在分析牵涉“神话质料”的古代与近代的诗歌对立时,谢林允许人类在构形方面有其自由,同时又提醒我们,在近代这里,这种自由即便在艺术创造的形式下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他认为,近代意识不能有新神话,只能有一种“局部的神话”(SW.VI,S.572);因为一种近代艺术,其出发点乃是个体,这完全不同于古代。也就是说,在近代精神这里不曾出现类族与个体的直接融汇。
“新神话”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构成存在论神话学构想的一个重点。迄今为止的谢林研究却并不重视它,更没有充分地处理它。笔者想就这个问题说几点:首先,谢林对这个关系之“审美—哲学史”的钩沉工作,没有其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借助于斯宾诺莎的实体性形而上学,对古老的“哲学与诗之争”做出的一个现代方式的解决。谢林是为揭示这个关系提出了自然哲学构成新神话的质料这一命题。这个命题与早期浪漫派关于艺术的自然哲学构想具有亲缘关系。在《关于神话的谈话》中的那些纲要式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出F.施莱格尔的思想有计划地指向一种由唯理念主义所规定的自然理论,要求新神话与神秘物理学的一种联结,后者诞生于德国唯理念主义的母腹,现代诗歌应当与德国唯理念主义有一种联系,如古代的诗歌与希腊神话之间的那种关系。[24]而在Systemprogramm那里,“更高的物理学”之作为新神话质料的这个断定还完全没有出现。在那里,新神话的思想主要是与一种关于“感性的宗教”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自然哲学——那里称为“更高的物理学”的,作为一个柏拉图—新柏拉图意义上的诸理念体系的第一部分——的任务是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对道德的生物,一个整个世界的存在是必然的?
早期浪漫派对艺术的自然哲学构想可以回溯到斯宾诺莎主义的赫尔德阐释那里。而赫尔德阐释斯宾诺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将莱布尼兹的神正论补充进去,他还在存在与认识之间引进一些假定的内在力量,作为一种第三者;而这样的区分在斯宾诺莎那里则被同一性命题扬弃了。[25]对赫尔德来说,各种内在的力都是对神的至善、对至高无上的力量和至高无上的智慧的自然表述。每一种可以体验的东西都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神性秩序的隐秘的标志。在这种上下文中,艺术是神的至高无上的智慧的标志。为此要求对非显现的诸事物的神话式洞观。在他这里,模仿自然的公设变成了艺术对创造性自然的导向的要求。
F.施莱格尔也在斯宾诺莎的实体论那里为自然的神秘秩序找到了形而上学的解释。他在斯宾诺莎主义中看到诗与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对神秘主义的每一种个体形式”都作为“一般根据和支持”适用。对斯宾诺莎思想的这种狂热,把一切事物置于永恒的视点下去看,F.施莱格尔认为即是原初的神话体验,这种体验使斯宾诺莎的作品成为对“怀抱在这种想象和爱的升华中的大自然的一种象形文字式的表述”,我们可以将它与“每一种美好神话”相提并论。[26]不过,在F.施莱格尔谈到借助于一种斯宾诺莎主义和时代的物理学重新复活“伟大的古代的美好诸形态”的时候,他指的并不是将“理性地思考着的理性的诸法则”引进和贯彻到新的神话中,这些法则将由于“想象那美妙的混乱”而被诗扬弃掉,因为诗能够把我们重新“植入在人类天性那原初的浑沌中”。正是在“作为关于整体的神秘科学”的物理学那里,F.施莱格尔找到了“诗的诸原始源泉”[27]。想象与爱是他于其中看见神话质料的两个点,他在这两个点上都诉诸斯宾诺莎主义的一般神秘特征。不过他并未吸收斯宾诺莎的同一性命题,相反是赋予艺术以那种功能:使无限者可以在有限者那里得以认识,使永恒者可以在时间中得到体验。
这种对真理与诗之间的直接联系的确信和对一切理性的诗性运作方式的浪漫派式的确信,来自于赫尔德的思想财产。[28]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最内在的神秘主义,都是诗所固有的东西之一种。F.施莱格尔诉诸情感,以对抗费希特的“理智直观”。而谢林的自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是斯宾诺莎的同一性命题,但他同时又在与费希特的唯理念主义的关联中,坚持费希特的“理智直观”。
其次,谢林的自然哲学,不仅提供处理自然的诸实在级次的自然哲学特殊部分,而且首先是关于自然的绝对认识——关于自然的学说、关于“万有”的学说和关于自然中的永恒诞生活动的学说。[29]然而对于近代意识,不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一自然哲学固有的意义,都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对这种在其近代来源中的意识来说,理解自然哲学的概念及其知识方式所要求的那种立场,一种指向同一性位置的立场,长久以来即已失落。现在谢林试图通过一种自然形而上学重新建立它,因为这一位置的自明性必须借助于思辨的哲学得到重新阐发。
最后,谢林一般地肯定自然哲学作为近代诗性的艺术创造活动和作为新神话质料的可能性。不过,他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实在有必要立即澄清一些严重的理论混淆。所有这类混淆都建立在一种狭隘化的反思立场上,它们都涉及近代的一般分裂态度。在这里也涉及阐发关于“整体的理念”这个问题。这些阐述基本上给定在同一性哲学的“万有论”和“诸理念论”那里。艺术的“质料”必须是“有机自然”也即神话。艺术必须取材于最高的有机自然,将它作为自己的“质料”;而这种“质料”总是直接地涉及“万有”即存在整体的自我展开的具体形式。
谢林持一种类似于早期浪漫派的观点,认为我们“必然要在更高的思辨物理学那里寻找一种未来神话和象征系统的可能性”(SW.V,S.449)。但他在阐述这个观点的时候一直坚持表明自己与早期浪漫派的区别甚至分裂,此一点不可不辨。我们在分析文本时能够看到,谢林通过详述“思辨物理学中存在未来神话的质料”这观点的三个重点,明确地给出了他与浪漫派的观点差异,这就是关于“更高的物理学”作为新神话的质料的问题(Ibid.,S.447),关于作为“公开的知识”(das offenbare Erkenntnis)的自然哲学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的衔接以及关于(存在的)质料的独创式运用和诗意构成的问题。
在这里,在考察艺术领域,考察宇宙最高存在级次上的创造活动时,谢林引进了“更高的物理学”的概念(Ibid.,S.449),以明白地昭示新神话的质料。这“更高的物理学”在谢林那里是自然哲学本身,但它在此不是直接作为绝对唯理念主义或作为“万有论”即一般自然形而上学而出现,不如说它在这里是同一性哲学体系内部的自然哲学,也即这一哲学的纯粹理论部分。它的任务在于,使“意识的主—客体”从“纯粹的主—客体”那里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它唯一指向自然的自在东西和理智。关于同一性哲学的这一部分与实践哲学部分的关系,谢林曾在同期的一篇文献中给出详细的论述。[30]简单说来,这个关系可以概括为同一性哲学的实在部分与其观念部分的关系,不过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反思所理解的那种“鸿沟”,相反,在同一哲学的这两个部分里存在着本质上的连续性:观念的部分具有一实在论的基础,而且本身恰从这基础发展而来(SW.IV,S.89)。当谢林将这一哲学的纯粹理论部分称为思辨物理学时,还特别提示了它的基础,那种对动态过程的理智认识,这种认识反过来又建立在有机自然学说的基础上。
谢林以此突出了“思辨物理学”在哲学体系内的先在性。哲学的理性是凭借更高物理学从“纯粹的主—客体”开始考察,它在这种考察那里永远不会脱离“观念—实在的东西”的同一性。这就是谢林宣称在作为“更高的物理学”的自然哲学那里必可找到新神话的一种“质料”的原因:仅在这个领域必然能看见那种“主—客体东西”的自我建构活动。这“纯粹的主—客体”就是自然本身,只不过,它在这里是在其最初级次上的自然。在这个“思辨物理学”看来,自然即是那个做建构活动的主体,它使观念活动的所有创造产物和级次都通过它的自我建构活动产生出来。在这种关系中,谢林谈到自然哲学特有的直观方向乃是“现代教化”直观的“相关物”(SW.V,S.447)。基督教的直观方向是从有限者朝向无限者,它以此扬弃了所有的象征性直观,反过来将持续地为理性要求一种对无限者的实在直观。而“思辨物理学”相反,它是对在有限者那里的无限者的“理智直观”,确切说来它“以一种普遍有效和科学客观的方式”做“理智直观”(Ibid.,S.448)。理性在自然哲学建构那里追随的不仅是自然现象的绝对自我创生活动,它自己就是与“质料”联系在一起的“主—客体”的这场生成活动,而且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指向自然当中的非客观东西,在自然的领域中“最终返回到一种创造活动和再创造活动上”,如谢林在解说思辨物理学的自然解释方式时强调的。[31]所以,唯有自然哲学的实在论解释方式可以胜任帮助现代教化的象征努力的这个任务,这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内在直观因其客观性匮乏无法完成的(Ibid.,S.448,447)。
谢林关于思辨哲学与基督教的必然综合这个思想,乃是按照宇宙“一般类型”作出的一种展开(Ibid.,S.448)。这类型即是宇宙的“统一—万有”,按照这“统一—万有”出现了所有的事物,而且是作为安置在秩序中的,作为整体的环节。谢林在这里一再强调,基督教“仅表现为向新世界的过渡,仅表现为新世界的因素,仿佛表现其一个方面”,它的“整合方面”必然把它作为对立面的统一体,这统一体是“对在有限者那里的无限者的直观活动”(Ibid.)。作为思辨物理学的自然哲学在宗教那里把自己构成为一种新的客观直观的源泉,借助于其认识活动的固有东西。因这里发生着无限者的自我构形,借助于原理在这里重新出现在无限与有限的绝对统一当中这种情况——原理证明自己是那种东西,直接通过自己即可以象征地表述神与自然的同一性。
谢林以对新神话质料的处理去思考基督教的完成,以此将基督教揭示为一种“过渡”。从神话学角度看,这种完成会是自然与历史的一种绝对的同一。这样的重新被产生出来的同一性的基础,谢林认为就在宇宙自身中,宇宙是自然和历史的同一性,而且这同一性永远不能被扬弃。如自然与观念世界的直接联系已被人的自由意识打破,自然与观念世界相互发生对立,但观念世界与自然的关系依然存在。自然对基督教如对希腊一样是无限者的基础和源泉。希腊是在“神性东西”(d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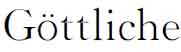 )那里直接看到“自然的东西”(das Natürliche),基督教则是透过作为神的躯体的自然,洞察到“内在的东西”(das Innerliche)和精神。也就是说,对于基督教,在它的历史诸神成为自然诸神的地方,确切说来,在历史的诸神“获得自然的资产”时(Ibid.,S.449),那里将有自然的再生,而且会被哲学地认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谢林才作出如下断定:
)那里直接看到“自然的东西”(das Natürliche),基督教则是透过作为神的躯体的自然,洞察到“内在的东西”(das Innerliche)和精神。也就是说,对于基督教,在它的历史诸神成为自然诸神的地方,确切说来,在历史的诸神“获得自然的资产”时(Ibid.,S.449),那里将有自然的再生,而且会被哲学地认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谢林才作出如下断定:
在自然哲学那里,就如它已从观念的原理构成了自己那样,已经造就了那种未来的象征系统和那种神话的最初的深远的资质。[……]它却必然不是由某个个人,而必然由整个时代来造就(SW.V,S.449)。
作为公开、客观的科学,自然哲学应该代表近代神话的另一个直观方向,将自己设定为对“观念东西”(das Ideale)绝对地压倒“实在东西”(das Reale)这种情况的一种均衡。因为在这种观念压倒实在的情况下,自然退回为神秘,理性不再以自然的观点,而是以魔幻的观点看待所有事物那种更高的统一。自然哲学应凭借其实在的考察方式,在主体的内在直观之外,在诸自然事物那里,证明实在与观念的同一。而这种自然直观即是未来神话的最初的,最深远的基础,在这种自然直观那里蕴含人类未来神话和象征系统的一般可能。
对于早期浪漫派,诗的“质料”涉及一种摹仿行动,而这个问题是与艺术实践直接相关的那种艺术理论关联中的一个问题。然而对于谢林,艺术与神话的关系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如古典时代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表述的那样。现在,艺术与它的“质料”神话的关系首先必须借助于哲学去重构。无论是“质料”还是自然哲学都必须存在论地去理解。从艺术创造的实践努力的角度考虑,他将解说的重点放在“质料”的必然性和“质料”的诗性再创造上。至于“质料”的选择可能,谢林从作为给定东西的“质料”本身去推导。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思想是关于近代世界的“质料”本身的固有东西的看法。按照他对观念神话的建构,“质料”始终是表述在整个历史中的同一性。如果说这种同一性在近代世界破裂,那么它却依然作为相互指向的元素“存在”(Ibid.,S.686)。所以对新的世界来说,哲学、宗教和艺术又是作为一般关系的生长点存在的。对于近代世界来说,真正的史诗即新的神话,应当从所有这些元素的“不可取消的混合”中自行构成。“质料”之来自自然哲学有一种必然。在近代,科学以诗和神话为前导,而自然哲学的直观方向必给予宗教的直观以帮助。完成的综合应该是诗人的整个时代所给定的东西与宗教、哲学及诗的诸理念的全面融汇,以此将满足近代诗的一般要求,也即达到普遍性。
与这个要求相应,谢林复将“质料”解说为必须诗意地重新创造出来的。新神话式的诗本身不允许“仅仅按照某些特定的哲学理念”被构想出来,而只能通过“创造”产生(Ibid.,S.446),它也不允许“它的诸神的观念构成通过物理学”被给定。于是历史理性不得不等待它的诸神,诸神必须构成自己,甚至于必须在观念性的构成过程中“完全独立于”自然哲学而构成(Ibid.,S.449)。所以谢林在讨论中直接批评了那些误解和轻率的错误做法,将“质料”仅看作经验意义上的现成东西这类误解,以及艺术实践内部的一些错误和轻率的做法,试图将这种“质料”当作经验类的材料运用到诗本身中,比如用希腊形象去象征某些自然哲学理念。正如诸神决不是时代关系的反射,对诗人的义务和规定的完成,亦仅仅发生在给定的“质料”的诗意构形那里。如果作为自由和必然绝对综合的新神话始终保持为公设,那么人只能通过整个历史去赢回这个必须重新建立的同一性状态。在这种上下文关联中,谢林思考了“诸神归来”的那些条件:自然哲学作为对存在整体的直观应当为赢回现实性的诗意创造、为新的神话的构成提供“质料”。但这也取决于这种自我生成和自我构形的“质料”本身固有的品性。
谢林的洞见具有一种普遍性,因其建立在自然哲学准备上。在这个总体关联中,谢林已经把自然哲学与新神话的关系从诗歌的构成活动的立场阐发出来。这个关系被构想为新神话的条件。新的自然哲学对近代构成活动的作用是走向重建自然象征观的途径,因为它可以克服片面的神秘主义的倾向。所以,谢林在System 1804的结尾,结合着对艺术“质料”的建构,把借助于自然哲学重建自然象征观阐发为“走向重建一种真正的神话的第一步”。不过,对于艺术“质料”本质的提问本身已经指向“某种更高的东西”也即“人性的重建”(Ibid.,S.507)。也就是说,真正的神话的自我构成以一种道德的整体性为前提条件,它要求一个能够把自己有机地构建为个体的民族。
以此,将自然哲学作为质料吸收到神话的创造中的真正意义,具体化在完成“真正诗意和普遍诗意的质料”这个要求中(Ibid.,S.447)。“质料”复被解释为某种必须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正如它的实现,作为一种综合,唯一只能通过绝对的形式原理,通过形式的诗意绝对性发生。只有构形在其固有的有机形式中,本身转化为神话诸理念的自然哲学,能够作为“未来的象征体系和未来的神话之最深远的基础”而起作用(Ibid.,S.449)。
从近代构成的个体出发点看,普遍的诗“质料”使自己折射在诗人的形式独创性那里,诗人应该从“神话诗”的整个混合质料中创造出时代的史诗(Ibid.,S.444)。独创性在这里首先标志着诗人普遍化的一般能力,借助于自己的能力独创地结合有限性与无限性。在诗尚未再次成为类族的事情之前,在历史尚未把“作为最普遍有效的形式”的神话还给历史理性之前(Ibid.,S.477),诗性宇宙的统一的客观启示将通过无限“质料”在艺术作品那里的个体化过程显现,确切说来,通过作为形式原理的艺术天才而显现。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独创性就是诗的绝对性的近代形式。对谢林来说,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诗的重生,仅仅取决于形式原理的自律,不可能从理论上得到推演。
这种对新神话的存在论的界说,自觉地与浪漫派的相关理解拉开了距离,后者乃是更多地着眼于艺术实践提出的。必须重申,自然哲学作为诗的“质料”这个思想在谢林这里,不允许按照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知识与行动的关系经验地去理解。自然哲学的理念和思想在这里并非直接服务于演绎和推导实践类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它们不如说是指向了那种纯粹的可能:“理智直观”中存在着走向整体性生存的通道。自然哲学是对整体的认识,它从内部作用于精神的构成活动,可说是现实性的生长点,在那里人类理性的共同生活重新开始。由于自然哲学本身直接联系着一种整体性自然观点的要求——它唯一指向打开“诸原始源泉”,指向“成为宇宙的一幅忠实图像”(Ibid.,S.381)——谢林也思考着在它那里寻找象征形式的可能性,使哲学与诗的古老争端在其中必然地被扬弃。他考虑了观念世界中的一切特殊东西在哲学中的消解。不过他仅仅提示了哲学与象征的自然关系的可能。要更进一步地考察这个重要思想,还须兼顾谢林对作为史诗之重要门类的“教诲诗”的阐发和建构。
在自然哲学作为新神话“质料”这个命题里包含这样的思想:必须将哲学理解为知识活动与诗的统一。谢林在这里思考的是:宇宙即存在整体的一种忠实图像,其本身已经是诗意的。这样一种自然哲学的榜样显然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其形成在历史上是刚刚从神话中解放自己。这种自然哲学那里可以典范地找到对神性的肯定性直观,它在自身内联系着神话和神秘,作为对万有的知识活动同时又是诗。在PdK的第四部分,那里处理史诗的特殊门类,谢林曾经从史诗的创生的角度,把他关于自然哲学是新神话“质料”的思想具体化。在讨论史诗的一个类型教诲诗的时候,他深入到讽喻诗歌的表述方式中。教诲诗是种诗性统一体,在那里,知识性学说是诗意地表达出来的,它的方式是:目的扬弃在作品中,作品显得是为自身而存在。这种方式的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知识活动和诗的统一原初必然就在知识活动自身那里。知识活动通过自己的本质——也即那种作为存在整体的忠实图像存在的能力,“作为诗的形式”出现,确切地说,作为几种史诗形式中一种“比较具主体性的”形式出现(Ibid.,S.663,662),因为它的表达偏重主体性。谢林把古希腊的教诲诗按照取材分为两种,“道德类”和“理论类”或“思辨类”,并把它们与宇宙也即存在整体的关系作了整理。他揭示出这种诗歌类型的普遍特征,比如在神谱式的诗歌那里,“人的生命”被造就为“反射”智慧和实践知识的“客观东西”(Ibid.,S.663),而思辨的史诗的努力可以在自然哲学家如早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在泰勒斯、巴门尼德和色诺芬等人那里找到。我们在流传下来的自然哲学文献断片中还能看到这样的痕迹,这些文献都可以标志为“关于诸事物本性的诗歌”(Ibid.,S.664)。谢林特别注意恩批多克里的自然哲学诗,认为它把阿那克萨戈拉斯的物理学与毕达哥拉斯派的智慧结合得如此之好,可以看到充足的能量和诗意力量即是清晰的思辨原型。而卢克莱修的诗作完全相反,明白地揭示自己是绝对教诲诗的一种努力,它一方面在韵律的形式中跟随恩批多克里,另一方面在诗的取材方面模仿伊壁鸠鲁。他那种“做大自然祭司的激情”被谢林概括为“主体式的”(Ibid.,S.666)。这种情况的原因却主要存在于对象本身那里:它按其本质就不可能是诗意的。卢克莱修把伊壁鸠鲁学说的道德伟大与一种实践智慧、一种“更高的秩序”结合起来,这使他的诗有一种统一的立场,可以从之出发,把一切事物的进程和生命的整个承受都看作一个整体。
F.施莱格尔也在他的《关于诗的谈话》中与马尔库斯谈到诗的“教诲”类型,把诗的本质按斯宾诺莎的精神概括为“对诸事物更高的观念目的”。所以对他来说,教诲诗不再是诗的一个特殊的诗类型,而是普遍的诗类型。每一种诗都应该是教诲式的,就如它们同时也应该是浪漫式的。因此他同意赫尔德的这个看法,即诗歌必然要在各种艺术和各种科学学科的传达和表述那里去寻找。谢林却思考得更为深入:通过把教诲诗的本质在绝对知识那里进行建构——这绝对知识是以“太一”为其对象——教诲诗作为表述者也有能力“本身作为诗性的”而存在(SW.V,S.664)。在这种绝对的观点中,不仅教诲诗的可能性得到保证,而且,存在的其实只有一种绝对的教诲诗,它要“在知识活动中表述宇宙的反射”(Ibid.,S.666—667)[32]。“宇宙最完满的图像”必然在自然哲学那里达到(Ibid.,S.667),哲学作为“所有级次的消解者”真正意义在这里完全解密:
教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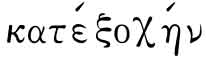 )只能是关于宇宙或诸事物本性的一种诗篇。它必然表述宇宙在知识活动那里的反射。也就是说,宇宙的完满图像必然在科学那里企及。科学被呼唤来成为这样的图像。这是肯定的:
)只能是关于宇宙或诸事物本性的一种诗篇。它必然表述宇宙在知识活动那里的反射。也就是说,宇宙的完满图像必然在科学那里企及。科学被呼唤来成为这样的图像。这是肯定的:
应该达到与宇宙同一的这种科学,不仅在质料的方面,而且也通过形式与宇宙吻合。同时,宇宙在多大意义上本身即是所有诗的原型,甚至于是绝对者自己的诗,科学就在与宇宙的同一中按照质料也按照形式本身是诗并融解在诗当中。也就是说,绝对的教诲诗或思辨的史诗的起源与科学的完成是融汇为一的。而且,如最美、最终的规定,起源与完成都返回到这个大海洋里。[33]按照前面对近代真正史诗和神话的唯一可能性已经揭示的东西,也即新世界的诸神(它们是历史的诸神)必须夺得自然的资产,以便作为诸神显现出来——在这种考虑中,我要说,最早的关于诸事物本性的真正的诗篇,其与真正的史诗应该是同时出现的(SW.V,S.667)。
这样一种教诲诗——其中不仅形式和表述工具是诗意的,而且作表述的东西自己也是诗意的——对谢林构成了真正自然哲学的理想图像和近代教化活动的目标,它是近代意识努力要实现的。这种情况就是最后的神话意义上的综合:哲学、宗教和艺术作为原初从神话中分流出来的几大潮流,最终借助于人类实存,复将自己完成为回归宇宙的回构活动的几大元素,以此把自己复构为一体的。谢林坚持关于新神话的思想,坚持一种通过美和艺术构成自己和构形自己的未来。
在谢林那里,早期唯理念主义对新神话的构想赢得了其完整形态,它现在成了存在论的神话学。相反,黑格尔还在他的耶拿时代早期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脱离开荷尔德林和早期浪漫派的影响,致力于神话的历史性问题。[34]对他来说,在精神上离开谢林的直接动因已经存在于谢林关于艺术作为哲学“官能”的这个先验哲学命题论证那里。所以他在Differenz(《费希特体系与谢林体系的差异》1801年)一文中提示了近代教化与古典的“活生生的艺术”的“生活关系那整个系统”的决定性的疏离和分裂。[35]随着耶拿后期他个人的美学思想的产生——这美学部分地建立在对神话的具体历史直观上——黑格尔最终在1806年彻底告别了早期唯理念主义关于一种新神话的构想。早期对历史阶段的三分法,随之还有对一种未来新宗教的理想——其特点是柏拉图的美理念——的鼓吹,均被放弃。他的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对“艺术的过去性”及艺术的历史功能的洞见上。黑格尔转而持续地致力于对神话的历史化。他的美学最主要地是为近代意识提供了真正的艺术及神话那里的那种“超出自己而作提示”的东西。[36]
【注释】
[1]Cf.F.Rosenzweig(hg.),”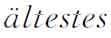 s Systemprogramm von1796/97“Sitzungs
s Systemprogramm von1796/97“Sitzungs ichte der Heidel
ichte der Heidel 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 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he Klasse,1917;Jamme/Schneider,Mythologie der Vernunft.Hegels”
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 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he Klasse,1917;Jamme/Schneider,Mythologie der Vernunft.Hegel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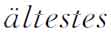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1984,S.13.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1984,S.13.
[2]参看PdK的导论部分,谢林在那里开门见山,明确地提出了返回诸理念也即“返源”的要求,他认为诸理念是“艺术的诸种原始源泉”,SW.V,S.360—361。
[3]F.Schlegel,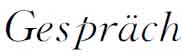 ü
ü die Poesie,1800.
die Poesie,1800.
[4]在其《论对希腊诗的研究》(1797)一文中,F.施莱格尔引进了对“审美革命”的文学史的观念,其涉及客观性在近代教化的理论和诗中的主导地位,近代教化问题在那里已提前作为中心问题勾划出来。
[5]对System的第四主要部分中实践哲学任务的第三解决,也即对此问题的解释:“意志活动究竟通过什么对自我重又成为客观的”,同时即是谢林对历史概念给出的先验阐发,而且是从三个考察点出发的阐释,即从关于历史的意识的可能性出发、从人类进步的历史标准出发和从作为“自由与必然的统一”的历史的特征出发的考察,Cf.SW.III,S.417—441,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88—256页。
[6]Cf.Bruno,SW.IV,S.332.
[7]在1802年的同一性哲学文献“论自然哲学与哲学一般的关系”中,谢林对最终的道德完成的论证重点是在“灵魂净化”及灵魂参与原知识活动那里,参看SW.V,S.121—124。
[8]此处指的是自然当中发生的诸理念的诞生。
[9]参看谢林对观念世界中绝对知识与绝对行动的同一性的论证(SW.VI,S.537—541),着眼于人类个体自由的自由与必然关系阐发(Ibid.,S.541—543),以及他在其“万有论”框架中对此的讨论(Ibid.,S.544—548)。
[10]Cf.SW.III,S.477f.,SW.V,S.416—417.
[11]在这里,笔者不准备对Systemprogramm即所谓《德国唯理念论最早的体系规划》的作者公案提出新的甄别讨论动议,的确在没有发现进一步的材料时,这个问题目前依然只能悬置。笔者只想适时提示下列几个事实:第一,除去在作者无定论的Systemprogramm那里,“新神话”这个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根本没有出现过,而黑格尔作为Systemprogramm的作者尚有待证明;第二,虽然青年黑格尔像谢林一样区别了历史的三大阶段,也即希腊自然宗教、基督教宗教和未来的新宗教,但他在其法兰克福时期之后,在告别荷尔德林,拒绝歌德时代之后,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新神话”这个思想的反对者。耶拿中期的黑格尔已经在坚持神话的“过去性”及美与艺术的“无力”的观点。他认为美和艺术不再能立法式地、给出规则地构形我们的未来。在《精神现象学》的前言中,在他的《美学》讲座系列中,我们都可以听到他反对理智直观作为对概念的哲学的一种克服的强烈抗议之声。对黑格尔的主导动机的分析,可参看O.波格勒在《黑格尔研究》(Hegel‐Studien)补卷20上发表的研究,见1980年号,第249—270页,正是这些动机最终使得黑格尔与诗人荷尔德林那种“完满的美是至高的统一”的思想拉开距离,并对谢林的《艺术哲学》公开采取了对立的立场和批判的观点。
[12]见“关于神话的谈话”,载《批判文集》(F.Schlegel:Kritische Schriften),W.拉施(W.Ra‐sch)主编,第307页以下内容;赫德(Herder)在他的历史哲学那里曾设想借助于想象的力量为个体去调和历史的诸种强力,比如借助于把早期时代与诗性时代等量齐观的做法;K.莫里茨(K.Moritz)则要借助于一个公设——走向美的真正概念的道路必然由一个以积极的想象力激发的神话所引导——完成类似的任务,参看Entwurf zu dem vollst-ndigen Vortrage einer Theorie der sch9nen Künste.Schriften zur und Poetik,H.Schrimpf(hg.),1962,S.123f。
und Poetik,H.Schrimpf(hg.),1962,S.123f。
[13]H.戈克尔并未在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和早期浪漫派的新神话理念之间作出分别,但他已注意到“新神话”这个关键概念在Systemprogramm中的表述以及谢林《艺术哲学》中的阐发与小施莱格尔在《关于神话的谈话》中的表述,存在着一种不和谐,参看其1981年的研究专著,第312—316页。
[14]谢林不曾构想一种确定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过他在自己的两个耶拿讲座系列中建构基督教的本质的时候,以及在Gesamtsystem von 1804中建构观念世界的级次时,都涉及了有关命题,特别是他在Philosophieund Religion中提出的“灵魂学说”表达了他的历史思考的主要观点。
[15]这是谢林的自然形而上学阐发,凭借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与康德商榷,其存在论的论证已完成在他的自然哲学那里。
[16]同一性哲学已经在这点上超出了早期的Briefe,因其已把自由与必然的同一作为先决条件,而在Briefe中这同一性是在悲剧的结束时才能企及的东西。Cf.SW.I,S.338f.
[17]参看PuR及S ystem 1804两部同一哲学文献中的相关内容。
[18]Cf.Materialien 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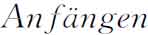 ,M.Frank/G.Kurz(hg.),S.110—112);F.W.J.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H.Fuhrmans(hg.),Bd.I,1962,S.70.
,M.Frank/G.Kurz(hg.),S.110—112);F.W.J.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H.Fuhrmans(hg.),Bd.I,1962,S.70.
[19]Cf.H.Gockel,Mythos und Poesie,1981,S.314.
[20]Hesiod,Theogonie,79,参看[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页。
[21]审美的诸理念,按照康德的提炼,乃是对这样的想象力的表象:“它们(想象力)大可成为思考活动的契机,但却不必与任何一种确定的思想也即概念切合;它们肯定是任何语言不能完全企及完全阐明的。”“理性理念——它反过来是个概念——的对应物乃是任何直观(想象力的表象)不能适宜地表现的”,Cf.KdU,§49,Kant‐W.Bd.X,S.249,250。
[22]Cf.J.Schmidt,Die Geschichte des Genie‐Gedankens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Philoso‐phie und Politik 1750—1945,Bd.I,Von der Aufkl-rung bis zum Idealismus,1988,S.390f.
[23]在促发一种新神话这个问题上,谢林与F.施莱格尔的关系,谢林研究大家X.蒂利特(X.Tilliette)的系统解释颇富启示,参见Schelling.Une philosophie en devenir,S.442f.,1970;R.海姆(R.Haym)提供的资料也相当完备,此处讨论的问题可参看Die Roman‐tische Schule.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1961,S.648,693。
[24]比较F.施莱格尔的表述,Kritische Schriften,1964,S.314,499f.。
[25]参看J.赫尔德的斯宾诺莎对话,见J.G.Herder,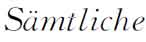 Werke,B.Suphan(hg.),1877—1899,Bd.16,S.431f.,S.541f.,S.479—480;另可参考戈克尔(Gockel)的相关表述,1981,S.169—173。
Werke,B.Suphan(hg.),1877—1899,Bd.16,S.431f.,S.541f.,S.479—480;另可参考戈克尔(Gockel)的相关表述,1981,S.169—173。
[26]见“关于诗的对话”,KA.Bd.2,S.320,S.317f.。
[27]Ibid.,S.319f.,S.415.
[28]Cf.J.G.Herder,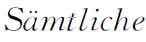 Werke,Bd.18,S.485f.
Werke,Bd.18,S.485f.
[29]谢林对“思辨物理学”作为同一性体系的自然学说、作为一般自然科学和作为科学本身的几种提示,在他的Studium(1803),PuR(1804)、System 1804和Aphorismen 2(1806)中都可以读到,参看SW.V,S.317,324;SW.VI,S.17—18,493—494;SW.VII,S.144;关于谢林自然哲学的现实性和界限问题,可参考H‐D.Mutscher,1990著作。
[30]见Wahrer Begriff,关于同一性哲学的内部关系和结构,参看SW.IV,S.88—89;我们讨论的上下文中的自然哲学不可混同于先验哲学体系中关于自然的唯理念论,注意第83—84页的表述,特别是谢林本人对同一性体系内自然哲学的“实在—观念”考察方向的先在性的表述,参看第92页。
[31]参看谢林在1.Entwurf中对自然哲学的科学特征的表述,SW.III,S.273—275。
[32]同一哲学的这种观点,是招致当代哲学美学批判的靶子之一。只有存在一种绝对诗的这种观点,对近代的历史理性无异于一种威胁,因为它去掉了多样性。
[33]谢林此处使用的意象,同他在System结尾处使用的一样,应该是一个神话学意象。
[34]按照语文学家O.波格勒对耶拿时期黑格尔一些手稿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手稿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正是历史哲学式地对审美希望作出拒斥。笔者认为假如波格勒这个研究判断准确并证据确凿,那么它反过来就很难支持黑格尔作为“规划”作者的断定。参看Hegelstu‐dium,Beiheft 20,S.249—270;以及黑格尔著作,Jenaer Systementwr fe I,Gesammelte Werke Bd.6,S.330f.。
[35]这个问题可参看O.波格勒的文章”Die Neue Mythologie.Grenzen der Brauchbarkeit des deutschen Romantik‐Begriffs“,in:Romantik in Deutschland,R.Brinkmann(hg.),1978,S.346—348;另参看L.Seep 2000年著作第46—48页。
[36]Cf.G.W.F.Hegel,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Gesammelte Werke Bd.9,1979,W.Bonsiepen u.R.Heere(hg.),S.402;另可参看C.Jamme,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Mythos,Bd.2:Neuzeit und Gegenwart,1991,S.26—41,5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