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神话作为艺术的形而上根基
谢林哲学的主线表明,谢林完整发展出其主—客体的唯理念主义的时候,也就是他存在论地集中处理神话的时候。谢林批判地与主观唯理念主义的美学拉开距离的时候,正是他转向审美直观中的神话的时候。完成同一性哲学的整体论,借助于以此获得的关于神的知识,谢林站在艺术的立场上把神话设立为哲学的题目,把一个理性的神话学纲要建立为艺术哲学的核心部分,这是近代哲学对神话的第一次伟大理性阐释和体系处理。谢林的这个真知灼见可以说是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获得的具有代表性的洞见:神话对于一种真正的艺术形而上学既非偶然的亦非不重要的,相反神话构成这种形而上学的必然组成部分。谢林一直保持这个洞见,直至他晚期在神话哲学当中作出的“宗教—哲学”的神话再发掘。
因此,对神话一般的哲学建构不仅构成PdK主要部分的重要内容,这神话学构架本身在PdK的整个问题集合那里也有一种关键地位。因谢林强调,整部PdK的基本任务正“在于对神话的建构”,借助于这种建构应该揭示美的一般生存。具体说来,就是要为这个存在论的提问——从一般和绝对的美那里如何可能出现诸特殊的美的事物?——找到一个理性的回答,提出一个维系性的纽带,一个提供同一性的原理。这种借助于神话而“存在论—认识论”地扩展理性的方式,而且恰恰凭借作为理性科学对照物的神话,可以看作是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史获得的一项重大业绩。柏拉图对神话的固有真理存有深度怀疑。尽管如此,他仍然为哲学而要求这种真理,如《高尔吉亚篇》证明的那样。神话在柏拉图对话中扮演的角色极其引人注目,他中期的对话如《会饮篇》,《斐德若篇》等皆是典范的例证,其对话完全借助于神话的表象方式和言说方式发展和收尾。[27]而在谢林这里,哲学着眼于神话的理性的关联,将它纳入在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体系内部,并赋予其坚实的论证:神话被哲学地论证为艺术的根基和源泉。谢林的神话学处理不仅陈述地阐明神话的真理,而且使这些真理全数成为哲学的命题。PdK以此赢得其问题集合的一种特有的维度,接近了这个事实——艺术必须存在论地回到它的神话根基那里;PdK必须将神话建构直接设立为一系列讨论的出发点,因为这些讨论均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提出这个关键的问题:艺术这个现实性的场所,其与自己的存在原始源泉,与自己的理念世界有怎样的关系?
谢林PdK中的神话学切入有意识地站在启蒙主义的神话理解对面,但它也是通过时代的启蒙主义精神直接促发的。这个时代中,启蒙意识在脱离了神话思维之后,感受着失去统一性的威胁,试图返回到本质那里并与之衔接。
在1800年左右围绕审美基础的密集讨论那里,神话渐次进入了中心。古典的神话研究、浪漫派对自然中情感世界的渴求等,都是要从神话那里得到人类理性的一种整体性支持,以均衡时代的一般理智和良知。但一种神话对艺术的意义仍然没有得到解释,神话还没有在哲学意义上重新获得。如果说神话问题的提出恰与近代发展过程密切相关,那么对启蒙主义者那种狭窄化的合理主义,对技术理性那种纯粹的使用态度来说,神话本身必然始终不可企及。因为它们在其偏见中只能将神话理解为某种流传下来的,属于过去的东西。而神话的整体决不允许自己仅仅被看作一种时间性的,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允许自己被看作一种过时的认识形式。它甚至不允许自己被看成一种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从属性的学科领域,其任务可以凭借狭窄化的合理主义观点去推动,其研究可按照经验的诸总体关联去穷尽。相反,神话面对科学的研究,总是不断指向一更大的维度。
对艺术哲学与神话哲学的本质关联的阐发,有助于对神话真理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赢得。哲学史地看,1802年谢林在PdK中的这一尝试是在继续展开一个已经存在的神话学纲要,即表述在Systemprogramm(1796—1797)中的“理性神话学”纲要。那里曾经以清晰的体系意识凸显一种指向“未来整个形而上学”的理论关怀:要建立“诸理念的一种完整体系”,即作为自由的、自我意识了的自我的理念,这是理性本身的理念,作为这样的东西是哲学反思的主体;作为一“整个世界”的自然的理念,这是从“无中出现的创世活动”,本身是“伟大物理学”的对象;以及人的理念,这是把自由作为其本质规定的生物,在他那里内在地联结着诸原理,即人的一种历史所必需的那些理念,如关于道德世界的理念、神的理念、不朽性的理念,等等。这个纲要恰恰也在一种与美学的紧密关系中把一种“理性神话学”作为任务:这种神话学应当帮助完成对诸理念的感性化。
在Systemprogramm中即有这样的宣告: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神话,不过这种神话必须服务于诸理念,它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神话学。
在我们使诸理念成为审美的也即神话学的之前,这些理念对于民众没有什么意义,而反过来说,在神话学成为理性的之前,哲学家必定要为自己感到羞愧。[28]
如果说,在这个“体系规划”这里,这种“服务于诸理念”的神话学还只是整个纲要的一个陈述命题,那么在谢林的PdK中——注意它恰恰是个“诸理念的体系”——它已经发展为一种存在论的神话学构想。此构想在谢林这里最初步的执行步骤即与Systemprogramm中要把“一切已得到解说的东西与尚未得到解说的东西”融汇在一起的指向格外吻合。[29]例如,在涉及哲学美学的基本建制的情况下,PdK努力要为艺术的尚未解说的“诸源泉”、为艺术与其神性原理的关系和神话真理要求的效力作出存在论的解释,由此已经把神话阐发为艺术的形而上基础。
从发生史来看,这个构想却不能直接等同于将Systemprogramm中的那些思想全部付诸实现。我们在这个哲学的神话学的建立这里,还必须突出早期浪漫派关于“一种新神话”的诗歌工程的重要影响。如果抛开早期浪漫派的这个“新神话工程”不谈,我们就无法完整把握谢林这个哲学神话学的切入,因为它与这个精神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其分有共同的精神方向。不过我们也应当记起,还在“新神话”这个术语在谢林的System结尾章的艺术哲学中第一次出现时,它就明确地带着一种理论商榷的论战印记——与早期浪漫派的艺术理论商榷。那里的宣布显然直接有所指,起因应该就是F.施莱格尔在1800年上半年发表在《关于诗歌的谈话》中的“关于神话的谈话”(”Redeü die Mythologie“)。F.施莱格尔在那里抓住关于“新神话”的思想,首先提出了一种浪漫派诗歌的建设工程。[30]这篇谈话的要旨,通过诗歌从现代精神的内部构想一种新的神话,完全指向对古典和现代做一种未来的诗性综合,而这种诗性综合的前提条件则是进行一场审美革命。[31]于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浪漫派的作为新艺术的“新神话”工程——其先行者可以追溯到赫尔德关于新神话的思想那里——以其对于古代和近代的对立的一种清晰的意识,对于古代和近代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认识为基础。F.施莱格尔更多地把古代视为历史地已消失的,对他来说,甚至温克尔曼和赫尔德对古今之争表示的那种立场也还很成问题。[32]他更多地想抓住从现代内部出现,本身构成为对古典的否定的那种新东西,而不是要求和促进一种新经典,一种脱胎于古典的再创造。
die Mythologie“)。F.施莱格尔在那里抓住关于“新神话”的思想,首先提出了一种浪漫派诗歌的建设工程。[30]这篇谈话的要旨,通过诗歌从现代精神的内部构想一种新的神话,完全指向对古典和现代做一种未来的诗性综合,而这种诗性综合的前提条件则是进行一场审美革命。[31]于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浪漫派的作为新艺术的“新神话”工程——其先行者可以追溯到赫尔德关于新神话的思想那里——以其对于古代和近代的对立的一种清晰的意识,对于古代和近代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认识为基础。F.施莱格尔更多地把古代视为历史地已消失的,对他来说,甚至温克尔曼和赫尔德对古今之争表示的那种立场也还很成问题。[32]他更多地想抓住从现代内部出现,本身构成为对古典的否定的那种新东西,而不是要求和促进一种新经典,一种脱胎于古典的再创造。
在System的结尾部分,那里,哲学的先验自我在走完“返回自身”的漫长途径后,通过艺术哲学达到了自己的旅程终点,为此谢林写道:
然而,如果说唯有艺术才能成功地使哲学家只能主观地表述的那种东西普遍有效地成为客观的,那么让我从中再推出一个结论:必然可以期待,如同哲学在科学的童年曾从诗中诞生,从诗得着滋养那样,哲学与所有那些借助它臻于完成的科学一起,在完成之后,犹如百川汇海,返流到它们曾由之发源的、诗的普遍性的大海洋里。至于科学的回归于诗的中间环节会是什么,一般而言不难回答,因为在这个现在看来是不可解除的分裂出现之前,这样的中间环节曾存在于神话那里。但是一种新的神话,一种不能是个别诗人的创造,只能是一种新的、仿佛是体现为一个诗人的类族的创造,本身如何能产生,这却是一个难题,其解决唯一只能期待世界未来的种种命运,期待于历史下一步的发展进程(SW.III,S.629)。
在这里,我们清晰地读出了早期唯理念主义的神话理解中所含的问题意识,它因这种问题意识而不同于、甚至对立于早期浪漫派的观点。首先谢林就强调地把一种“新神话”的产生方式总结为历史哲学的一个问题集合。人类的这个有待实现的目标位于无限遥远的地方。谢林给出了一种提示,那就是,“新神话”在历史中必然始终是一个“问题”,以此他首先完成了与早期浪漫派在“新神话”名义下的艺术实践理论和工程的一个清楚的概念划界。谢林还在脚注中补充说,他准备出版自己多年前写好的一篇关于神话的论文,那里可以看到他如何展开其唯理念主义的神话学思想[33]。A.阿尔沃恩据这个脚注推测这篇东西与PdK中的神话学章节有着直接的总体关联,这却仍然不能认定。[34]因为PdK中有关神话学的这一部分是否确实在多年前写就,现在作为其一部分收入PdK,这是谢林手稿专家们迄今未能搞清楚的问题。一般认为,现在能够确定的只是,System中的神话提示与艺术哲学中的神话学建树属于同一个神话学动向。还有,它们那种与早期浪漫派的商榷姿态也是同样地鲜明。也即,在关于一种“理性神话学”的提法这个问题上,谢林与早期浪漫派的共识是有前提条件的,他坚持这个问题集合。因为对他来说,“新神话”的思想及其理论切入,根本上关系到如何重新赢得“诸种原始源泉”,而一种“新神话”只有被纳入在这种问题总体关联中才能谈得上做哲学的处理。
实际上我们在考察早期唯理念主义对早期浪漫派的新神话思想的作用以及两者的共同之处时,还必须不断地想到它们的区别。两者是通过一种精神运动中的交互作用发生关联并有共同的理论来源。但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立场和观点,反映出彼此不同的哲学素质。从这种意见相左的方面看,整个“耶拿维尔茨堡”时期的PdK的产生也完全可以解说为谢林对早期浪漫派借助于一种政治的审美革命完成“理性均衡计划”的一种论战式理论商榷。
谢林在1802年致A.施莱格尔的一封信给了我们一些提示,那里提到谢林在当年夏季学期开始的时候,“主要把力量放在神话学上”,他已经将其建立为PdK的开端部分。当时这部分文本的完成状态究竟如何,我们在维尔茨堡手稿的神话章节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资料源可供参考,这就是谢林研究专业圈中所说的“罗宾森—笔记稿”[35]。这个笔记稿的流传也可以佐证笔者的命题,即PdK中的神话学纲要乃是全书一般部分的核心。
现代理性把重新赢得人类的现实性树立为自己的行动目标,而艺术对于这种“重新赢得”的行动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具有与神话的那种天然联系。神话是艺术的原始源泉,艺术还在其童年时代就建立了种种与神话的关联和关于神话的各种体验,并以此成功地保留了神话。这种关系正是笔者要在下一章里继续展开的。
【注释】
[1]对谢林自然哲学与其1801—1802年的同一性哲学体系间的关系问题这个研究课题,推荐参考德国唯理念论专家H.霍尔茨(H.Holz)教授一系列专著,首先就是他的名著Die Idee der Philosophie bei Schelling,1977年版,S.64—126,尤其是其中论证形成谢林的自然概念背景的那些理论因素,S.19—63;关于谢林自然哲学的问题史和基本特征,可参看他的”Perspektive Natur“,in H.M.Baumgartner hg.Schelling.Einführung in seine Philosophie,1975,S.58—74;另参看他的唯理念论研究专集下卷中有关论述:”Schellings Ans-tze zu einer Naturphilosophie“,”Das Ontologische Argument und die Philosophie Schellings“,in Geist in Geschichte.Idealismus‐Studien.II.Halbband:Fichte,Schelling,Hegel.Die Macht der Idee im konsystematischen Monolog,1994,S.228—248,249—277。
[2]关于谢林吸收康德的目的论批判这个问题,我在这里首先提示W.施米德科瓦齐克教授对德国唯理念论这段问题史的深入研究,参看同一作者1996年专著第37—65页的分析,如前所提示,此书已被收入拜恩科学院谢林学会《谢林研究丛书·卷8》;O.马夸德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更愿意将这个问题集合概括为在康德那里的“审美切入”和谢林那里的“审美替代”,参看其1989年的著作Aesthetica und Anaesthetica,S.9—14,他在其1987年的著作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Romantische Naturphilosophie.Psychoanalyse中也提示我们,在谢林那里,美学问题与自然哲学的问题总体上是关联在一起的,S.100—166。
[3]参看本书第一部分第四章第一节关于谢林的《第迈欧研究手稿》的研究状况简述。
[4]我们在这里完全不介入对谢林哲学的形态问题的争论。
[5]众所周知,耶拿时期的黑格尔在其著名的文章《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Differenz,1801)中还完全站在谢林立场一边,其关键论述,可参看黑格尔的”Vergleichung des Schellingschen Prinzips der Philosophie mit dem Fichteschen“,in G.W.F.Hegel:Werke,Suhrkamp,1970,Bd.2,S.94—115。
[6]可比较R.劳特(R.Lauth)对费希特先验自然论的全面阐述,1984;较好的材料还有P.Ru‐ben,”Natur und Freiheit.Zum Naturverst-ndnis Johann Gottlieb Fichtes“,W.Janke,”Fichtes Bestimmung der Natur an ihr selbst“,in K.Gloy/P.Burger(hg.)Die Naturphi‐losophie im Deutschen Idealismus,1993,S.24—49,50—66;M.Frank,”Die naturphilos‐ophische Abkehr von Fichte“,in Eine Einführung in Schellings Philosophie,1985,S.104—118;对此还可以参看谢林在其Gd P(1827)中对其“自然哲学—同一性哲学”理论建设及对费希特的绝对唯理念论批判的回顾,SW.X,S.90—98。
[7]笔者在此有一个提示,谢林在克服费希特哲学的时期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表达法:“为什么对理性必然有一外部世界存在”?这个提问法在其自然哲学文献、System和同一性哲学文献中都曾经出现;而Systemprogramm的作者也使用了这同一个表达,见其中的提问:“为什么一个为了道德生物的世界必然被创造出来”及其对自我与世界同时诞生的回答意向和相关叙述。
[8]Cf.J.G.Fichte, das Wesen des Gelehrten,J.G.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69,Bd.I,8,S.73f.
das Wesen des Gelehrten,J.G.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69,Bd.I,8,S.73f.
[9]以下缩略语Wahrer Begriff。
[10]谢林的同一性哲学以系列文献形式流传下来,其中包含已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著作,也有未完成的著作手稿。
[11]关于这同一性体系对康德的借鉴和对歌德思想的吸收,可参看B.朗(B.Rang)的工作成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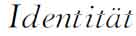 und Indif ferenz,2000。
und Indif ferenz,2000。
[12]以下缩略语Bruno。
[13]以下缩略语F.Darstellungen。
[14]以下缩略语PuR。
[15]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称绝对者为主体与客体的“绝对无差别”,因为绝对者既是哲学知识体系的主体又是其客体。绝对者作为主—客体,那种观念—实在的东西,既是精神又是自然,但不能把它理解为有区别的东西,因为它是精神与自然的无差别点。这样的无差别点同时也是所有哲学知识体系原初的绝对出发点。谢林在建立整体论的哲学体系时所寻求的正是这样一个“绝对无差别点”,他认为在这个点上,实在论和观念论不过是从同一个点发出的两种合法的考察观点或论证方向,所以他的同一性体系要借助于绝对同一性原理抓住和考察这个点,以确立一种与特定的自我肯定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绝对同一性表象。
[16]关于同一性哲学的柏拉图吸收,Cf.C.Beckermann,Schellingiana Bd.11:Das antike Denken in der Philosophie Schellings,S.147—196。
[17]级次说是谢林关于诸级次(Potenzen)的理论。诸级次是谢林哲学的基本概念,其自然哲学与同一性哲学都以诸级次指称自然中诸创造活动的动态的阶段和层次。但在其自然哲学那里,级次说重在标志自然过程的序列层次关系并突出其普遍显现方式为诸级次的三重性,较高的级次在更高的差别化中重获较低的级次;而同一性哲学对级次说的诠释重点不同,它更强调诸级次是走出绝对同一性的诸形式,并把诸级次诠释为绝对同一性诸形式间的量的差别。
[18]Cf.Darlegung,SW.VII,S.52.
[19]“无差别”是谢林同一性体系的核心概念,谢林用“无差别”与同一性这两个概念去标志其整体论的哲学规划,它要扬弃自康德的理性批判以来在哲学中所设定的那种分离,因此谢林思考的重心是对立面的一种统一。例如在其自然哲学的思辨论证中,谢林将自然中的一种朝向原始同一性的奋争作为公设。这种奋争的现实实现就是“无差别”也即对立面的统一,不过,所有现实地实现的统一都并非原始的同一性,而只是从差别即对立面中重新创造出来的同一性。
[20]Cf.Darstellung,§13,§14,SW.IV,S.51—52;另见F.Darstellungen中将思维与存在作为无限者与有限者关系的全部推演,同上书,第381—389页;特别还有哲学对话Bruno对一种生产性的想象力的总体关联的构想,同上书,第239—242页,243—251页;与自然哲学有紧密的联系、为自然哲学而作的Aphorismen 1所勾勒的整个的“有限者与无限者的关系学说”,SW.VII,S.189—197。
[21]按照谢林长子K.F.A.谢林(K.F.A.Schelling)为《艺术哲学》而写作的编者前言中的说法,谢林写作《艺术哲学》只是进行“一种尝试”,他的这个讲座使用了席勒、歌德、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材料,以便将他自己哲学中获得的各种思想和方法运用到艺术科学上。谢林本人认为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字乃是他撰写的关于悲剧的那些章节,故而不主张出版全书,只同意发表其中的部分内容,Cf.SW.V,S.VII‐VIII;而著名的浪漫派史学专家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1821—1901)在比较研究谢林《艺术哲学》与A.施莱格尔的艺术理论讲座这两份文本后确认,“哲学家从文学史家那里取用、借用资料的情况,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得多”,相反却是A.施莱格尔在“直接从谢林先验哲学收尾段落中的富于启示的思想那里”吸收营养,以“建立个例丰满、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美学体系”,参看该书第837页;另参看G.L.Plitt(hg.):Aus Schellings Leben.In Briefen.Bd.I,第397—398页,E.Laune(hg.):A.W.Schlegel,Kr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批判文集及书信集》),SW.II,特别是第225—316页。
[22]关于System中对艺术的先验演绎构成艺术哲学的一种前提条件这个问题,可参谢林专家H.M.鲍姆加特纳(H.M.Baumgartener)1996年的专著第97页以下的内容,这本书被公认是谢林哲学基础导论中最好的一种,其在问题史的叙述中同时将研究最前沿的信息带给入门者。
[23]关于谢林先验哲学及其思辨自然哲学中审美措施的“替代”特征,可参看O.马夸德1987年的著作中的看法,第131—168页,尤其是第153—160页的内容。
[24]参看W.韦尔施(W.Welsch)1996年的专著Grenzg-nge der 中《从美学的诸后果看席勒批判》(”Die Schillerkritik hinsichtlich der Konsequenzen der
中《从美学的诸后果看席勒批判》(”Die Schillerkritik hinsichtlich der Konsequenzen der “)一文中对谢林的批评,斯图加特版,第118—121页。
“)一文中对谢林的批评,斯图加特版,第118—121页。
[25]关于谢林的自然理念及其现实性问题的综合研究,我在这里提示T.施奈德(T.Schneider)1997年的工作。
[26]在这里不能深入到对谢林自然哲学及其整个问题集合的总体表述中。在下面关于“万有论”的章节中,笔者也只能暂时先处理和讨论一个要点亦即其“级次说”。
[27]对进一步了解柏拉图如何借用神话的表象方式和陈述方式,可参看W.Hirsch,Platons Weg zum Mythos,S.230f。
[28]Cf.H.Fuhrmans(hg.):F.W.J.Schelling.Briefeund Dokumente,Bd.1,1962,S.69—71;M.Frank/G.Kurz(hg.):Materialien 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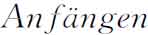 ,1973,S.110—112.
,1973,S.110—112.
[29]Cf.H.Fuhrmans(hg.):F.W.J.Schelling.Briefeund Dokumente,Bd.1,1962,S.69—71;M.Frank/G.Kurz(hg.):Materialien 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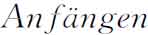 ,1973,S.110—112.
,1973,S.110—112.
[30]我们注意到当F.施莱格尔在于1799—1800年冬季号Aten-um上发表《关于诗歌的谈话》并宣布了一种新神话时,谢林立即在其1800年早春发表的System中表态,与这种浪漫派的思想划清界限。参看KA.II,S.317f;SW.III,S.629,特别是脚注。对于辨别这一思想的先在性归属问题,可参看谢林研究专家X.蒂利特的重要提示,”Schelling als Verfasser des Systemprogramms?“in:Materialien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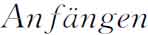 ,S.200;参看黑格尔研究专家O.珀格勒的判断,”Idealismus und neue Mythologie“,载K.R.Mandelkow主编:Die
,S.200;参看黑格尔研究专家O.珀格勒的判断,”Idealismus und neue Mythologie“,载K.R.Mandelkow主编:Die  Romantik,Bd.I,1982,S.179—204,还有他的另一篇文章”Die Entstehung von Hegels
Romantik,Bd.I,1982,S.179—204,还有他的另一篇文章”Die Entstehung von Hegel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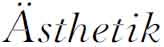 in Jena“,in:Hegel‐Studien Beiheft 20,S.257f;另外,H.戈克尔(H.Gockel)及F.施特里希(F.Strich)两人指出,除了赫尔德关于新的神话的思想(在诗歌中复活神话)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K.H.海登赖希(K.H.Heydenreichs)要求一种诗性扩展的System der
in Jena“,in:Hegel‐Studien Beiheft 20,S.257f;另外,H.戈克尔(H.Gockel)及F.施特里希(F.Strich)两人指出,除了赫尔德关于新的神话的思想(在诗歌中复活神话)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K.H.海登赖希(K.H.Heydenreichs)要求一种诗性扩展的System der 对F.施莱格尔的美学构架、对其”Studiums‐Aufsatz“和”Redeü
对F.施莱格尔的美学构架、对其”Studiums‐Aufsatz“和”Redeü die Mythologie“这两篇专文发生的影响,参看H.戈克尔著作,第75—84页。
die Mythologie“这两篇专文发生的影响,参看H.戈克尔著作,第75—84页。
[31]由F.施莱格尔所引进的关于一种文学史上的审美革命的思想,其目标直指对古代和近代的对立的一种克服,即通过在近代的教化的理论和诗歌中的实践活动促进和支持客观化的主导地位。他的”Studiums‐Aufsatz“一文是早期浪漫派文学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篇,以设想这种革命为其核心问题。Cf.Schriften zur Literatur,Rasch(hg.),S.128f.
[32]温克尔曼1766年的文章”Versuch einer Allegorie“已经以诉诸古典神话为基础,其写作的目的之一即是为诗性的想象打开一块自由领地,那里可以借助于与历史质料的联系产生出一种特有的共同图像。
[33]这里所提到的论文并未问世。谢林专家X.蒂利特把这里的宣布阐释为一个商榷的标志,与早期浪漫派关于一种新神话的诗歌实践发生商榷。
[34]Cf.A.Allwohn,1927,S.26、27f.
[35]Cf.E.Behler 1988,Studien zur Romantik und zu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S.171—195,还有之前他在1976年的《哲学年鉴》83(Philosophischen Jahrbuch 83)上面的报告,第133—183页;前面那本书的附录收入了H.C.罗宾森(H.C.Robinsons)以笔记形式流传下来的谢林1802年的PdK讲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