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在与费希特的先验哲学自然观点发生理论商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成熟的同一性体系纲要。这种哲学认为它并非只是在补充主观唯理念主义理论从而超越之,相反它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重新提出和建立被康德的批判哲学拆毁又被康德的“公设学说”一再敦促的那种形而上学。这样的形而上学是关于“绝对者”的一种学说。尽管同一性哲学体系的形态松散且未全部完成[10],但是,它包含着相当连贯的一些思考过程,这组著作和文献的相关动机之间有着鲜明的亲缘关系,本身紧密聚合在一起,在思想内容方面可以相互提示。
谢林最初宣布这个体系,即是在上面提到的Wahrer Begriff一文中,此文第一次将他与费希特的思想冲突公之于众。这篇文章突出了自然哲学对于“哲学一般表述”的形而上意义和体系意义(SW.IV,S.83—84)。1801年谢林接下来发表的重要文献Darstellung,用哲学纲要的方式提出了这个同一性哲学体系。谢林在这里借助于采纳斯宾诺莎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思想,首次为他先前已经提炼出的“作为哲学思考相互对立的两极”的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SW.IV,S.108),确定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于是此前尚未建立相互联系的两个体系,自然哲学的体系和先验哲学的体系,现在通过关于绝对者的学说已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科学整体内的两个并置部分。[11]在作为实在和观念之同一性的绝对者那里,自然和精神、以此实在和观念,都找到了它们最深层的论证。1802年问世的对话体著作《布鲁诺或关于诸事物之神性原理及自然原理:一个对话》[12](Bruno oderü das
das  und natürliche Prinzip der Dinge.Ein
und natürliche Prinzip der Dinge.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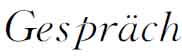 1802,SW.IV.),诉诸乔达多·布鲁诺的泛神主义,重新抓住“绝对者”之内诸对立的统一问题,突出了存在于整体内部的对立的意义。它还通过吸收新柏拉图主义,同时提供了一种对“真—美”理念的统一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现在统一地对“诸事物的神性原理和自然原理”进行界说完全是可能的。1803年的《从哲学体系做出进一步的表述》[13](Fernere Darstellungen aus dem System der Philosophie)接下来构想了“宇宙”或曰“绝对者”之整体存在的各种范式,它们同时承担着揭示人与世界之不可去除的基本关系的任务。进一步地,这些范式作为对“万有论”的最一般构想,展开在PdK的演讲系列(1802—1805年)和System 1804当中,并被提炼为精神哲学的一般结构。Studium(1802)也以相当大的篇幅处理了这个结构。直到1807年的Freiheitsschrift重新采取谢林在1804年的《哲学与宗教》[14](Philosophie und Religion)中早已设定的动向,并由此转向关于自由的哲学之前,同一性哲学的整个思想运动不间断地返回并联系其自然哲学,正如我们在谢林1806年为其自然哲学及其导论写作的两个箴言那里仍能直接看到的那样。
1802,SW.IV.),诉诸乔达多·布鲁诺的泛神主义,重新抓住“绝对者”之内诸对立的统一问题,突出了存在于整体内部的对立的意义。它还通过吸收新柏拉图主义,同时提供了一种对“真—美”理念的统一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现在统一地对“诸事物的神性原理和自然原理”进行界说完全是可能的。1803年的《从哲学体系做出进一步的表述》[13](Fernere Darstellungen aus dem System der Philosophie)接下来构想了“宇宙”或曰“绝对者”之整体存在的各种范式,它们同时承担着揭示人与世界之不可去除的基本关系的任务。进一步地,这些范式作为对“万有论”的最一般构想,展开在PdK的演讲系列(1802—1805年)和System 1804当中,并被提炼为精神哲学的一般结构。Studium(1802)也以相当大的篇幅处理了这个结构。直到1807年的Freiheitsschrift重新采取谢林在1804年的《哲学与宗教》[14](Philosophie und Religion)中早已设定的动向,并由此转向关于自由的哲学之前,同一性哲学的整个思想运动不间断地返回并联系其自然哲学,正如我们在谢林1806年为其自然哲学及其导论写作的两个箴言那里仍能直接看到的那样。
借助于批判地将自己的立脚点改换和提升到绝对理性的立脚点上,同一性哲学扬弃了费希特的绝对唯理念主义与斯宾诺莎的泛神实在论之间的对立。现在,这种哲学作为“完成了的唯理念主义”在自身中既包含实在论与唯理念主义的那种二元对立,也包含这两者的“绝对同一”(SW.VI,S.13)。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新的哲学的体系构架。新的哲学是一种“观念—实在论”,以适宜地表达“绝对者”的那种“选言式”的反思表述形式,因为作为哲学原理的“绝对者”,按照先验知识学的方式必然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完全看成观念的或完全看成实在的”(Ibid.,S.24)。按照谢林在Stu‐dium中的说法,同一性哲学体系的构架本身是按照哲学的内在类型而形成,它主要建立在三点上:
绝对无差别点[15](der absolute Indifferenzpunkt),在它那里实在世界与观念世界被洞察为一个东西;两个只是相对或观念地对立着的世界,其中之一是表述在实在东西那里的绝对世界,是实在世界的中心,其中另一是表述在观念东西那里的绝对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中心(SW.V,S.283)。
也就是说,整个同一性体系只包含“两个主要部分”,即“一个纯粹理论的或实在论的部分和一个实践的或观念论的部分”(SW.IV,S.89)。由两部分的结合得出的是一种“第三科学”,一种“客观化了的唯理念主义实在论”(Ibid.,S.86)。这种唯理念主义的实在论,谢林又称为“实在的唯理念主义”(Ibid.,S.89),它不是别的,正是艺术的体系。我们看到,谢林对整个同一性哲学的体系连续性的强调同时也在提示:位于同一性哲学体系内部的这个PdK,已不再有调和的任务。对1800年的System,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之间的一种“平行”曾经是不言而喻的,有时候这种“平行”被看作下列做法的原因——谢林将作为实存升华的艺术功能思考为结合两个对称的体系构架的“合拱石”。在先验体系那里,尽管艺术在理性的巅峰上起着反思的自我认识活动的思维结构的“合拱石”作用——自然则反对着这种反思的思维结构,把自己表述为在其合目的创造中将思考的自我统一起来的——但对进行认识活动的理性来说,存在于自然和艺术那里的同一性并不是得到论证的,它始终还只是一种提示。那么现在,站在同一性哲学的总体哲学体系的立场上,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平行关系必然已被扬弃。这种扬弃是重要的变化,标志着谢林哲学立脚点的大调整,我们决不可以忽视或错认这点。
当哲学的建构依次完成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的建设——即“从自然到自我”的方向以及“从自我到自然”的方向——之后,同一性哲学立场上的谢林现在强调,他要采取“真正的方向”,那就是“自然本身已采取的方向”(SW.IV,S.78)。面对一种世界理解活动,在谢林此时看来,两个体系间不再可能存在一种“对称”,因为我们从人类精神中永远也不可能推导出一个自然来。自然的不可扬弃的实在性本身直接涉及宇宙的唯一实体。谢林并且在Wahrer Begriff中提示,他本人这个新动向直接是诉诸亚里士多德传统的:
哲学现在返回到物理学和伦理学那种古老的(希腊)划分那里,这物理学和伦理学复通过第三部分(诗学或艺术哲学)统一起来(SW.IV,S.92)。
我们现在于是能够理解,谢林在PdK的建构开始时立即作出的提示是什么意思:艺术哲学的建构“并非在每一个可能的方向上”追随哲学的那些首要的原理,而是仅在那个“实在—观念的”考察方向上追踪这些原理的运动(SW.V,S.373)。因为这个方向通过指出其确定的研究对象这种方法,预先即规划了一种艺术哲学的基本任务。这个方向即是“更高的实在论”的方向。所谓“更高”,指它要求按照唯理念主义的存在观念而非仅仅以具体经验的尺度去把握对象。所谓“观念的实在论”则是说,其与哲学中所有其他的实在论都因此而判然有别:这一“观念的实在论”把所有的存在者都理解为进行直观活动的,同时也把自然理解为整个被理性所贯穿的。此外,自然哲学和艺术哲学之间即观念的实在论与实在的唯理念主义之间存在的“平行性”,也道出同样的一种考察方向和表述方向:自然哲学和艺术哲学都客观地表述“绝对无差别点”。如果说自然哲学是关于绝对和神性本质的“第一科学”,那么艺术哲学是关于绝对和神性本质的“第三科学”。前者是一种自然神学,后者是一种“神谱”,两者均以“绝对者”为其唯一研究对象。
下面我们考察同一性哲学的几个主导思想,它们对于阐明体系的总体关联举足轻重,只是我们在此无法追溯和检查原理展开时所有的个别情况。[16]暂时我们只能满足于,在我们的主要题目的视野中去把握它们。确切地说我们要在三个点上把握之:同一性与整体性、作为对立面之辩证统一的同一性以及“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关系。
第一,同一性与整体性。绝对同一性和绝对整体性本是作为同一性哲学原理的绝对者的谓语。这种哲学努力要衔接古典关于“万有”的思考活动,从一个唯一的“太一”(Das Eine)那里系统地推演出哲学的知识活动的整体。推演的出发点乃是绝对原理本身。这原理作为其自我设定活动的绝对主体,永远不会过渡为客体,哲学的理性之所以能够接近它,是以此为前提条件:将立脚点批判地提升到绝对理性那里。在建构中,原理是从其存在方面系统地展开:
对理性的存在来说的最高法则,以及对所有的存在[……]——因为(按照§2)没有任何事物存在于理性之外——来说的最高法则,乃是同一性的法则(SW.IV,S.116)。
“绝对者”的本质,作为先验的原理,理性只能在同一性的法则那里窥见。“绝对者”无条件地无限存在,作为这样的东西绝不会停止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将所有存在者都看成这绝对同一性,正是因为所有存在者,自在地来看无非是“太一”。这种哲学因此同时要求对诸事物的一种绝对的理性考察方式,也就是如诸事物自在存在的那样去认识它们,“就它们都是无限存在的,就它们都是绝对同一性本身而言”(Ibid.,S.120)。这是一种不断将一切事物采纳和消解于原理之中的认识方式。同一性的存在方式本身将在同一性的自我认识活动那里去洞察:同一性“仅存在于一种同一性之同一性的形式那里”(Ibid.,S.121),也就是说,“仅存在于对它的与其自身的同一性的认识活动的形式那里”(Ibid.,S.122)。为了认识自己,同一性无限地把自己同时设定为主体和客体。它的存在形式的法则在哲学上必然要以“A=A”的公式去把握。同一性在这个“A=A”的等式这里让自己作为同一个A,即那个同时把自己设定在谓语和主语的位置上的东西,重新得到认识;尽管由于这样做,它使自己表现在主体性和客体性的一种关系那里。这乃是绝对原理的本性,置身于所有的界限和对立之外,使作为未分别的同一性的自己,只能在实在与观念之间的无差别点那里去把握。然而,以此同一性与其整体性的统一同时也被揭示出来:如果主体性和客体性,确切说来,作为有区别者的绝对无差别存在于绝对同一性的存在形式那里,那么所属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形式,连带地也属于一切存在的形式。在这里,差别、原理之内的差异必然存在。只是随着差异,原理的自我认识活动的形式才现实存在。然而,这种差异仅仅存在于整体之内,确切说来,它们是从个别事物的角度看才设定下来的,此时差异是作为那种与绝对原理分离开的东西,因为同一性决不能“从与所有存在者分离的角度去思考”(Ibid.,S.125)。
绝对同一性作为这样的东西也被谢林称为“宇宙”即存在整体:在“宇宙”那里,存在的一切事物必须在其本质中洞察,必须被洞悉为一种其在整体中的“随同存在”。原理的生存形式之整体性本身表述为“个别那里的差别和整体那里的无差别”(Ibid.,S.127,脚注5)。也就是说,随着这个设定,不仅有差别本身出现,而且有作为所有的事物的普遍关联的整体性出现,它作为存在者的整体或存在者的整体的秩序,从存在上说先行于其本身所有部分。只是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这一整体性,才可以思考诸事物与整体的一种分离,就存在要在整体内把握而言。反过来说,这种分离本身仅仅建立在形式的区别性上,因为在整体性那里原初包含和同时扬弃了个别存在者的多样性,是作为它自己固有的显现。整体性在自身内统一地包含所有的差别和规定性的可能,作为原理的所有生存形式的可能。整体性无非是无所不包的同一性本身,它同时以一种本质性的和不可分的方式是“一切事物”。相反,从自然的世界观点去看的话。被看作具体东西的个别事物只是对那种在本然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否定。笔者将在本书第七章指明,谢林如何努力以一种级次说[17]思辨地去均衡自然的多样性和历史的繁多性。
谢林这里的理论努力,借助于对“绝对者”的自我展开做出理性表述而肯定性地调和同一性原理,本身联系着不同的自然哲学来源。这里,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因素与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表述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布鲁诺泛神论的自然哲学理解的影响。谢林对同一性和存在原理的整体性的思考在这里也衔接于布鲁诺,即把思考指向存在于自然内部的一种神性原理。所以,整体性对谢林意味着整个现实性体系,而对整体性的阐述是将之阐发为一种有机的“统一—万有性”。同一性原理在这种视角下不仅是活生生的,它已经等同于“创世”:它使得在自身内自然的规定性的整个多样性可能存在,使得整个有机生命可能存在,也使得诸事物的多样和个体性可能存在。
第二,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同一性原理把自己表述为对那种真正的现实性东西的存在论问题的最后解决。理性既不能单独在物质也不能单独在精神那里,既不能单独在“自我”也不能单独在“非我”那里,既不能单独在主体也不能单独在客体那里,既不能单独在思维活动也不能单独在存在那里,发现这种真正的现实存在。这种现实存在,绝对者本身,在自然哲学那里被概括为一种“万有—统一”,其按照显现方式恰恰把自己表述为原理的两种谓语。因为原理正是上面说的所有的对立面的同一,所有这些对立面在它们的二极性中实际上只是在建构“太一”。在这种总体关联中,同一性之内的二重性的意义凸显出来,同一性是通过“对立面的统一”这种辩证法表述自己。同一性本身,从其活生生的生存来看,就是这种辩证法或辩证过程,是把自己实现在运动中的统一,这统一在其“二性”那里复努力要成为第三者,它将在这第三者那里重新达到与自己的同一。[18]
绝对原理的那种起初尚是纯观念性的整体性那里,包含着一种实在化的行动,它通过对立面统一的法则把自己设定在这种整体性的观念可分别的规定性中,把自己实在化在这些规定性中。借助于这一法则,整体性中尚未分离地包含着的诸规定性升华为走向整体性的那些相互对立的因素。这个辩证法辩证过程的作用,使一种三分的现实性展开:原理从自己的统一性中,作为一种“二性”的结果出现,以便重新返回到作为目标的原初同一。以此同时解释了世界的统一:绝对者必须走出其必然性,创造一无限的宇宙,以便在其中展开自己的整个自我。借助于对立面统一的法则,原初的统一上升为诸事物的创生。原理现在从一般生存过渡到其多样性和无限规定性。由此创造出来的第三者是一种无差别(Indifferenz)[19],对立设定的两极在它那里相互接触,对立面如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观念与实在,复成为不可区分的和一体的。在无差别这里,对立面东西的存在原理返回它自己。谢林在对原理的活生生生存的同一性哲学阐述中,完成了对绝对同一性的肯定性表象。绝对原理的现实存在的原因被引回到它自己那里,通过它的自我设定行动去解释。这样,原理的纯粹本质不会由于这种“走出自身的活动”而变得不纯粹。进一步地,在绝对者内部的设定统一与差异的对立,复被阐发为仅以“关系的方式”发生的(SW.IV,S.237),又是仅发生在其“主体—客体化活动”那里的。于是,即使通过在这个运动内的“变成有限的活动”和“变成客观的活动”,纯粹观念性的原理也绝不允许自己像斯宾诺莎的“实体”那样丢失在客体中,而是胜利地重新上升到整体性的一个更高级次上,在这整个必然继续行进的运动中始终保持为主体,始终具有其所有的上升活动。在原理的这个自我设定活动中,存在着世界、生命的肯定性起源,从结果上说,也存在着所有的存在者的根据。
同一性哲学对对立面的辩证统一的这种视角,特别是它这个深刻见解——对立面的肯定意义同时是整个辩证活动的做统一活动的环节的意义,可以看作是这种具有“绝对连续性”的实在的唯理念主义的一个特征。这一哲学不断地将对立面东西联系到其统一的总体关联那里。于是,出现在“两极”那里的矛盾对立现在一方面被把握为原初统一性的否定性一极,因原初统一性被这矛盾对立所扬弃,另一方面又被看作辩证过程的一个创造性环节,因为在这矛盾对立那里同时又出现朝向同一性的一种奋争。在此,矛盾对立服务于原理一般生存的肯定活动,如果说每一种向着同一性的奋争都以这种矛盾对立为条件,如果说主体在每个层面上只能借助于一种现实地设定的矛盾对立提升到其真正本质那里,只能以这种方式重新企及作为“无限者”的自己。也就是说,不存在矛盾对立的话,也就不存在生命而只能存在绝对的静止。因为,绝对统一性仅在为自己设定一种矛盾对立,一种阻碍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矛盾对立不仅标志着辩证活动的中间站,因为“它们在绝对之内将停止作为矛盾对立存在”(SW.V,S.470)。矛盾对立—随之也设定了发生一种必然的继续行进的原因——即使在其所有的界限和所有的否定性中,仍构成为统一性显现的必要前提和条件。这个辩证过程也贯穿着整个同一性哲学。所以说,无论是建构唯理念主义和实在论不同的科学体系原理,还是思考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的对立,对现实的矛盾对立的展开都是重点。最典范的是在自然哲学对那种自我设定,把自己创生在其所有规定性那里的主体的历史的展开那里,是在对一个精神在艺术诸形式的风格和所有多样性的二重性那里的贯穿的处理。在对矛盾对立的所有这些研究那里,所寻找的恰恰都是创造着的原理的构成活动的连续性。
第三,“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关系。为了解释宇宙中区别性的现实产生这个问题,同一性哲学也从自身中发展出关于“无限者”与“有限者”之关系学说。[20]不论在哲学一般还是在艺术哲学的更深刻的考察那里,可以说这个关系都普遍适用。
实际上笔者在这里特别关心的是,同一性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自身内包含一种“绝对美学”,而这种美学也即艺术哲学在自身内保持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视野,在前者和后者当中都统一着超感性和感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对于作为关于“太一”的哲学的同一性哲学,艺术哲学只是它在一个更高直观层面上的重述(Ibid.,S.363)。它在理论上决没有期待从感性到超感性的一种提升,从非审美到审美的一种上升。在目前我们的谢林研究还相当初步和基础的情况下,强调这一事实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同一性哲学并不思考这种提升,而是转而集中思考“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内在共存关系,以便最终将其揭示为宇宙的生命公式。这是一种只能在绝对原理的原初统一之内去推导的关系。
从“绝对理性”的立场——它在这里是哲学考察的出发点——出发,只能这样去考察存在的一切:“如它们自在地”存在的那样去考察它们(SW.IV,S.119)。所以同一性哲学不承认任何“自在地去看是有限的”东西的存在(Ibid.)。对这种哲学来说,有限东西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按照存在本身说,并没有任何东西产生出来”(Ibid.)。通过将“有限者”与“无限者”关系存在论地引回到“有限的生存与无限者或神的关系”那里(SW.VII,S.189),同一性哲学在这种总体关联中同样地统一了从“无限者”到“有限者”的一种直接过渡。然而,必须注意,它并不是在传统“流射说”的意义上表述一种连续性表象,而是直接在“无限者”的概念那里认识和理解有限者。也就是说,这“无限者”的概念现在已经同一性哲学重新处理,因为许许多多重要的理性观点与它密切相关,比如生命的现场化的诸种条件以及以一种改变的形式对世界上的弊病和道德上的恶的起源发起的种种提问,等等。
“无限者”的概念在谢林这里,现在是通过对作为原理的绝对者的这同一个概念,通过神的自我肯定活动来定义:“直接从神的理念得出了无限者”(SW.V,S.375)。而且以一种永恒的方式,作为神的自我肯定活动的无限性。相反,“有限者”只是借助于其在“无限者”那里的“共在”或“随同存在”才存在。这“有限者”不可能与“无限者”分割开来存在,因此只是存在于“无限者”之内,或者说只能在它与“无限者”的关系中去思考。“无限者”与“有限者”,这两者的存在论的关系只能辩证地作为观念的突出出来,因为“有限者”本身只是一种存在关系,“无限者”则直接地、无需任何关系地仅凭借其本质而存在。据此,“无限者”是那种按照其概念是“无限者”的东西,“有限者”亦是那种按照其概念是“有限者”的东西。两者只是在观念上相对而设立,实在地却是一体的。但是,差别在这里却有一种存在论上的意义:如果“无限者”与“有限者”按照概念确实永恒地有着差别,那么可以推知,在此种关系中“有限者”永远不会停止在观念上是有限的。所以,在宇宙中同样地又存在着所有的形式差异,即使这些形式在统一体那里原初是尚未区分的。就“差别”这样地包含在“无差别”中而言,每一种“有限者”都可以从统一体那里为自己取得一种自己的生命,都可能观念地过渡到一种有差别的实存中。这对艺术直观也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艺术直观必须在自己那里保有其固有的“双重观点”:一方面是不断地在“有限者”与“无限者”的关系中看“有限者”,也即不断地在“无限者”那里消解地看“有限者”,为了以这种方式最终能够将“有限者”认识为“无限者”的一种“这样地存在”,另一方面,“无限者”同时又在这个“有限者”那里,在这个“有限者”的全部可理解性那里得到直观。因此,即使在哲学美学的立场上看,谢林对“有限者”与“无限者”在整个宇宙中那种不可扬弃、不可解脱关系的阐发已经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功绩,它服务于同一性哲学和艺术哲学的最终关怀:探究“人与其世界的基本关系”(SW.VI,S.74—75),以此为理性打开一种机会,重新去赢得其与存在整体的统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