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殖民时代的创造力和哀悼之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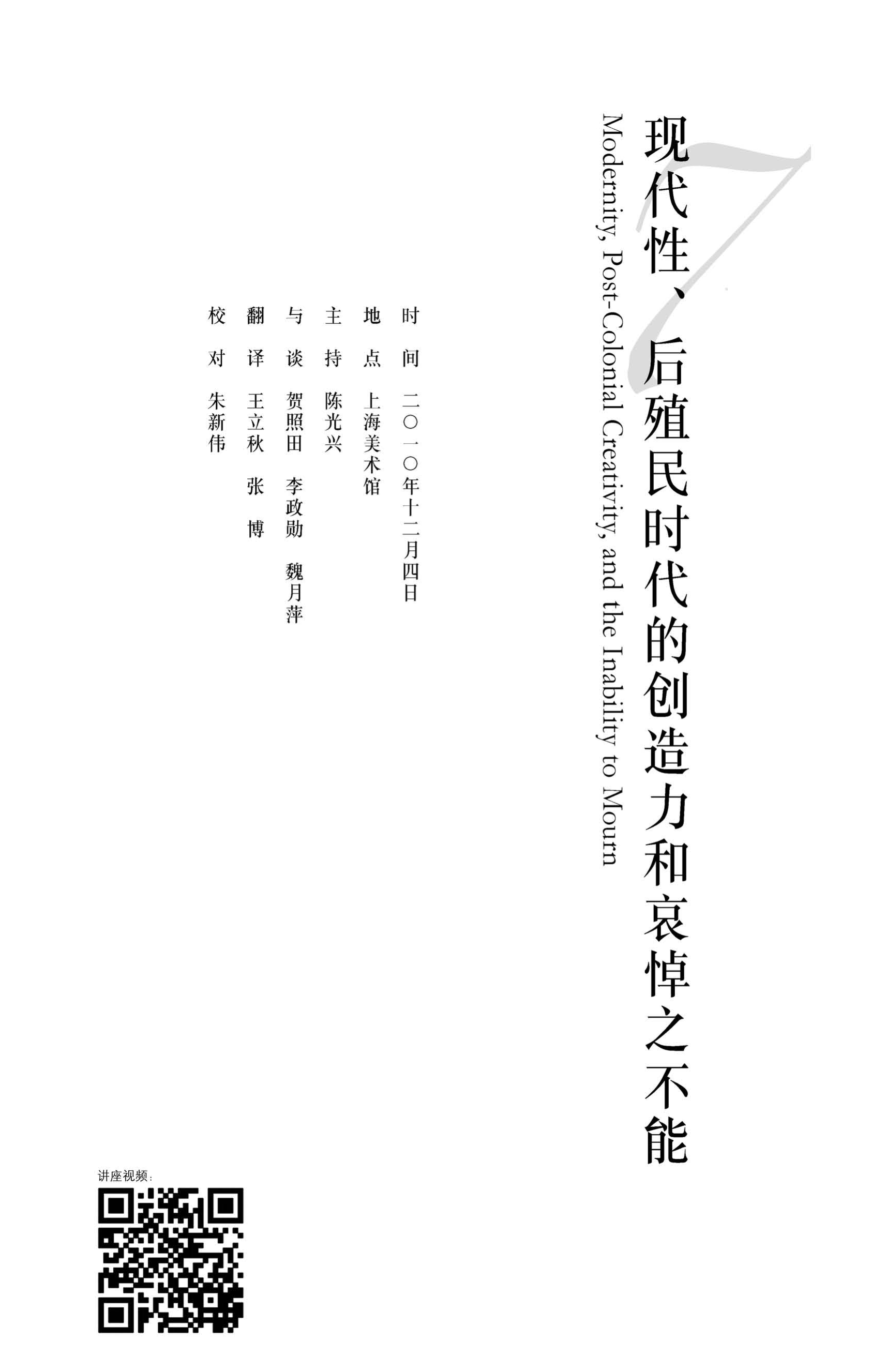
在帝王的生活中,征服别人的土地而使版图不断扩大,除了带来骄傲之外,跟着又会感觉寂寞而又松弛,因为觉悟到不久便会放弃认识和了解新领土的念头。黄昏来临,雨后的空气里有大象的气味,炉子里的檀香木灰烬渐冷,画在地球平面上的山脉和河流,因一阵晕眩而在懒散的曲线上颤动,报告敌人溃败的军书给卷起了,藉藉无闻的君主愿意岁岁进贡金银、皮革和玳瑁的求和书给打开了封蜡,这时候便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压下来。我们这时候在绝望中发觉,我们一直视为珍奇无比的这个帝国,只是一个无止境的不成形状的废墟,腐败的坏疽已经扩散到非我们的权杖所能医治的程度,而征服敌国的胜利,反而使我们继承了它们深远的祸根。[1]
在亚洲和非洲社会的政治文化中,殖民主义协助建立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2]由此,传统被赋予了两种含义。第一种,传统即现代性的反面,它对理性和民主的精神总是怀有敌意,而且保守、刻板,对新知识后知后觉。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力主本土民众摆脱偏见和仇恨,向以前的统治者和现在的一小撮精英学习理性、灵活性和宽容等美好品质。这些怀着传教激情的人同时扮演着原告、证人、陪审员和法官的四重角色。思想更为深邃的社会思想家和研究者可能不认同传统的这种含义,但它实际上支配着南半球的政治文化。
然而,此种观点不是空洞、愚笨的政府官员或目不识丁的老百姓的专利。在过去两百年间,一些非常杰出的思想家——从詹姆斯·穆勒到尼拉德·C.乔荼利(Nirad C. Chaudhuri)——都曾使用过传统的这个意义。更有意思的是,在使用传统的负面定义时(传统即现代性的反面),亚洲和非洲一些最优秀的头脑用传统的观念来批判当代,重新想像、驯服现代性,使现代性本土化,构建一种替代性愿景——借鉴启蒙价值但又不受其支配的美好社会。这种替代性想像不受传统的控制;传统的观念只是帮助我们深入自我,探求超越时代限制的资源。最近几十年间,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和布吕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西方学者的研究计划便践行了这种想法。在南亚,这项计划一度主要以甘地和泰戈尔的世界观为代表,但如今,它也在许多从纨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到兹奥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克劳德·阿瓦雷斯(Claude Alvares)到塔里克·巴努里(Tariq Banuri)的活动家与学者那里以离散的、碎片化的形式幸存了下来。
在许多后殖民社会和穆斯林社会中,传统还有第二种含义。根据其定义,“真正的”传统,可以适应现代性,并且事实上也的确适应了现代性,它只需防止被坏人歪曲或误用。比如说,在印度,传统对许多人来说就是印度的正典文本。如果你熟知《奥义书》《吠陀经》《圣经》或《古兰经》,并通晓梵文或阿拉伯语,那么在现代印度,你也就获得了谈论传统的权威,你可以宣称,这些文本与18世纪以后的欧洲所珍视的价值观毫无冲突之处。阿玛蒂亚·森显然同情这种观点。他说自己能阅读梵文经典的一手资料,不必盲从印度教沙文主义者。“底层”文化总是容易使精英难堪,因为它看起来非理性、无意义、混乱、不可控制,没法用它来在全球中产阶级文化中捍卫自尊。因此,根据第二种含义谈论传统的那些人中,很大一部分从未严肃看待本土社群的传统,而就我们所知,这些传统如那些经典文本一样古老,例如桑塔尔族(Santhal)的治疗学说,玛利亚·龚德(Maria Gond)的农学,喀拉拉邦的数学理论,以及拉贾斯坦邦的无数游牧部落的复杂而精致的音乐传统。虽说时代不同了,大多数现代印度人,除却人类学家、民俗学者或民间宗教学的学生,谈论传统时一般都不会想到这些东西。他们重新阐释或批判性地重估传统,为现代性创造空间,尤其是发展、世俗主义和进步等观念,而这些都仍然局限在经典文本的范围内。他们希望印度变得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必须服从现代性的制约。政治社会学家D.L.西斯(D.L.Sheth)讲述了一个女学生的故事,这个女生说她的父亲非常自由主义,允许她和任何人结婚——无论是黑皮肤的非洲人或是蓝眼睛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这个人出自同一种姓阶层。
这种思维方式常常被用来抨击种族沙文主义者和宗教极端主义者的传统观,因此,我无意对其太过严苛,无论他们多么狭隘或偏颇。数以千计的人采纳陈旧的、英国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忙于“从几年前的学术涂鸦中提取他们的愤怒”,他们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以及两者共同的敌人——宗教民族主义或种族民族主义者——相互缠斗。一个人若是信了这些斗士的话语,受典型的意识形态诱导,那么,很容易就会投入西化的城市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已经逐渐主宰了我们对南方世界的理解。
不管怎么说,我在此关注的既不是印度的传统也不是它的贬损者。我是要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南方世界的现代主义和“进步”的观念几乎没什么创造力,除了以视觉艺术、诗歌等文学形式,以及音乐,也即只有在那些按定义来说低层次的、相对不受意识形态蹂躏的那些部分,它才具有创造力。现代性及其启蒙的视野,无法释放多数人的创造力,尤其是社会知识方面的创造力。这有许多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已有相关的深入研究,那些悲叹本土社会学和政治学分析的重复模仿和崇洋媚外的人有时也会对此进行直接研究,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要治愈现代性的顽疾,必须施以更大剂量的现代性方案。很少有人严肃地探究社会和政治思想以及社会科学中,受到昂贵教育的、西化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思想贫瘠的原因——他们操纵现代世界竟如此自如、自信。我推想,这种探索的失败并非偶然,其背后有某种意识形态驱使的厌恶感,使得人们不愿意去面对它。下面我将详细讨论。
南方世界的现代性在社会知识领域之所以贫乏,是因为它一直以来缺乏与伟大的现代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密切相关的因素:由现代性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导致的丧失感(sense of loss)。在艺术领域,这种丧失感可以轻而易举地化入创造性作品中;在组织化的思想中,它必须得到认可并被纳入理论图式之中。这种认可变得越来越困难,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许多现代人的这样一个信念,即,在决策的时候,如果得益超过了损失,那么,我们就必须欢庆得益而遗忘损失。对丧失之物念念不忘是一种任性的、伤感的怀想。其次,是因为一种广泛的担忧:纵容历史在“传统”的伪装下攻击现在,这乃是一种危险的娱乐,容易招致复兴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利用。
这两种立场都没有根除传统,只是把传统赶入了地下。我在其他地方曾论述过,莫利奈·森(Mrinal Sen),这位印度的天才电影人极具都市和现代气息,却极力否认他在孟加拉的福里德布尔县的童年记忆,称其是子虚乌有的怀旧。然而,在最具创造力的时刻,他却不得不向这些记忆回归,与来自过去的幽灵争斗,并最终哀悼他抛弃的那个“家园”。森是个特例,因为他是创造力很强的艺术家,而非学者。印度极少有严肃的现代思想家会自觉地这么做。在我所知的范围内,吉林德拉赛克哈·博思(Girindrasekhar Bose)算是一个。他是非西方世界的第一位心理分析师,力图在印度传统中建立精神分析,而不是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印度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他比森更有创造力。但他们对此并无自觉意识。社会科学必须探求内部连贯性,但在学术规范的体制中,几乎不可能像艺术家或电影制作人一样去哀悼前现代或非现代的消逝或失败,例如萨耶吉特·雷伊(Satyajit Ray)这样的电影制作人,尽管他是一名强硬的现代主义者,至少可以在《音乐室》(Jalsaghar)和《不速之客》(Agantuk)等作品中作出努力。[3]博思在他的孟加拉语写作中保留了自我的私密部分。对他的外国读者来说,他看上去较为传统、呆板,或者还可以说,思想贫瘠。
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性自有其原因。现代性在大部分南方世界以零散的形式存在,被各种传统所包围,这些传统是活生生的、充满生气的,偶尔衰落,但随时可能勃兴。结果,现代性看起来就像一个需要保护和吹捧的被困之地。许多人至今以为现代性是政治异议者的标志,虽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与权势、财富密切相关。现代亚洲人和非洲人都是其受益者,他们不会主动检验现实,承认自己属于胜利的一方,因为那只会让自己难堪,或者让自己思维混乱。他们宁愿活在自恋的世界里,幻想着现代性被围攻的状况,把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少数族裔恐惧症当作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骚动。
多年前,我读到了阿多诺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违背本阶级的利益,那这个人就更为接近真理。阿多诺不是在鼓吹“去阶级化”。许多激进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都宣称自己是“去阶级化”的革命先锋。他们总是把本土社群当作愚蠢的受害者,等待他们用思想和革命活动加以解救。我的看法是,阿多诺在设想某种精神分析治疗式的国家模式,这种类型的国家会把那些心怀不满的人降为二等公民,并宣布他们缺乏理解和表述“真理”、真情实感的能力。在这样一个国家,现代性教条的反对者不是作为罪犯被惩治,而是被当作某种精神官能症患者或无生活能力的人接受治疗。敏锐的思想家注意到了此类以专家意见、科学理性为名的宰制,他们开始思考“丧失”的概念。尼采对于“丧失”有着极为深刻和痛苦的感受,在他所构建的批判理论中,现代性的特征是信仰和神性的丧失。尼采的理论为当代世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提供了新的总体性。在他看来,现代性似乎不可避免,但生命不再能够安居于超越死亡的信仰之中;生命不得不面对更为不安定的死亡观念。甚至像马克斯·韦伯这样推崇人类理性的学者,也怀有某种忧郁与怀疑。更不用说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们对都市——工业主义世界观的批判也伴随着丧失感。
更显著的例子是两位启蒙运动之子:卡尔·马克思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马克思口头上不愿承认怀有任何丧失感,但他论述原始共产主义的方式,让人不禁想到某种有缺陷的、宿命论的前现代田园乌托邦想像。在征服者的驱动下,被殖民化的社会进入现代性的阶段,以为这是进入“成熟”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丧失感便是这种世界观所付出的代价(原因也许是,历史作为不可动摇的进化过程,逼迫人们选择血淋淋的资本主义,放弃原始共产主义)。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更为严肃地思考这种隐含的丧失感,恩斯特·布洛赫首次将其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加以讨论,李约瑟在这一点上则不那么明显。
弗洛伊德也认为,现代性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各种压抑、侮辱和理性化造成了文明内部的不满情绪。形式上的自由,牺牲了个人的本能自我,压抑、隔绝自我,或抛弃神话所激发的生命活力,遁入狭隘的个人想像。我们害怕自我被驱逐,小心翼翼地维持自己的心理活力,时常以心理疾病的形式打破心灵的禁锢,而这可遇不可得,并不受人欢迎。所有的神经官能症都可以解读为进步和文明观念的自我牺牲。马尔库塞等人着重讨论多形性倒错(polymorphous perverse)和压抑的双重性,也是基于同样的出发点。
这种剧烈而痛苦的丧失感在南方世界的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当中无迹可寻。有一个原因是,许多人还生活在影响深远、颇为自信的前现代或非现代的社会体制中。面对现代性的威胁,这些体制拒绝屈服。更重要的是,许多研究者将现代主义作为武器,反击家庭或外界的旧威权。任何与前现代、后现代或非现代的妥协,都被视为理论上的俄狄浦斯情结而遭到拒斥。这些研究者意志坚定,不容置疑。
在他们看来,启蒙主义世界观所塑造的现代性是慈爱的上帝。他们凭借对“上帝”的虔诚之心而实现了某种归属感,以弥补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舍弃的传统社群的牵绊。在现代性尚未占据霸权地位的社会中,现代性只属于少部分人的意识,现代人的社群想像为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提供了某种心理安全感,他们可以充当先驱者和设计者的角色,用他们自身的心理来改进或重构底层民众的心理。这类设计工程对当今的全球秩序有好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希望把本土社群定义为单纯的穷人或被剥削者,仿佛本土社群除此以外便无法定义自身,仿佛这些人群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文化或知识可供对抗贫穷与剥削。进步主义的胜利者姿态和狂热情绪已经开始对底层民众进行公然抨击。
也不乏对现代性表示反对的声音。实际上,批评者的在场恰恰是现代性的价值之一。经历了奥斯威辛、广岛与古拉格事件之后,现代性几乎一直饱受批评。但这类批评必须出自现代主义者的内部阵营。如果是来自传统的批评,那这批评就会被视为危险或愚蠢的意见。传统只能低声下气地请求现代性留给它一片生存的空间。
即便能够共存,传统也必须在一套既定的严格规则中立足。根据南方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意识形态,传统几乎等同于“古典思想”或老古董,地位十分被动。具有现代性因素的传统文化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来源之一。吠檀多与量子物理、禅宗与心理治疗被和谐地并置在了一起,成为畅销书的主题。没人会把两者颠倒过来,把吠檀多和禅宗作为量子物理和心理治疗的合法性来源。同时,南方世界为数不少的现存传统像是神神道道的玩意儿。不过,传统已经习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这些批评比现代科学、体制、政治和社会思想遭受的批评更为苛刻。不但现代主义者要批评传统,多元化的传统和生活习俗互相之间也会产生矛盾。例如,南亚的成百上千种传统习俗就一直在互相辩论、争吵和批评。不同宗教、教派和哲学流派——就像各种治疗体系、农学和技艺传统一样——一直以来都在进行对话,而那些围绕所谓文明对话高谈阔论的根本不知道这些。批评还来自生命的互相交流,日常经验会否定、支持、忽略或避开某些特定的传统。
如今,这些批评显得远远不足,还需要某些主动的推力。我使用“批判性的传统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理论框架。在这个频繁使用“民主”一词来掩盖对民主的恐惧的时代,有些人通过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偏见来抵制传统进入公共生活。我使用这个词主要是为了突出新、老传统内部的日常生活的尊严与智性。我甚至曾故意用“传统主义”一词来反击所谓的“批判主义现代性”,后者也许与亚非世界具有某种关联性,但与启蒙运动的内部批判者或“逆子”也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不过,我渐渐怀疑,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富有活力的社会、政治和艺术创造活动来说,显得过于停留在认知层面。也许,我们在理智可控的范围内可以更好地接近那个本能的、和睦的自我。这就关系到丧失感。丧失感为那些善于调动现代性资源的人提供了力量。在某种层面上,创造力是在做修补的工作,补偿或消除我们内心的摧毁力。那些心甘情愿投入日益蔓延的历史垃圾场的人,对于丧失感的相关范畴会尤为敏感。
在我看来,现代性伴随而来的丧失感是对当前盛行的进步主义观念的一种纠正或反制。这种进步主义观念深植于19世纪的“好社会”、“好生活”的意识形态,以及试图超越历史、避免千禧年主义的未来想像。当今的批判性传统主义的基层理论从中汲取了力量。这种乐观和自信的精神不是去轻易地拥抱那个必然的、莱布尼兹式的、所有可能选项中的最优化世界。我所说的未来想像牵涉到丧失感的经验,即弗洛伊德的世界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重感的结合。
对于未来的关注和参与责任感有助于我们加强传统主义的批判性,加强失败者、边缘人的传统生活的政治地位。坚持对于好社会的多元想像,乃是事关未来的事业。对于未来的参与感可能会时断时续,因为它不断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摇摆。人们在摸索传统的同时,也在与未来打交道。这就像处理现代性命题时免不了要面对过去一样。未来是乌托邦也好,反乌托邦也好,它似乎不受我们控制,但如果我们干预当下,那就会在不经意间重建过去与未来。
这使得此项事业在两方面都呈现出开放性,因为文化和传统的概念已经变得含混而可塑。但这种含混性和可塑性来自其本身。如果人类学家与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能够接受“文化”一词各种不同的含义——就像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教科书第一章里面写的那样,那么,颂扬失败者世界观的那些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论文化和传统,并主张失败者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的世界观有其自身的价值。我不是想为被压迫者描述他们的痛苦和抵抗。他们有能力为自己说话。我只是为自己以及知识结构和我差不多的人,打开另一个可能的知识世界。对于另类世界的追寻,可以打破既有知识世界的神圣性和完美性的假象,后者以真理和社会道德的名义施行着知识霸权。就算我试图开拓政治空间的知识世界出现错误——但愿不是如此——我也不会心碎。这种探索和嬉戏本身便可以让我们体会含混性带来的宽容精神,我们由此可以自信地面对开放的自我。关于创造力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业已证明,探索和嬉戏是人类创造力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4]
我不是要把各种文化纳入耳熟能详的话语体系,而是试图探讨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在南方世界的成果寥寥无几,为什么少数优秀成果无法改变模仿的、自卑的、重复的社会科学现状。模仿的泛滥不可能通过对其他文化和知识系统的“透明”描述得到改善。实际上,这种透明性对于许多小型社群和文化来说有着致命危害,恰恰是文化交流的缺失和抗拒才保证了它们的生存。已故的文学理论家纳加拉吉(D.R. Nagaraj)曾讨论过许多“如嬉戏一般无法沟通”的传统世界观、认识论、生活方式和无法用理论概括的实践。
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丧失感的缺失并不总是会扼杀创造力,因为艺术的眼光不那么社会化,艺术创造者没那么理论化或意识形态化。丧失感不会顾忌艺术家和写作者的感受,它会闯入他们的作品,甚至在较为拙劣的作品中亦是如此。我将以最近流行的一部孟买电影为例。这部电影延续了嘉年华式的反电影,民众的心态取代了电影制作者的内心欲求。
2002年前后,布汗萨里(Sanjay Leela Bhansali)推出了大片《德夫达斯》[5]。这部电影的故事来自查特帕德耶(Sarat chandra Chattopadhyay)用孟加拉语写作的流行小说。小说《德夫达斯》被翻拍过将近20次,有各种语言版本。另外,(沉迷于爱恋、酒精、自我放纵的)小说主人公德夫达奔向城市,却一无所获,最后又徒劳地返回乡村。印度通俗电影中常常出现这类形象。电影批评家达斯古普塔(Chidananda Dasgupta)对此颇为不满。原著者虽然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但此部小说却并非经典。查特帕德耶创作这部小说时还不到20岁,没想到它会那么受欢迎。布汗萨里翻拍《德夫达斯》耗资巨大,本来就没指望收回成本。知名导演拉吉米(Kalpana Lajmi)在报纸专栏上批评德夫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不可能在当代印度获得观众的共鸣。票房证明那些批评者说错了。自从伯斯(Nitin Bose)1930年代首度将其翻拍成默片起,《德夫达斯》就成了印度观众热捧的作品,至今热映不衰。
我猜测,《德夫达斯》之类的电影之所以能感动印度观众,主要是,通过强烈的丧失感,城市的匿名性、非人性和孤独的个人主义愈演愈烈,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谈论丧失之感。《德夫达斯》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它没有遵从既定的现代美学规范。
一般认为,印度的电影与板球生态在心理上非常相近。这种相似性给我们以启发。传统的板球动作规矩、姿势优雅,一些板球评论家因此称之为“前工业时代”的价值观。来自19世纪的传统板球是对21世纪规则系统的批判。印度板球和通俗电影中的嘉年华式的喧嚣与俗套属于生活中的神话因素,人们表面上接受启蒙价值观,却在细微处加以反抗。观众探求那已经消逝的过去,为未来预留一片新的空间,在自我意识的边缘生存下去。
最后,我想提一下知识的政治文化本质。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丧失感的问题。当今世界已经被出卖给了进步主义,一切丧失感都已被定义为贻害无穷的怀旧,只有一些环保主义者试图扳住进步的齿轮,重新赋予自然以神圣性,在这个害怕保守主义的世界引入“保护”的观念。另外,还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则试图消除“生产”(production)一词的迷惑性,强调“生育”[6]的神圣性。
我前面已经说过,大概从卢梭开始,一些西方思想家、艺术家和作家将“丧失”放置于复古主义的概念。在他们看来,田园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是理性尚未统治世界以前的乌托邦,而复古主义的思想将创造新的未来路径。南方世界没必要像绵羊一样顺从全球秩序统治者对他们的解读;南方世界肯定能够建立自己的标准,重估西方思想。西方世界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南方世界应有适合本地的文化。南方世界或许可以主张,所谓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完全站得住脚的、现实主义的策略,在炎热而潮湿的热带世界反击定规。这一策略逆转了城市——工业主义的社会进化路径想像,拒绝把田园当作应当淘汰的文明初阶。浪漫主义和文化怀旧,包括所谓重新发现的传统,也许可以用来解读亚非世界的历史,挖掘潜力、颠覆线性历史观,拓宽美好社会的想像,为那些被迫复制欧美发展路径的社会提供开放的思想空间。
也许,这就是许多非西方思想家重视田园的原因,印度的甘地和泰戈尔便是明显的例子。甘地和晚期的泰戈尔看上去是在嗟叹过去,实际上是在思考19世纪欧洲所塑造的钢铁架构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影响到南方世界的未来。甘地不是出生在印度农村,这并非巧合。他关心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他想要寻找一个思考未来的基点。或许,他奋力抗争的对象正是我所说的文化上的某种神经官能症,这种激烈的神经官能症在亚洲和非洲被称为“祖先嫉恨”(ancestor envy),人们可悲地希望转而与欧洲的过去发生联系。亚洲和非洲大陆试图与合法的过去勾连起来,就像欧洲回到其海伦时代,而不会招致复古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批评一样。
【注释】
[1]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trans. by W. Weaver, London, Vintage, 1997, p.5. (中译文引自《隐形的城市》,陈实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译者注)
[2]This essay has grown out of an unpublished keynote lecture at the conference on “Does Culture Make a Differenc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rganised by the Max Mueller Bhavan, Calcutta, on 22-24 April 2004, and later, given as a public lecture at GTZ, Berlin, on 14 July 2004.
[3]Ashis Nandy, “Satyajit Ray’s India:Cinema,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Italo Spinelli(Ed.), Indian Summer:Films, Filmmakers and Stars Between Ray and Bollywood, Locarno:Edizioni Olivares, 2002, pp.24——33.
[4]更多例子,参见 Frank Barron, Creativity and Personal Freedom,Princeton, NJ:Van Nostrand. 1968; and Rollo May, The Courage to Create, New York:Norton, 1994。
[5]Devdas,又译作《宝莱坞生死恋》。——译者注
[6]reproduction,也有“再生产”的含义。——译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