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的存在论维度
本书在第二部分要用专题处理的方式批判地考察谢林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艺术哲学的核心思想。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按照分期顺序去整理谢林本人的思想发展脉络。在全书绪论中我已提到,探讨谢林1802年至1805年间的耶拿维尔茨堡系列讲座《艺术哲学》[1](Philosophie der Kunst)中的核心思想是本书的另一个工作重点。这首先是因为,PdK这整个艺术哲学纲要代表了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的整体性努力,即彻底贯彻康德先验哲学的体系要求,在哲学美学中对先验知识活动进行跨越,最终实现一种“绝对美学”;其次,它所提供的“哲学神话学”标志着早期德国唯理念论哲学美学的一个重要奠基工作;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题目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同一性哲学时期的PdK及其整个问题集合,迄今为止在国内外的谢林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处理,相反,由于当代美学的新导向,它即使在德国学界也基本属于一个被忽视的题目,与其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探究个中原因,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发现,证明这种忽视是由于各式各样的误解、遮蔽和误读引起的。首先可以肯定,遭受误解这种情况与晚期谢林本人对PdK书稿的消极态度不无关系。德国学界很清楚这个事实,即谢林在其同一性哲学阶段之后告别了艺术,进入其“否定哲学”的理论总结。而晚年的谢林进行自我回顾时,对他本人早期所持的“基督教的艺术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而这个观点正是在PdK中得到重点阐发的观点之一。这些做法当然会对PdK的影响史发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另外谢林在世时没有发表PdK的全稿,只发表了它的“一般部分”,他也不主张编辑者把PdK全书收入他的全集。这些做法都很容易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随着早期浪漫派发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审美革命”的黯然收场,谢林本人也从他的浪漫主义艺术狂热中清醒过来。实际上,谢林研究者中因此认为谢林的艺术哲学属于“审美搁浅”的大有人在,典型的代表就是H.桑德库勒(H.Sandkühler)。[2]
但这种看法却是一种很典型的误解。从清理问题史的结果来看,可以认为,晚期谢林的这些做法确实与其对早期德国浪漫派的批评态度和理论分歧有关。然而这并不等于说PdK中的思想能够归纳到属于早期浪漫派立场上的主体性审美理论的名目下,这是我们特别要厘清的。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尽管早期唯理念主义与早期浪漫派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和相互的思想影响,青年谢林却并非早期浪漫派的哲学代表,而恰恰是早期唯理念主义的理论代表。而耶拿时期的谢林与浪漫派小组的关系充满张力和矛盾,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在与早期浪漫派的思想关联中把谢林的PdK划归早期浪漫派的“审美革命”的范畴内,认为它是随早期浪漫派的那种“艺术崇拜”的思想兴起而兴起,随其衰落而衰落,甚至忽视其整体论核心,可说将导致严重的理解错误。
实际上,谢林在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这部PdK的思想探索,标志着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乃至近代意识内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向,无论对美学还是对思想史,都有建设性的意义。特别是其中的哲学神话学纲要,因为PdK的核心正是这个哲学神话学。而学界包括德语世界的谢林研究对它的理论发掘迄今阙如,其维度没有被全面打开,这种情况,应该说主要是种种来自外部的误解、遮蔽和干扰造成的,典型的就是将PdK判断为上面所说的早期浪漫派意义上的“审美的”举措而对之不予重视。在这样的理解角度中,PdK及其全部理论尝试都被看作极端的、草草收场的“审美主义”的理论试验,被误解为没有价值的理论搁浅。
与此相反,笔者在本书这部分要完成一个任务,即借助于文本研究证实和揭示PdK的核心是一种建设性的存在论神话学。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笔者孤立的个人意见。B.巴尔特(B.Barth)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谢林PdK研究专著,带动了德语世界中谢林研究对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和探讨,在导言中他已经附带地提到,谢林PdK这部著作的重点应该是其中的神话学。[3]但巴尔特本人的研究兴趣是想象力或曰创造构成力之扩展理性能力的问题,也即谢林的艺术哲学究竟怎样在理性能力建构这方面接续康德KdU中的工作,所以他的这个PdK研究完全没有涉及此一哲学神话学问题。之后的谢林研究和讨论继续搁置这个问题,直至2006年,德国哲学界还没有出现一部专著,对谢林PdK中这个神话学纲要作出综合研究和全面探讨。如果考虑到谢林的全部艺术哲学思想对整个德国唯理念主义历史的分量,以及它透过其在先验唯理念主义体系和同一性哲学体系中的理论形态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艺术运动和其同时代人产生的重大影响,再考虑到德国学界古典哲学研究队伍阵容之强大,考虑到谢林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已重新成为一门“显学”,那么PdK的核心,一种哲学神话学竟长期未进入当代哲学美学的讨论视野,种种讨论都没有进入这个问题,反而一直以来在遮蔽和忘却这个问题,实在很能说明问题。
笔者在此指的并不是谢林PdK中的这个神话学纲要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的注意。问题恰恰是谢林的这个思想贡献在哲学史研究那里不断受到误解和漠视。举例来说,我们稍作文献披检即不难了解,马堡的康德研究者阿道夫·阿尔沃恩(Adolf Allwohn)早在1927年的专著中已对PdK中的这个纲要做了归类研究。他发现在谢林不同时期的神话学思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连续性”。据此他把谢林的神话学研究划分为“早期的”、“审美的”和“宗教神话学构想的”三个阶段;将PdK中的相关处理和思考归入谢林的“审美的唯理念主义阶段”,相应地把他同一性哲学中艺术哲学的神话学定义为“审美的神话学尝试”[4]。
阿尔沃恩所谓谢林的“审美的唯理念主义阶段”,指的是从1797年到1806年这段时间。我们知道这个长约十年的时间段正好涵盖了青年谢林成为费希特思想的重要同路人,此后又凭借其自然哲学努力坚决地从费希特的哲学影响中分离出去,进入他自己建立的同一性哲学的这整个时期。其间以谢林为代表的早期唯理念主义与以F.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的理论探索曾经发生紧密的联系和各种思想交叉。谢林的神话观点与一种带有“古典—浪漫派”烙印的“新神话”思想发生了各种商榷,激发了后果极为丰富的理论探讨热潮。不过,随着早期浪漫派所主张和推行的“审美革命”在1804年左右“搁浅”,随着早期唯理念主义与早期浪漫派在1806年左右完全中止相互间的思想合作,谢林哲学发生了新的转向:艺术不再是他的中心题目。为了追踪谢林的思想发展,我们可借助大量文献史料厘清这段错综复杂的问题史架构。
问题在于阿尔沃恩把谢林这个哲学时期概括为其“审美的唯理念主义阶段”,并且不假思索地将其中所有的哲学动向及其各种理论切入,包括PdK中的神话学导向,统统冠之以“审美举措”,这种理解上的偏差起了相当大的误导作用。因为,尽管我们确实要把System中的“艺术—哲学”纲要理解为康德的先验美学转向(并非是费希特主体性哲学)的直接理论接续,谢林同一性哲学时期的哲学思想却完全不能以主体性美学意义上的“审美”范畴来定义,PdK中的神话学处理更决非“审美的”。这个误解亟待纠正,因为它像前述的误解一样典型,一样遮蔽问题的实质,容易使人发生误会,落入前述的偏见,即以为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只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哲学代言人。至于谢林这个阶段的哲学探索为什么不是此种意义上的“审美的”,笔者在下面将以文本研究为根据给出自己的论证。在这方面,谢林研究大家、海德格尔弟子H.策尔特纳的研究判断可作为一种佐证,他早年对谢林同一性哲学的研究颇有影响,在那里对这种哲学的存在论维度给出了清晰的阐释线索。[5]
在接下来的70多年中,相关研究既没有对这个分期定义表示异议,也没有接续这个讨论。再次提到这个说法,已经是在1970年德国哲学界关于“诸种神话学构想问题”的大讨论中。德国唯理念主义研究专家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在他的一篇哲学短文中回顾了谢林的理论贡献包括同一性哲学的美学讲座系列PdK中的神话学切入,顺带也提到了阿尔沃恩对谢林神话学的这个分期法。然而他彼时的发言指向的是同一性哲学的潜在历史哲学维度,并未与阿尔沃恩这个分期的定义直接发生商榷。
此外,谢林的PdK之遭受忽视,也还有别的原因或更深的一个原因,这就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界的各种讨论可以说一直没有重视以笛卡尔为标志的近代过程早期的哲学美学阶段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对话特征”。而谢林的PdK及其神话学纲要不仅深深植根于这个大过程之内,它恰恰还代表这个对话运动中积极的也即建设性整合的那一极。这一点很晚才被德语世界的研究者注意到。此前谢林思想受到不少的误解甚至遮蔽,特别是来自黑格尔美学思想的遮蔽。笔者是指,在哲学史的新导向中,一些德国研究者认为近代美学全部问题集合的最高表述包括其“结束形式”,都可以在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哲学命题那里找到。从这种黑格尔主义和准黑格尔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人们经常忽视谢林的PdK所体现的形而上学整体论关怀,这个哲学本身也往往被看成对理性的任意越界,甚或作为一种出于误解的错误举措受到批评和指责。[6]不过,把唯理念主义的“绝对美学”评判为黑格尔美学的理论准备和前阶段,由此最终把它评判为“前近代的”理论,这种在当时的讨论中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做法,表现出一种致命的缺陷,因其未能完整地把握近代过程的复合性质。
如笔者在本书第一部分的问题史回溯中已经谈到的那样,还在20世纪60年代,图宾根大学的唯理念主义专家D.雅格就已致力于通过深入的文本研究澄清谢林PdK的问题集合与德国唯理念主义的问题集合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7]按照他的研究结论,当时的谢林正处在从主观唯理念主义到客观唯理念主义的过渡阶段。这是1800年前后的一个短暂阶段,此时谢林主张艺术在哲学那里有决定性和建设性的工具作用及整体性功能。也就是说,实际上,此时期问题涉及的并不是一种美学上的失败,而是涉及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内部的一个重要转向,这转向必须按照一种“理论升级”的范式去考察。即使在谢林稍后的“宗教转向”那里,D.雅格也看到审美理性最终以某种形式取得了胜利。所以与一般的成见相反,他坚持谢林的艺术概念的不可逾越,甚至坚持它的现实性,即使在与黑格尔美学的比较中也是如此。这种对谢林哲学的艺术概念的关键性地位的重要表述于是促发了捍卫哲学美学的进一步的集中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无论是唯理念主义哲学美学的那种绝对的体系诉求,还是审美东西(dassthetische)的调和力,均成为批判考察的中心。其间谢林“绝对美学”的举措不再被研究者简单地看作一种搁浅或失败。不过,借助于一种艺术哲学,主要是借助于一种哲学上被赋予有效性的艺术去实施基础哲学的那些基本功能,这种做法亦受到了激烈批评,在方法论上被指为彻底过时的和无效的。[8]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条问题线索,即由所谓《德国唯理念主义最早的体系规划》(1796/1797)残稿引发的争论和讨论。黑格尔手稿专家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了这份短小的手稿,经辨识后认定,虽然它是以黑格尔的笔迹写就,但无论其内容还是其表述方式都是谢林的。这个“规划”最早提出唯理念主义体系的理念论建设形态,其核心词之一就是与建设新美学有关的“新神话”。因其整个的思想线索与谢林的艺术哲学甚至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追求及展开路径极其吻合,《规划》被罗森茨威格断定为谢林的作品,黑格尔被认为是抄录人。但此后又有其作者是荷尔德林(Friedrich  ,1770—1843)的推论提出,论证亦能言之成理。到了20世纪70年代,语文学家和黑格尔研究者奥托·珀格勒(Otto
,1770—1843)的推论提出,论证亦能言之成理。到了20世纪70年代,语文学家和黑格尔研究者奥托·珀格勒(Otto  )教授根据自己的一系列语文学考据和手稿研究,把《规划》判定为青年黑格尔的作品。这个判定重新激发了围绕《规划》的激烈而集中的争论。参加讨论的研究者的观点共来自三方,即主谢林者、主黑格尔者和主荷尔德林者。
)教授根据自己的一系列语文学考据和手稿研究,把《规划》判定为青年黑格尔的作品。这个判定重新激发了围绕《规划》的激烈而集中的争论。参加讨论的研究者的观点共来自三方,即主谢林者、主黑格尔者和主荷尔德林者。
围绕Systemprogramm文本的这个讨论大大促进了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澄清,讨论的重点原初是澄清这份手稿、这一哲学《规划》的作者。但最终看来,它的主要成果却不是对作者问题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不如说,首先是在研究者当中消除了对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问题史和神话学理解尚普遍存在的无知状态。[9]笔者认为,除了揭示这个体系规划与谢林PdK里的神话学理解之间的思想平行性和它们的内在共同归属性,这一“作者讨论”最主要的成果在于,它重构地展示了“新神话”这个思想在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那里的整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如果说这个思想在Systemprogramm那里还没有提出体系的诉求,那么在谢林的PdK中它已经与一种整体论的哲学体系无法分割。最终,黑格尔在他关于“神话的丧失”和“艺术的终结”的理论那里,实际上又无情地驳回了谢林的这个思想。无论如何,这个
对比H.策尔特纳在其《1954年以来的谢林研究》(Schelling‐Forschung seit 1954)一书中的报告,特别是第25—29页;还可参看D.亨里希(D.Henrich)的有关论文,“Kunst und Kunst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legung mit Rücksicht auf Hegel)”,收在W.伊泽尔(W.Iser)主编的Immanente
legung mit Rücksicht auf Hegel)”,收在W.伊泽尔(W.Iser)主编的Immanente ,-sthetische Ref lexion一书中,见第11—32页,1966。讨论对把Systemprogramm的作者判定给黑格尔有利,但这个判断的理论支持却并非没有困难。黑格尔捍卫者们不得不十分费力地去解释,为什么黑格尔作为这样一个Systemprogramm的作者,在其早期包括追随谢林的耶拿早期,很少提出关于新神话的真正见解,为什么他个人的哲学发展道路甚至恰恰与这个“规划”背道而驰。于是黑格尔是从同窗荷尔德林而非从他的耶拿导师、友人和同事谢林处接受相关影响,并且在耶拿早期即发生思想转向等等,都是必须设立和必须论证的假设了;确实也有一批黑格尔研究者为澄清此问题而投入了对黑格尔的耶拿手稿的集中研究。[10]而谢林支持者们的难题主要是珀格勒教授的这个实证主义挑战:手稿的笔迹经过认证,表明其毫无疑问来自黑格尔本人,那么相关研究按照逻辑首先需要去证明它不是黑格尔的作品,然后才能去证明它是别人的比如谢林的作品。关于Systemprogramm的作者认定的讨论,直至目前,在一定意义上仍旧是开放的。
,-sthetische Ref lexion一书中,见第11—32页,1966。讨论对把Systemprogramm的作者判定给黑格尔有利,但这个判断的理论支持却并非没有困难。黑格尔捍卫者们不得不十分费力地去解释,为什么黑格尔作为这样一个Systemprogramm的作者,在其早期包括追随谢林的耶拿早期,很少提出关于新神话的真正见解,为什么他个人的哲学发展道路甚至恰恰与这个“规划”背道而驰。于是黑格尔是从同窗荷尔德林而非从他的耶拿导师、友人和同事谢林处接受相关影响,并且在耶拿早期即发生思想转向等等,都是必须设立和必须论证的假设了;确实也有一批黑格尔研究者为澄清此问题而投入了对黑格尔的耶拿手稿的集中研究。[10]而谢林支持者们的难题主要是珀格勒教授的这个实证主义挑战:手稿的笔迹经过认证,表明其毫无疑问来自黑格尔本人,那么相关研究按照逻辑首先需要去证明它不是黑格尔的作品,然后才能去证明它是别人的比如谢林的作品。关于Systemprogramm的作者认定的讨论,直至目前,在一定意义上仍旧是开放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在多种讨论中渐次得到澄清的一个事实上来,那就是,对早期唯理念主义的思想史问题史的整个整理工作,本质上并不涉及追踪一种学科完善的基本走向,比如发现一个理论如何地自我修正,并与它的理论对手不断商榷、相互矫正,最终修成正果,完善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理论大厦。情况并非如此。在对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整个发展过程的理论整理和归纳中,就神话的题目来说,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对一种神话观的不同阐释方向。也就是说,在谢林的神话构想和黑格尔的神话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方式的思想并存、思想交叉和思想对峙。
但当时在关于Systemprogramm的作者争论那里,显然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唯理念主义思想运动内部这种区别和复合的真正的意义所在。相反,在这种“作者争论”的背景下的讨论经常出现一个倾向,也就是片面地倚重黑格尔的观点。于是黑格尔对谢林的“绝对美学”的真理诉求及其整体性诉求的削弱影响了许多的研究者,最终导致他们将“绝对美学”贸然地判决为不符合理性化过程、不符合近代化过程的,也即判决为失去效力的。不过,与此相对,讨论中同时仍出现了反对这种片面性思考的声音,它们在“绝对美学”的基本思想和反近代性那里恰恰看见近代性本身固有的东西。在后面这种视点中,谢林的这个神话学纲要在有些考察那里,比如在对概念史的回顾性考察那里,即被普遍承认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整合努力:它要战胜那种简单化的“非此即彼”式错误态度,“要以‘理智直观’的概念战胜那种神话与逻各斯的二分法”[11]。如果说,与此同时审美东西的调和功能不再允许是对自然与历史的任何一种直接调和,艺术的真理特征也不再能直接地满足整体性诉求,那么谢林PdK的独特东西,哲学与艺术通过作为一种统一意识的神话而达到的那种统一,却在黑格尔关于艺术局部性的学说的巨大现实性之旁,毫不逊色地始终作为另一个中心引起极大的研究兴趣。借助于统一性的和创造性的构成力的支持,这一哲学美学的模式得到捍卫,它的有效性亦得到承认。[12]这种美学为理性打开了一种关于诸事物的另一种秩序的视野,揭示了艺术的一种真理概念。由它所凸显的审美东西的那种反近代的潜在倾向发展出一种历史性的影响和作用。它的影响在后来所谓“真理派美学”,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也在阿多诺那里,在那种关于艺术自律的观点那里都可以观察到,至于G.卢卡奇仍在与这种唯理念主义传统重新衔接,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3]
于是我们看见谢林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密集的理论探讨中经历了某种“复活”。因为这些讨论特别集中地反思近代思想过程的一种典型特征——它的两极性,为此大量的讨论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1800年左右的哲学特有的对话处境上来并获得了深化的认识:无论在审美领域,还是在近代过程之内,启蒙主义与德国浪漫派及唯理念主义所共同体现的那种极性和共属性,都要求我们把它们理解为创造性的和不可扬弃的。也就是说,尽管启蒙主义站在一边,浪漫派和德国唯理念主义站在另一边,这两边却共同存在于一个内在的总体关联之内。[14]无论在启蒙主义那里,还是在德国浪漫派和德国唯理念主义这里,对一种无所不包的整体性秩序的追求和渴念,对一种能够为社会生活提供合法性和意义的总体关系的追求和渴念,其存在都是必然的。这种追求和渴念“正是随着近代、并且在近代之内才获得它的全部意义”[15]。例如,德国古典主义与德国唯理念主义那里的神话理解,已经以启蒙主义的历史思考打开的进程为前提条件,这种思考已经把古典的榜样,把古代诗歌和古代神话的原型推到无限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早期浪漫派和早期唯理念主义对神话的重新发现,毫无疑问都是针对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发出的一种清楚的抗议,盖因理性在后者那里被狭隘化了。[16]正是在一种分裂的社会的背景上,早期浪漫派曾尝试借助于一种“审美革命”去调和这种分裂,也正是在启蒙主义带来的一种工具性理性的形成过程中,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关于一种“新神话”的观点证明它自己极其重要、不可扬弃。而谢林以其对神话作为美学的给定内容的哲学建构为哲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那里实现了对古典的真理概念和古代的整体性诉求的建设和保存。PdK中的神话学纲要,实际上代表了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哲学神话学理解。
谢林PdK中的神话学的哲学探索同时也建立在一种来自对古代研究本身的整体性世界理解上。这一绝对美学按谢林的看法直接处于与自然哲学相关的总体论证关联中。其实,对德语世界的哲学研究者来说,PdK这个普遍精神史的框架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不过它却很少得到透彻的讨论。如果说这个观点,即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新神话思想在谢林那里是建立在其自然哲学的认识上,已经出现在一些讨论中[17],那么我们看到,19世纪的实证论意识,它与发生在哲学那里的放弃绝对体系诉求的做法,与发生在自然科学那里的与科学和哲学的内在论联系拉开距离的做法相应,并没有接过对一种无所不包的自然哲学的那种意义重大的形而上学的把握,不如说,它追随的是另一个方向,也即经验的方向。
令人欣慰的是,在谢林研究学者当中,一系列的研究很久以来已经打破了这种忽视。大约30年以来,对整体论导向的自然形而上学的新兴趣已经觉醒,这种形而上学可以认作是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针对合理主义对自然功能的那种狭窄化处理的清楚的抗击反应,是它针对18世纪对合理主义的自然科学的绝对化的表示的坚决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恰恰正是出现在形而上学的“世界图像”走了下坡路的总体背景中。如果我们说,在W.威兰(W.Wieland)那里,要求严肃对待谢林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界说的主张乃是建立在此种洞见上:必须把自然哲学的意识理解为哲学从理性出发的自我批判[18];那么许多研究还尝试从自然科学的有效性出发为谢林的自然哲学正名,谢林及其自然的“实体性统一观”对科学史的客观影响在这期间也得到了批判的考察。[19]只不过,反思的重点重新放到了谢林思想的内容上,比如其自然概念和其超出对象认识的现实性理念。今天,这一世界哲学日益赢得它的意义,正是因为在它那里,这种哲学试图从自然本身的现实性总关联中去理解人类的生存活动,主张我们人类应该而且必须“从生活实践的兴趣出发,重新思考我们与自然的关系”[20]。
正是在此处,笔者看到对谢林PdK的研究有一个继续深入讨论的契机,这就是把谢林PdK中的神话学凸显为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哲学神话学的本质性理解。笔者的研究将首先致力于揭示这一点:近代美学在谢林那里实现了一种向艺术哲学的转向,而且是借助于贯彻一种无所不包的自然形而上学实现的。与这转向同时还发生了美理念与“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真理传统的重新衔接,因为在其原初的、存在论的意义上,这理念本是“原现实性”。因此笔者认为,“一个活生生的,通过其自身存在的自然”的理念(谢林语),不仅在谢林的神话理解及其与古希腊的象征自然观的关联那里起着一种背景命题的作用,它还主导和贯穿着其整个神话建构。谢林这个神话学构想的形而上学动机是对“原型东西”或“原初同一性”进行再结构,以此克服人与自然的那种分裂。进一步说来,谢林又是借助于哲学的体系并站在艺术的立场上来处理这个神话学构想,并把它作为一种艺术哲学的核心内容来处理,这对德国唯理念主义建设及其批判研究均是开辟性的。[21]
不过,本书第二部分的考察重点,并不是同一性哲学时期谢林的绝对唯理念主义的思辨论证,而是他的思路,特别是他的这个重新发现:神话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切艺术的给定东西。为了展开他这个观点,笔者将在分析讨论中直接援引谢林在1801年到1807年之间写作的同一性哲学文献中有关的神话陈述,在相关的语境和提问中对它们作出判断和评价,通过文本分析说明它们与这一艺术哲学种种命题的内在关系。这个处理是以谢林本人对神话的存在论维度的清晰意识为论证基础:在其著作中不同的个别处理那里,这个意识都清楚可辨,不会使我们发生误解。尽管如此,笔者的目的并不是对谢林PdK一书中哲学神话学的整个问题集合提供一种无所不包的诠释,笔者的工作重点只在于揭示这个哲学神话学的问题总关联及其思想内容,特别是哲学美学讨论仍然需要澄清的那些问题。
本书第二部分在《〈艺术哲学〉(1802—1805)中的存在论神话学》的这一研究题目下,以七章来处理PdK中这个存在论神话学。第六章的重点是表述PdK所隶属的同一性哲学框架,阐明它的自然哲学切入点,说明作为神话学总体构想基础的那个“世界理解”的构架。第七章探讨谢林对“万有论”着眼于艺术作出的界说,指出它意在对“绝对美”做出存在论阐述,并讨论与“万有论”总体相关的“表述论”,揭示谢林按照同一性哲学把美的理念与艺术的理念重新衔接的特别意义——通过这个衔接,艺术在其与整体原理的关系中成为原初世界知识的代表。第八章集中于界说谢林的神话学构想,揭示它固有的深层关怀。这个构想并不涉及对神话做一种“更新”,如早期浪漫派那类的理论努力,它仅仅致力于研究“神性诸事物”、研究它们的现场化,即艺术的永恒真理内容。在考察谢林的“理念论—诸神说”释义之后,第九章探讨谢林对神话的存在论结构的阐发,同时借助于对相关文本的解说,说明谢林对古典神话学探索的吸收。第十、十一、十二这三章,分别处理谢林对“实在的神话”即希腊神话、“观念的神话”即基督教神话和“新神话”的哲学建构。后面这一系列神话学考察意在展示神话学建构的历史维度,它是谢林着眼于艺术的历史方面为我们打开的。谢林对希腊艺术与近代艺术的对立所做的处理可定义为“存在论—神话学”的,他将整部艺术史存在论地理解为对神性东西的历史性调和的直接表述。谢林与早期浪漫派关于“新神话”的规划的理论商榷和争辩也是考察的重点。当然,即使是最后这一章,也要在大题目下对各个具体的提问加以限制。笔者只从下面这几个切入点来讨论谢林围绕“新神话”的那些重要的思想,比如在关于新神话的产生问题上,在新神话与新艺术的关系那里,在谢林的作为艺术创作基本命题的“天才说”那里。第二部分的结语将返回谢林这个存在论神话学构想的独特思考,阐明它意欲借助一种整体的自然观,使神话的那种同一性原理——它提供生命本来意义上不可扬弃的整体性,对人类理性来说重新可以接近。
【注释】
[1]以下缩略语PdK。
[2]参看H.策尔特纳在Schelling forschung seit 1954中的批评,1975年。
[3]Cf.B.Barth,Schellings Philosophie der Kunst.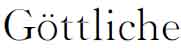 Imagination und-sthetische Einbildungskraft,1991,S.15.
Imagination und-sthetische Einbildungskraft,1991,S.15.
[4]Cf.A.Allwohn,Der Mythos bei Schelling,in:Kant‐Studien,Erg-nzungshefte 61,1927.
[5]Cf.H.Zeltner,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 Idee und d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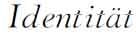 ssystem,1931.
ssystem,1931.
[6]Cf.H.J.Sandkuehler,Schelling.
[7]Cf.Schelling:Die Kunst in der Philosophie Bd.I+Bd.II,1966,1969.
[8]Cf.H.Freier,Die Rückkehr der G9tter.Von der-
 schreitung der Wissens‐grenze zur Mythologie der Moderne.Eine Untersuchung zur systematischen Rolle der Kunst in der Philosophie Kants und Schellings,1976.
schreitung der Wissens‐grenze zur Mythologie der Moderne.Eine Untersuchung zur systematischen Rolle der Kunst in der Philosophie Kants und Schellings,1976.
[9]参看R.布勃纳(R.Bubner)主编的Das Systemprogramm,1973年版,其中虽然收录了法国的谢林研究大家克萨维尔·蒂利特(Xavier Tilliette)的重要论文“Schelling als Verfasser des Systemprogramms?”,但这个讨论卷中的研究可以说集中代表德国唯理念论研究者中黑格尔派的意见:手稿归属黑格尔,正如参与者的身份亦多为重量级的黑格尔研究大家,且直接来自唯理念主义研究大本营海德堡大学和波鸿的黑格尔研究档案馆:Dieter Henrich、Hermann Braun、Klaus Düsing、Friedrich Strack、Otto
Systemprogramm,1973年版,其中虽然收录了法国的谢林研究大家克萨维尔·蒂利特(Xavier Tilliette)的重要论文“Schelling als Verfasser des Systemprogramms?”,但这个讨论卷中的研究可以说集中代表德国唯理念论研究者中黑格尔派的意见:手稿归属黑格尔,正如参与者的身份亦多为重量级的黑格尔研究大家,且直接来自唯理念主义研究大本营海德堡大学和波鸿的黑格尔研究档案馆:Dieter Henrich、Hermann Braun、Klaus Düsing、Friedrich Strack、Otto  等等;另两位黑格尔研究者Chr.雅默(Chr.Jamme)与H.施奈德(H.Schneider)合作主编了《神话和理性:黑格尔的“德国唯理念主义最早的体系规划”》(Mythologie der Vernunft.Hegels”
等等;另两位黑格尔研究者Chr.雅默(Chr.Jamme)与H.施奈德(H.Schneider)合作主编了《神话和理性:黑格尔的“德国唯理念主义最早的体系规划”》(Mythologie der Vernunft.Hegel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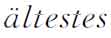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 ismus“,1984),也是研究引用较多的参考资料集。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 ismus“,1984),也是研究引用较多的参考资料集。
[10]以下结集出版的黑格尔耶拿手稿已是早期黑格尔思想研究重要资源:Jenaer Systementwür fe I:Das System der speculativen Philosophie.Fragmenteaus Vorlesungs‐manuskripten zur Philosophie der Natur und des Geistes 1803/04,hrsg.v.K.Düsing u.H.Kimmerle,Hamburg 1986;Jenaer Systementwür fe II:Logik,Metaphysik,Natur‐philosophie 1804/05,hrsg.v.R‐P.Horstmann,Hamburg 1982;Jenaer Systementwür fe III:Naturphilosophieund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1805/06,hrsg.v.R‐P.Horstmann,Hamburg 1987。
[11]Cf.H.Gockel,Mythos und Poesie.Zum Mythosbegriff in Aufkl-rung und Frühromantik,1981,S.7.
[12]Cf.B.Barth,Schellings Philosophie der Kunst,1991.
[13]我在此不能阐发这些哲学家的这种自觉衔接的问题史方面,只限于提示他们均与唯理念论美学发生各种商榷,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P.Bürger,Zur Kritik der idealis‐tischen ,1983。
,1983。
[14]Cf.W.J-schke,H.Holzhe(hg.)Der Streit um die Grundlage der (1795—1805),1990.
(1795—1805),1990.
[15]Cf.W.J-schke,H.Holzhe(hg.)Der Streit um die Grundlage der (1795—1805),1990,S.36.
(1795—1805),1990,S.36.
[16]Cf.Chr.Jamme,Idealismus und Aufkl-rung,1988.
[17]参见O.Marquard,“Zur Funktion der Mythologie bei Schelling”,收在1976年德国学界的重要讨论集Terror und Spiel一书中,第257—263页;雅姆(Chr.Jamme)1991年发表的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Mythos对清理问题也很有启发,参看该书第17—57页;Cf.H.Freier,1976,S.176—214。
[18]Cf.W.Wieland,”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Schellings und die Frage nach der Natur“,in Materialien zu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An f-ngen,1975,S.237—279.
[19]Cf.M‐L.Heuser‐Keler,Die Produktivit-t der Natur.Schellings Naturphilosophie und das neue Paradigma der Selbstorganisation in der Naturwissenschaft,1996;K‐J.Grün,Das Erwachen der Materie:Studieü den spinozistischen Gehalt der Naturphilosophie Schellings,1993;两书均为谢林自然哲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den spinozistischen Gehalt der Naturphilosophie Schellings,1993;两书均为谢林自然哲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20]Cf.W.Schmied‐Kowarzik,Von der wirklichen,von der seyenden Natur.Schellings Ringen um eine Naturphilosophie i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Kant,Fichte und Hegel,1997,S.15f.
[21]本书暂不讨论“肯定哲学”框架中的谢林后期的神话哲学中的处理,仅在比较研究时给出必要的提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