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书名: The Novel and the Sea
译著书名: 《小说与海洋》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Cohen),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安德鲁•哈蒙德(Andrew B. Hammond)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法语语言、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
译者简介:陈橙,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出版专著《文选编译与经典重构》,译著《风拂绿柳》,主编《域外中国文化形象研究集刊》,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上海市哲社项目等多项课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译作十余篇。
内容简介: 从历史的沉船事件到现代文化想象中的海洋魅力,《小说与海洋》审视了两百多年的海洋小说。作者将小说置于海外开拓和海上作业的大背景中,视海洋小说的起源为横跨大西洋历史的必然结果,其中充满了海洋奇遇和海洋冒险。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学史作品,《小说与海洋》可以改变读者对传统陆地型小说的认知。该书分析了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如何通过对无人岛、暴风、船难、海盗等的诱人描写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海洋文学作品;探讨了美国小说家库柏如何使后殖民背景下的美国海洋冒险小说焕然一新,如何改变了19世纪描写海外探险的文学作品的诗学形态;剖析了法国小说家凡尔纳如何将冒险小说改变为科幻小说;展示了梅尔维尔、雨果、康拉德等如何在语言和思想的迷雾波涛中独步前行;揭示了侦探小说如何运用海洋小说中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等。作者在分析大量作品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崭新而大胆的海洋文学史。该书既适合具有专业知识的读者,也适合对海洋小说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该书获奖:
2012年国际叙事学研究学会“伯金斯奖”(The Barbara and George Perkins Award),叙事学界的最高奖项;
2010—2011年美国18世纪研究协会“路易斯奖”(Louis Gottschalk Prize);
2011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列文奖”(Harry Levin Prize)第三名。
译文节选:
“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
——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特里斯坦说道
(引自艾略特《荒原》[1])
跨越边界
“崇高”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美学概念,一般被定义为亲眼目睹巨大的力量而带来的愉悦。这个概念最早由古罗马时期希腊学者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提出。朗吉弩斯指出,崇高包括了藻饰的技法和伟大的思想,让听众忘记了他们是在听演说,忘记了评判,只是被“深深吸引了”。虽然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崇高的作品都再现了伟大的力量和情感。朗吉弩斯的概念涵盖了升华和毁灭两个层次,即崇高的“光明”与“黑暗”,这里借用了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对画家透纳的画所做的评论,透纳是崇高画作的大师。[2]
在朗吉弩斯看来,《圣经》中上帝的话语闪现着崇高的光辉。他认为,“要有光”这样的语言融合了简洁的力量和伟大的思想。而对于“黑暗”的一面,朗吉弩斯虽然也有所论及,但是叙述起来却感到不适,因为它们“让人恐惧;从另一个角度说,它们是邪恶的,越过了善的边界”。[3]
当朗吉弩斯举例说明越界的崇高之邪恶一面时,他反复引用了现代水手称为海上异事的场景描述。因此,他提到了荷马笔下的一场暴风雨,荷马用来比喻赫克托耳作战之勇:
他扑上去,宛若巨浪打在一艘快船上,
在浓云之下狂风掀起了惊涛骇浪,
浪花把船淹没了,可怕的飓风若狂,
在船帆上怒吼,舟子发抖,因为惊慌,
出于毁灭之下的逃生十分勉强。[4]
当解释为什么这个场面如此吸引读者时,朗吉弩斯指出,荷马并不把惊险限于一时,他“描写舟子们不断地处于毁灭的边缘,一浪接着一浪打来”,这种细节描写扣人心弦。通过使用非常规的句法,形成张力,荷马再现了这种惊险的场景。朗吉弩斯写道,荷马“在‘出于毁灭之下’这短语中,强迫两个前置词结成一个不大自然的复合词,他这样强扭其语言,使之符合当前的灾难,以语言的紧凑庄严地绘出苦难的场面,几乎使他的辞藻也带上这场惊险的烙印了——‘出于毁灭之下’云云”。[5]
朗吉弩斯所指的崇高,有一个隐含之意,即跨越边界的美学效果,就像水手跨越生活的局限,诗人跨越修辞和句法的局限。崇高就是由这些局限及其越界形成的美学效果,它源于古典悲剧的一个核心要素,即人类的局限性,但崇高违背了对局限性的敬畏,而这种敬畏是古典传统的重要特点。在文学批评领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体现了古典传统对局限性的敬畏。他关注的是悲剧如何遵循完美的写作模式,而非寻求打破既定模式的创新。朗吉弩斯并没有在理论上阐释跨越边界的重要性,不管是在修辞上,还是在海洋描写上。但是,他却强调了跨越边界的力量,视之为崇高的一种,使之成为现代性美学中重要的一类。
在现代初期以前,朗吉弩斯的论说并没有引起欧洲美学的重视。直到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大师尼古拉·布瓦洛在1674年将其文章《论崇高与奇迹,译自朗吉弩斯》翻译成法文,才引起批评界对朗吉弩斯的关注。布瓦洛在译文的序言中指出,朗吉弩斯的美学说明了,除了传统的高雅文学形式所体现的华丽堂皇,还有其他的文学形式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再现来感动读者。他说道:“崇高常常需要美丽的辞藻,但是仅仅一个想法、一个数字和一个词语,也可以体现出崇高。”[6]布瓦洛的这种观点赋予了“崇高”现代意义,使之在根本上从一种文体特点转向对内容和思想的关注。[7]
当布瓦洛试图描述这种强力有的再现方式时,只有“崇高”这个词似乎还不够。在其译文标题中,除了“崇高”,他还加上了“奇迹”,并在序言中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称之为“非凡”和“惊异”。他说道:“我们必须知道,朗吉弩斯所说的崇高并非演说者所指的崇高的文体,而是指作品非凡和奇异的特质,可以让读者开心、让读者激动、让读者入迷”,并强调说:“我们必须明白朗吉弩斯的崇高指的是非凡、惊异、奇迹”。
为了把握崇高的特质,布瓦洛用了一个语义网:奇迹、非凡、惊异。这些词在当代常用来指海洋边界地带的新发现和种种危险。“奇迹”指新大陆的发现,“非凡”和“惊异”则常指海上异事。在布瓦洛之前的几年,后来被公认为现代崇高风格鼻祖的诗人弥尔顿通过描写水手在危难中的行为,塑造了跨越边界的超凡力量,这种力量颠覆了上帝。
海滩上的撒旦
弥尔顿的《失乐园》,初版于1667年,内容既包含光明的崇高,也有黑暗的崇高。光明的崇高来自弥尔顿对天堂的描述,黑暗的崇高则来自反叛的撒旦的堕落。当弥尔顿描述撒旦的幽冥王国的恶劣环境时,批评家们注意到,这些环境描写和航海家们在边界外的浩瀚海洋中所遭遇的险境很相似,尤其是在北极荒地。例如,伊恩·麦克莱恩特别指出,弥尔顿笔下撒旦群魔发现的“冰冻大陆”与《托马斯·詹姆斯船长航海历险奇遇记》(1633)中描写的北极荒地十分相似,后者是弥尔顿那个时代的畅销书。[8] 通过弥尔顿的再创造,詹姆斯的北极荒地变成了充斥着无边黑暗的大陆:
……那儿黑暗而荒凉,不断地受
风暴、冰雹、大旋风的袭击,
冰雹落在那坚硬的地上就不消融,
堆积成山,看来像古塔的断壁残垣。
此外只有很厚的积雪和冰,
……那儿的空气干燥而严寒,
冻得你肌肤疼痛,有如被火灼伤[9]
撒旦手下的群魔“大胆探险”来到这片大陆。[10] 他们流动的天性和水手一样,超越知识和技术的局限,寻求西北新航线,开拓未知的边缘地带。[11]
海洋边界形塑了撒旦堕落的崇高性,不仅体现在他的幽冥王国上,还体现在弥尔顿怎么描述撒旦的力量。撒旦从天堂堕落至火海,弥尔顿把他比作海中怪兽利维坦。但是这只怪兽很快展现出一个熟练水手的气质,“他的头露在火焰波浪上面,/两只眼睛,发射着炯炯的光芒”,意志坚定。[12]
为了仔细分析撒旦在险境中的行为,我们再来看看他采用了什么样的技艺。堕落之时,撒旦处于恐怖的险境中,“洪水泛滥”。但他并非独自一人,“那和他一起坠落的,是无法抗拒的/有如洪水旋风般的狂暴的火焰……在他之旁”。[13]作为一个熟练的水手,撒旦在困境中乐观而积极地想办法。他鼓励同伴去寻找那一片“荒凉的原野”,“我们往那儿去,一避火浪的冲击……从希望中可以得些怎样的援助/或从失望中来一个怎样的决策”。[14] 接下来,撒旦就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些话,他飞过海洋,落在一个未知的海岸,然后发现了“干燥的土地”,好像是“火烧”,他“踏着沉重的脚步”,“不像当初走在天界那样矫健,轻盈,/而且遍地是火,热浪扑面而来,/炙烤得他浑身疼痛。”忍住疼痛,撒旦显示出水手的耐心和努力:“但他强忍剧痛,走到火海岸边,/他站住”。[15] 弥尔顿还把撒旦的长矛与船上的桅杆相比,桅杆体现了海上冒险的勃勃雄心,因此这个类比把海滩上的撒旦和勇敢的水手更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同他的长矛相比,那从挪威群山采伐下来,/可作兵舰桅杆的高大松树,/看来只不过是小棍。”[16]
然而,熟练的水手在浩瀚而多变的海洋面前,处处谨慎;与之不同的是,撒旦得意地夸耀自己技艺的力量。当撒旦和同伴到达海岸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他和他的亲密伙伴飞到哪儿,/都洋洋自得,夸耀自己神通,/能够逃出地狱的火焰,全凭自己,/而不是由于至尊大能者的默许。”[17] 带着这种大胆的自信,撒旦开始像水手一样工作,勘察并绘制这块新发现的土地:“那失位的大天使说道:“难道这就是我们用天堂换来的土地?/换来的就是这块地盘,这片疆域?/天上的光明只换得这可悲的幽冥?”[18] 撒旦和他的手下蔑视天意,宣扬自身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弥尔顿似乎意在反驳水手技艺的神学观,虽然撒旦这种大胆的挑衅行为与水手传记中对生存和救赎的战战兢兢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未缀锦成文,吟咏成诗的题材:应变大师弥尔顿
海滩上的撒旦是开路的水手,打探他的新王国的恶劣环境。他的塑造者弥尔顿,同样也是一个开路者。在这篇“大胆而崇高”的史诗的开头,弥尔顿就指出,他“这篇大胆冒险的诗歌”,不走寻常路,“从未有人尝试缀锦成文,/吟咏成诗的题材,遐想凌云,/飞越爱奥尼的高峰。”[19]
追寻前人未尝试过的事物就是超越过往。可以和海滩上的撒旦这一场景形成互文对照的,是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描写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踏上新大陆,他绕过好望角,完成了以往欧洲航海家们从未完成的航行,开辟了通向印度的新道路。这时,达·伽马展示的是航海家的技艺,试图确定他的方位,而不像撒旦那样洋洋自得。[20] 达·伽马调整好星盘,因为星盘在沥青的船板上不好固定:
但是我,却迫切地想知道我在哪里,
和水手们一起站在海滩上,
测量太阳的高度,用我们的技艺
确定航海图中我们的方位。[21]
自中世纪末以来,人们一直用星盘测量方位,但这种技术复杂而低效,16世纪被轻便的直角器和背测式测天仪所取代,后来又改进为六分仪,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定位系统取代了传统的航海测量仪器。
撒旦着陆的时候,有一个时髦的望远镜。这是一项新发明,引发了现代科学革命。弥尔顿运用了诗歌中的比喻修辞技巧,让撒旦这位《圣经》里的角色使用这么一项最先进的技术。卡蒙斯的史诗,是描绘实践的传奇,没有修饰润色,只是简单描写了达·伽马的动作,叙述其应对策略和方法。[22] 相比之下,弥尔顿通过赋予撒旦望远镜,做了一个暧昧的英雄主义的比喻。这个比喻出现在撒旦背负着盾牌,挣扎着向岸边走去之时:
……那个阔大的圆形物
好像一轮明月挂在他的双肩上,
就是那个突斯岗的大师
在黄昏时分,于飞索尔山顶,
瓦达诺山谷,用望远镜探望到的
有新地和河山,满布斑纹的月轮。[23]
当我们把这个比喻层层解开,就会为弥尔顿拍案叫绝,比喻让我们反思技术性创新、人类技艺、科学和人对神学的反抗之间的关联。
研究弥尔顿的学者认为“突斯岗的大师”指的是伽利略,望远镜的发明者之一。事实上,当伽利略被囚禁审查的时候,弥尔顿曾在科学家的陪同下观看过伽利略的望远镜。[24] 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一方面是为了观测天体运动,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天文知识解决测算海上经纬度的问题。如果撒旦背上的光晕是用伽利略的望远镜看到的月亮,那么这个光晕是在科学知识和航海技艺的合力推动下显现出来的,二者的目的都在于通过探索天体和地球,推进知识进步。
正如伽利略的迫害者们所害怕的,这种科学探索将会完全颠覆神学的宇宙观,不管是天文学的力量,还是反驳太阳和月亮都绕着地球转的宗教信仰。这句诗中弥尔顿用了有歧义的句法,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如果把“明月”变成主语,望着地球上的观察者,那观察者就变成了宾语。虽然我们倾向于按照历史事实去解读,这句诗中比喻的含义却是暧昧不清的。如果是“透过望远镜看到的月轮”注视着“突斯岗的大师”呢?在这里,可颠倒的句法提供了可能性,即月轮,也就是撒旦的喻体,变成了注视的主体,回望着地球。通过比喻、句法以及比水手的猜想更为奇特的想象,弥尔顿充满创造性的权宜之计让撒旦的武器库中多了望远镜。[25]
当然,弥尔顿并没有把他自己在《失乐园》中所做的尝试比喻成撒旦坠入黑暗的堕落。相反,弥尔顿想达到的是崇高的光辉和缪斯的顶点。(事实上,从崇高的两个分支来看,升华总是和向上达及神性联系在一起,而堕落则是掉入万丈深渊和浩瀚无际的海洋。)为了达及神性,弥尔顿虔诚地吟诵道:“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26]。尽管如此,虽然弥尔顿想向上飞升,他却和撒旦一样,也和那些航海家一样,想要跨越边界。这种跨越边界的欲望其实蕴含着对神学的颠覆,即使作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
开路的航海家和冒险的艺术家在崇高性上是相似的,画家乔纳森·理查森在其《绘画理论漫谈》(1725)一书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在理查森看来,艺术家为了拓展诗学技巧而超越局限,从而达到崇高:“崇高不屑被束缚,它没有界限,是天才的迸发,是人性的完美”[27]。在此意义上,艺术家和航海家同命相连,共同寻找新世界。“谁知道时间的发源地里藏着什么东西!”理查森说道,“下一个天才或许会使拉斐尔黯然失色;一个新的哥伦布或许会穿越大西洋,把那赫拉克利斯之柱抛在身后……蒲柏说‘所以艺术家应该/沐浴天堂之火/在未知的渴望中达至完美’。这是抵达崇高的伟大路径。”[28]
海盗的低级崇高
从某种角度来说,水手和艺术家称得上是撒旦的贵亲,因为他们都游走在现代性的动态边缘地带,而在现代航海史的初期,海滩上的撒旦则可以找到无数臭名昭著的兄弟,这就是海盗,大胆地往返于边界外的浩瀚海洋,“谋取暴利,犯下滔天的罪行”[29],亚历山大·艾斯克默林在《美国海盗》中这样说道。和布瓦洛译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一样,《美国海盗》也是出版于17世纪,通过描写海盗游走边界、突破边界的决心和意志,开启了现代浪漫主义的大门。艾斯克默林在书中描述了最残暴的海盗,他将之比喻为恶魔。例如,当海盗罗罗洛亚拷问被囚的西班牙人时,他们反抗不从,这时罗罗洛亚“像愤怒的魔鬼,用他的短刀刺穿其中一个人的心脏,把心脏取出来放在嘴里咬啮,然后再扔到其他人的面前,说道:‘谁再不从,下场就和他一样。’”[30]
在《海盗简史》(1724)中,“约翰逊船长”也把这些令人发指的海盗恶行比喻成恶魔。书中最残忍的海盗之一是爱德华 • 迪奇船长,也叫黑胡子。作为海盗头子,黑胡子让他手下的海盗都要欣赏崇拜他犯下的恶行,因为“谁罪大恶极,谁就能引起其他人的嫉妒,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特别勇猛”,甚至他的欢乐“都是建立在邪恶上的欢愉,好像就是要让他手下的人觉得他是恶魔的化身”。我在前面一章(指该书第二章。——译者注)引用过他的故事,他怎么在船舱里制造一个“人间地狱”。[31]
罗罗洛亚、黑胡子以及他们的海盗弟兄们所犯下的罪恶行状是崇高风格的另一极端,不同于理查森所说的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或者是追寻知识的英雄水手。但他们毫无疑问超越了界限,用朗吉弩斯委婉的话来说,“它们是邪恶的,穿越了善的边界”。在拜伦看来,海盗和现代性中奋力向上的精神是紧密相连的,都体现了海上作业的浪漫主义中产阶级对自由的追寻。
未知航程的愉悦
那些讨论崇高的批评家们在解释积极向上的崇高所带给人的愉悦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他们试图解释令人恐惧的经历为何能带给人崇高的愉悦时,他们费尽周折、使出浑身解数。海洋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充满了崇高的恐惧,它不像山峰,总是与崇高的上帝联系在一起。因此,约翰·丹尼斯在1704年提出了“令人狂热的恐惧”这一说法,用来指一种特殊的崇高情感,这一情感伴随着“雷电、暴风雨、怒海、洪水、急流”,还有魔法、妖怪、地震,以及其他奇异的地理现象。[32] 后来当艾迪生(18世纪英国美学家。——译者注)思考为什么海洋能激发崇高性时,他把丹尼斯的“令人狂热的恐惧”变成了“令人愉悦的恐惧”。在1712年9月20日的《观察者》中,艾迪生说道:“在我所见事物之中,没有什么比大海或者海洋更能激发我的想象力。每当看见汹涌的波涛翻滚,即使是在平静的大海,也能带给我欢愉的惊喜。当暴风袭来,所有的边际消失,只剩下波浪滔天、怒海翻腾,这种场景带来的令人愉悦的恐惧简直无法用笔墨形容”。[33] 通过把海洋的崇高性和暴风雨中的情感联系起来,艾迪生其实是把崇高的概念和极端危险带来的对生命的恐惧联系在了一起。在面对暴风雨时,水手会显示出勇敢和乐观,用熟练的技艺解决问题。但是,为了达至崇高,这种乐观主义和求生的奋斗被令人愉悦的恐惧所取代。
事实上,恐惧会变成崇高本身的基础所在,埃德蒙·伯克总结了近半个世纪对“令人愉悦的恐惧”的讨论,在《论崇高与美丽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1757)中,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阐释了这种恐惧的功效。他指出,这种恐惧体验对心理是有好处的,尤其对那些患有抑郁症的人有好处。[34] 恐惧的场景会激发人们自我保护的情感,使没有亲身体验过危难的闲散的审美读者觉得自己充满了生气与活力。[35] 根据伯克的观点,崇高风格的审美比《鲁滨逊漂流记》给业余航海爱好者带来的愉悦更为高级,后者在想象中和鲁滨逊一起荒岛求生。
在水手日志或是已发表的作品中,真正经历了种种困境的航海家们却闭口不谈航海中的恐惧带来的愉悦。事实上,他们几乎不谈航海的愉悦,只是表明他们纯熟的技艺和完成任务的使命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库克船长在日志中思考“未知的航程”带来的诱惑:“当成为第一个未知领域的发现者,即使这个未知领域只是一片沙滩,也会感到一种自然涌发的愉悦。如果不是为了这种愉悦,这样的航行断不可能,尤其是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缺乏食物,缺乏一切必需品”。[36] 让我们惊异的是,在这里,库克船长谈到物资贫乏的航海的愉悦时,无关启蒙主义运动、无关名利的诱惑,也无关资本家的原始积累。他把这种诱惑称为“自然涌发的”,也就是难以用概念来阐释的,说明了这种诱惑是不可抗拒的。
库克船长在其航海探险记录中能够描述出这种愉悦,或许是因为他的日记写成于18世纪六七十年代,而那时正是崇高美学兴起之时。库克船长日记采用的是朴实无华的水手日志风格,但是我们仍能从其中找到几处激动人心的场景描述,体现了崇高的风格。其中一处是前面引用过的,库克船长描写了几乎毁掉他们船只的大堡礁是多么势不可挡、超乎想象。这时,库克船长用了一系列表现崇高风格的词汇,说明这次困难不仅是技艺的失败,也是面对未曾想象的困难时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欧洲人从未听说过这块暗礁,它几乎是从深不可测的大海中直立而起的一堵珊瑚礁墙,水位高时,它在水下7到8英尺深处摇曳生姿,水位低时,便露出水面变得干燥;浩瀚大洋上的巨浪在这里猛然受阻,激起山峰一样高的惊涛骇浪,特别是遇到季风推波助澜,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37] 让我们注意一下在平实的水手叙述中,这些具有崇高风格的词“浩瀚的”“深不可测的”“惊涛骇浪”。通过这种描写,库克船长向我们展示了崇高风格如何从美学领域转向水手经历。美学领域提供的只是面对现代性局限时所激发的恐惧的余像,而水手则是在现实世界中与这些令人生畏的困难斗争。当库克船长写下日记之时,崇高风格表现了现代性对超越极限的迷恋,这种迷恋无法用工具理性来解释,但却产生了更矛盾的——或是更黑暗的?——迷恋。
这种超越极限的痛苦努力所带来的黑暗欢愉,是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的理论家和诗人一直讨论的有关崇高的问题,有时他们也通过航海这一题材来触及这个话题。例如,我曾谈到,波德莱尔如何迷恋于航行,其《恶之花》就是以长诗《航行》作结。既然崇高性与跨越局限的关联充分体现在航行中,那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诗的结尾出现一艘由死亡掌舵的船只,而为什么在航行中,波德莱尔让船员们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登陆。“去往地狱还是天堂”,愤怒还是理想,“又有什么关系呢”?超越善恶才能找到“新的所在”。[38]
崇高的海洋:只管眼中所见
18世纪的哲学家和作家越来越多地运用海洋来阐释崇高,但是人类活动却从中缺席。当艾迪生在18世纪初把海洋视为崇高之物时,他认为崇高的最好体验就是站在一艘船上。[39] 他写道:“在我看来,对于掌舵的水手来说,躁动不安的海洋是他所看到的最大的动态物,这会给他无穷的想象,从而激发最深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伟大的事物”。[40]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这种从海船上看到的崇高渐渐消失了。
例如,1747年,约翰·贝利提出了海洋有两个方面并不符合崇高的特点。第一,崇高与日常经验是不相容的,并且会被熟悉感所破坏:“我们每天看到天空,因此天空的伟大不会感动我们;而只要在船上待上两三天,就会使我们看到海洋时产生的崇高的愉悦消失殆尽”。第二,在实际的航海中,个人的安危过于重要:“一些暴风雨的描述会让人觉得恐惧,这种被强化的恐惧(当人身处其中时,更是如此)会毁掉崇高”。[41] 伯克在谈论“令人愉悦的恐惧”时,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用伯克的话说:“当危险或痛苦过于迫近,就不能使人产生愉悦,只会产生恐惧;但是如果拉开一些距离,再加上一些修改,它们或许就会让人愉悦,就像我们的日常经验一样”。[42]
将海上作业与海洋的崇高割裂开来,更多地来源于启蒙主义的观点,认为艺术和业务,以及工具理性是分来的。在艾迪生的同时代人,沙夫茨伯里看来,崇高应该与业务断绝关系。因此,他借用归隐田园的“哲学叙事诗人”西奥克勒斯的话来说明崇高的性质:“田野和森林,才是脱离尘世喧嚣的静地”。[43] 在西奥克勒斯眼中,自然的崇高与人类技能无关,而来自生活本身。因此,他在荒芜的山顶找到了崇高的极致,宣称:“看啊!我们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天空,大力神仰起他高傲的头颅,冰雪覆盖,白云缭绕,广阔无垠。寂静在无声地孕育,未知的力量在心中聚集,含混的事物正在苏醒。”[44] 很显然,沙夫茨伯里并没有在崇高美学的语境下去描绘海洋。相反,他画笔下的海洋是荒诞生活的再现,甚至可以说,他是带着憎恶去描画海洋的。因此,他强烈抨击航海小说中对“妖魔怪兽”(“巨大的鱼或怪兽”)的描写,以及“更可怕的人”:“他技艺熟练,手艺非凡,还会讲那些最离谱、最可怕的事情”。[45]
康德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如果把海洋和生物、知识、工作联系在一起,就会阻碍海洋成为崇高的象征。在《判断力批判》(1790)的“分析崇高”中,康德写道:
如果我们想要看到海洋的崇高,就不能用平常思维去思考它,不能用各种知识去看待它,例如,把它看作一个水族群居的广大领域;看作大的水库以备蒸发,这些蒸发用云雾充塞空气以便丰饶陆地;看作一种要素,它虽然使大陆隔离,却又使相互间的交通成为可能。因为这只是一些目的论的判断。我们必须像诗人那样去看待海洋,只管眼中所见,这样才能发现它的崇高。[46]
康德所提出的美学和工具理性的分离,是启蒙主义的核心所在。
在这种启蒙主义观点的塑造之下,崇高美学带来了狂野的海洋,是不受束缚的自然界中令人恐惧的所在。时至今日,只要一提到海洋,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也还是这样一种意象。这种美学观影响之大,当时的批评家和文化历史学家都把崇高的海洋和海洋的诞生视为艺术和文学中的新话题。在《牛津海事书》的前言中,乔纳森·拉班讨论了这个奇怪的现象,即为什么当现代初期航海家遍布全世界时,海洋却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美学想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拉班看来,这意味着18世纪海洋的崇高性是艺术和文学对海洋的再创造。从航海技艺的现代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再创造意味着海洋从与人类活动的紧密关联转向了“空间本身”。[47]
文化历史学家阿兰·柯尔班也谈到了我称之为海洋的升华的过程。在《海洋的诱惑》一书中,他讨论了对自然的海洋的美学欣赏,如何吸引了18世纪后半叶的悠闲旅行者。他写道,在18世纪上半叶,很难发现“有人表达对无尽浪涛的欣赏,或者看到大海的景色就产生愉悦的情感;也从没有人表达过想要感受波涛的力量这种愿望,或者想要用身体去接触冰凉的沙子,或者享受海水的光亮与透明”。[48] 但是从海洋的升华的角度来看,看似来自自然的海洋,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海洋,剔除了手工技艺的知识,也去除了舱底的污水和工作的水手。纳撒尼尔·科尔森所绘制的有关海底泥沙的种类图,集中体现了实用而有条理的航海知识,这在启蒙主义所塑造的平静、空虚、崇高的海洋中消失殆尽了。
黑色波涛起伏、无边无际、无穷无尽、伟大而崇高
当人类活动从海洋中抽离,浪漫主义作家就开始忙着创造各种各样的生物来填充海洋。柯勒律治在《古舟子咏》中塑造了一个由精灵鬼怪统治的古老而神奇的海洋王国。但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即当时真正的海洋世界,在科学、技术、通信和商业等各个方面都是处于先锋地位。对于波德莱尔和兰波来说,海洋冒险已经内在化了,不管是波德莱尔《七个老头子》中把光怪陆离的现代大都市比作“可怕的、无边的大海”,还是兰波《醉舟》中超现实的内在图景,无不如此。在《荒原》的第四部分,通过描述从艾略特的老家科德角出发的一艘船遭遇的船难,艾略特试图用海洋的边缘性来比喻现代性对于进步的追求是毫无结果的。然而,庞德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把海洋视为现代性的领域,认为艾略特这部分描写很糟糕,建议删去,最后艾略特只留下了以“腓尼基人弗莱巴斯”开头的八行,把海洋视为古老的王国,这一点和柯勒律治不谋而合。
拜伦自己熟知一些海洋技艺,他是英国航海家约翰·拜伦的孙子,约翰·拜伦曾著有《维吉号船难》,描写了安森爵士的环球航行(1740—1744)。然而,拜伦诗中的海洋也是脱离了人类技艺的,他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这样写道:“黑色波涛起伏;无边无际,无穷无尽,伟大而崇高/——永恒的意象——/无形的王冠。”[49]
当浪漫主义者把现代初期身怀技艺的海洋英雄人物放置于抽离了人类技艺活动的海洋中时,他们其实是把海上作业转化为了存在主义式的奋争。这当然也是拜伦笔下海盗形象的转变。紧随着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在拜伦笔下,海盗的暗语变成了存在主义式的自由——并非自由航行于世界之海的不道德的权利,而是有关生命、自由、幸福,以及追求(别人的)财富的不受限制的权利:
在暗蓝色的海上,海水在欢快地泼溅,
我们的心如此自由,思绪辽远无边。
广袤啊,凡长风吹拂之地、凡海波翻卷之处,
量一量我们的版图,看一看我们的家乡!
这全是我们的帝国,它的权力横扫一切,
我们的旗帜就是王笏,所遇莫有不从。
我们豪放的生涯,在风暴的交响中破浪,
从劳作到休息,尽皆欢乐的时光。[50]
在这种民主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推动下,海盗令人发指的恶行变得沉默无语。拜伦笔下的海盗有时还呈现出罗宾汉式的侠盗式英雄形象。
自从拜伦将海盗塑造成存在主义式的英雄,这种形象就一直激发着从兰波到威廉·巴勒斯的后浪漫主义文学。[51] 当后现代主义高歌无政府主义的叛乱,去领土化、流动性时,这股后浪漫主义思潮达到了顶峰,集中体现在20世纪末的一份海盗宣言,即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哈基姆·贝提出的《临时自治区、本体论无政府主义以及诗意的恐怖主义》。[52] 然而,尽管哈基姆·贝的海盗们反对启蒙主义的认识论,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海洋仍然是具有浪漫主义崇高性的平静而虚空的大海。
暴风雨本可以带来些许慰藉
海洋的升华不仅出现在文学中,也出现在视觉艺术中。1712年,艾迪生建议作家们学习“那些伟大的画家,不仅画花园、树林、草地,还常常将笔墨投向大海”。[53] 艾迪生这里指的是17世纪蓬勃兴起的海洋题材类绘画,这时的航海活动也达到其顶峰。在荷兰海洋画家小威廉·梵·德·维尔德的画作《迎风向前的荷兰小船》(1672)中,大自然、狂风和波涛的力量与水手操控船只的技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小威廉·梵·德·维尔德的儿子科尼利厄斯的画作《暴风雨中驶向岩石海岸的船只》(1703)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大海形象。科尼利厄斯住在英国,是艾迪生同时代的人。这两幅画不仅准确描绘了船只的类型、波涛的形状、海水的质地,还细致勾画出操控船只的状态,展示了水手在恶劣天气中采用的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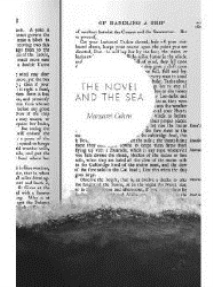
图1 《小说与海洋》原著书影

图2 《小说与海洋》原著作者玛格丽特·科恩

图3 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
我们在这些画中看到的有关天气和水手技艺的详细信息,在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译者注)的画作《海边的僧侣》(1809)中消失无踪了。在这幅画中,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就是海洋和天空,海边的僧侣孤独地注视着这一切。但是海洋和天空并不是呈现人类技艺活动的舞台,而是虚空的自然,留待观画者自己去想象。弗里德里希刚开始画了两艘船,但最后还是把船去掉了,以增强画面的孤寂感。他的选择是成功的,玛丽·冯·库盖尔耿1809年对一个朋友评论此画说:“这幅画再现了天空的无边无际,没有风、没有月亮、没有暴雨——事实上,暴风雨本可以带来些许慰藉,至少可以让人看到生命和运动。在无休无止的海洋中,没有船只,没有舰队,甚至没有海怪,在沙滩上连一片草叶也找不到,只有几只海鸥从空中飞过,让画面更加孤寂和荒凉,让人心悸。”[54]弗里德里希的画中所体现的虚空的海洋正是浪漫主义的风格,不仅脱离了人类技艺,也使海洋风景画中的信息功能丧失殆尽。航海家们往往通过海洋风景画来记录航行途中看到的未知的海湾景色,例如威廉·霍奇斯笔下的风景画。他是库克船长第二次航行中的画家,这幅画是《黄昏中的海湾》。
【注释】
[1]T.S.Eliot, The Wasteland, A Facsimile and Transcription, ed. and intro. Valerie Eliot,New York: Harvest Books, 1971, p.136.
[2]参见John Ruskin, Modern Painters, in Elibron Classics, Vol.4,Adamant Media, 2005. 在London:George Allen, 1906版基础上的再版。这两个短语贯穿整个章节。
[3]Longinus, On Great Writing (On the Sublime), trans. G.M.A. Grube,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1957,p.13.
[4]Longinus, On Great Writing (On the Sublime), trans. G.M.A. Grube,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1957,p.18.
[5]同上,第19页。朗吉弩斯谈论的修辞手法包括夸张:“在强烈情感的重压之下……表达出当时的伟大情境”(第50页)。对于不符合语法规范的散句,他说道:“这些句子不相连接,却显得更急速”(第31页),“语言和思维都打破了常规”(第33页)。当夸张而绝妙的细节侵入理性的分析,修辞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就会消融:“我们自然而然听信了较有感染力的话,所以我们被吸引着,从推理方面转向想象所产生的魅力,于是事实的论证就仿佛笼罩在灿烂的光环中”(第27页)。
[6]Nicolas Boileau, Réfl exions sur Longin (Réfl exion 10), in Oeuvres de M. Boileau Despreaux (Amsterdam:D.Mortier, 1718), vol. 1, 136. 下面两段中的引用也出自这篇文章。
[7]当塞缪尔•芒克在20世纪重新阐释崇高时,他最早指出了这种转变,见Samuel H.Monk, The Sublime:A Study of Critical Theor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35.
[8]Ian MacLaren, “Arctic Exploration and Milton’s ‘Frozen Continent.’” Notes and Queries new ser.31 (1984):325-326. 又见Anne-Julia Zwierlein, “Satan’s Ocean Voyage and 18th-Century Seafaring Trade,” in Fictions of the Se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Ocean in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d.Bernhard Klein,Farnham, Surrey, UK: Ashgate, 2002, pp.49-76.
[9]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ed. Gordon Teskey, New York: W.W.Norton, 2005, book 2, pp.588-595.
[10]同上,第二卷,第571页。
[11]在《史诗与帝国》一书中,大卫•昆德指出,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改变了史诗中对水手英雄形象的描写,例如从奥德修斯到卡蒙斯笔下的达伽马。对于昆德来说,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在于把撒旦和他的手下塑造成“商人冒险家”,控诉了“欧洲人的扩张和殖民主义”。在我看来,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尽管水手和商人常常互为搭档(因此,寻找西北航道也就是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之路),但是他们彼此是不可取代的,不管是在文学作品中他们的形象,还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作用。在把撒旦塑造成一个水手时,弥尔顿将水手技艺融合其中,并潜在地颠覆了宗教世界观。见David Quint, Epic and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65.
[12]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194—195页。
[13]同上,第一卷,第76—78页。
[14]同上,第一卷,第180页、第184页、第190—191页。
[15]同上,第一卷,引自第257行,第296—300页。
[16]同上,第一卷,第292—294页。
[17]同上,第一卷,第239—241页。
[18]同上,第一卷,第242—245页。
[19]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13—16页。在约瑟夫•艾迪生的诗《论最伟大的英国诗人》中,作者称弥尔顿的《失乐园》“大胆而崇高”,可以激发“恐惧和愉悦”。见The Annual Miscellany for The Year 1694, London: Jacob Tonson, 1694, p.322. 有关讨论弥尔顿在18世纪上半叶对崇高风格的影响,见Leslie E.Moore, Beautiful Sublime: The Making of Paradise Lost, 1701-1734,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最初由理查德•范肖于1655年翻译成英文,弥尔顿对这首诗很熟悉。见John T. Shawcross, “John Milton and His Spanish and Portuguese Presence,” Milton Quarterly 32,no.2(1998), 41-52, p.42.
[21]Luís Vaz de Camões, The Lusíadas, trans. Landeg Wh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Canto V, stanza 26, lines 5-8.
[22]只有在描写达伽马的航行时,作者才加入了浪漫传奇的叙述。在描写伊斯兰世界以及众神之战时,卡蒙斯的语言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23]弥尔顿,第一卷,第286—291页。
[24]有关弥尔顿和伽利略的关系,不管是书面记载的,还是实际生活中的,可以参见George F.Butler,“Milton’s Meeting with Galileo: A Reconsideration,” Milton Quarterly, 39, no.3(2005):pp.132-139.
[25]我的这一想法得益于尼可莱•司丽卡。在2009年12月1日的邮件中,他提到这句诗由于歧义而产生的另一种解读可能。他说道:“或许这是弥尔顿在提到望远镜这种先进的观察仪器时,试图抑制洋洋自得的情绪;或许是洋洋自得的读者认为伽利略正从均势的角度望着明月/月轮/盾牌/撒旦的盔甲;或许与之相反的是,还有一些读者撒旦通过望远镜望着伽利略,由此隐喻现代人受制于自己发明的技术(这与简单化的法兰克福学派一脉相承);或许还有一些读者认为这是弥尔顿有意识地写成充满歧义的句子,从而凸显现代化技术的难题所在(这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引申出来的更为精妙的观点)”。
[26]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26页。
[27]Jonathan Richardson, An Essay on the Theory of Painting (1725), cited in Andrew Ashfi eld and Peter de Bolla, eds., The Sublime: A Reader in British Eighteenth-Century Aesthetic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此处及以下的引用来自第48页和第47页。
[28]与之相似的是,约瑟夫•特拉普把崇高的动力视为现代人征服时空的先在极限:“自然促使人类形成了不断探索的才能,使人类领悟并敬畏自然。人类并不是无意义的旁观者,而是参与到自然的种种活动中……广阔的宇宙并不能限制人类的想象,人类将思想延伸到其他世界,只有在无限中才会迷失”。特拉普还引用了托马斯•克里奇翻译的《卢克莱修》中的句子:“他的思想强劲而活跃/超越了世界的极限”。参见Joseph Trapp, Lectures on Poetry (1742), cited in Ashfi eld and de Bolla,p.56.
[29]Alexander O.Exquemelin, The Buccaneers of America, trans. Alexis Brown, intro. Jack Beeching,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0, p.89.
[30]同上,第107页。
[31]Daniel Defoe (用的是笔名Captain Johnson),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 (1724), ed. Manuel Schonhorn,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1999, p.85.
[32]John Dennis, The Grounds of Criticism in Poetry (1704), cited in Ashfi edl and de Bolla, p.38.
[33]Joseph Addison, The Spectator, no.489, Saturday, September 20, 1712, cited in Ashfi edl and de Bolla, p.69.
[34]凯瑟琳•加拉赫也指出了这种想象活动和实际工作之间的关系:“粗俗的作品会带给人痛苦,而高雅的作品则会带给人恐惧。”加拉赫还指出,这种关系把“诗人的痛苦和劳动者的不幸结合了起来”。见Catherine Gallagher, The Body Econom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
[35]乔纳森•兰姆在《南海航行中的自我保护,1680—1840》一书中,指出“自我保护”是伯克的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其他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家常用的一个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是现代早期水手们叙述自己在海洋的边界地带如何自我保护与生存所形成的。但是兰姆并没有把读者这种自我保护的阅读经历和崇高联系在一起。兰姆感兴趣的是,航海小说如何推动了现代主体性,他十分关注自我保护与“不可言喻”的关系。“不可言喻”是17世纪法国新古典美学理论用来描述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体验。“不可言喻”影响了布瓦洛对崇高的解释,也使兰姆关注现代主体性。在评论伯克的《福克斯的东印度公司法案》的演说时,萨拉•苏莱瑞把崇高的难解性与欧洲人开拓全球航海未知领域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这一演说发表在伯克《哲学探究》一书成书25年之后。用苏莱瑞的话说,“演说‘虚伪而含混的表述方式’说明伯克多么费劲地想阐释清楚,当印度的历史文化,甚至只是地理环境,在殖民者眼中是一种威胁时,英国殖民话语如何必须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见Sara Suleri, The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7.
[36]James Cook, The Journals of Captain Cook, selected and edited by Philip Edwards, New York: Penguin,2003, p.168.
[37]同上,第166页。
[38]Charles Baudelaire, “Le Voyage,” from Les Fleurs du mal, in Oeuvres Completes, Paris: 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 1975, vol.1, p.134.
[39]艾迪生引用了一段有名的为水手祈福的祷告,来说明什么是崇高:“他们乘船入海,与狂风大浪打交道:他们看到了上帝的杰作,隐藏深处的奇迹。上帝呼风唤雨,掀起狂浪。他们一会儿被冲到天上,一会儿被打入海底,他们的灵魂在困境中挣扎。他们来回摇晃,像醉汉一样踉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他们呼唤上帝,渴求上帝把他们带出灾难。于是上帝让暴风雨停歇,海浪归于平静。他们又高兴起来,一切又归于平静。上帝把他们带到了向往的港口。”艾迪生认为,海上航行使他找到了朗吉弩斯所指的崇高:“我几次出海,都遇上了暴风雨。那样的场景往往使人想起古代诗人的海洋诗歌。我记得朗吉弩斯高度赞赏荷马描写暴风雨的场景(前文谈到朗吉弩斯的时候,引用了该诗)荷马把描写暴风雨的场景汇集在一起,最能使人产生恐惧的想象,而这些暴风雨在现实的航行中确实会发生。”见Joseph Addison, The Spectator, no.489, Saturday,September 20, 1712, cited in Ashfi edl and de Bolla, p.69.
[40]同上,第69页。
[41]见John Baillie, An Essay on the Sublime (1747), cited in Ashfi edl and de Bolla, p.90, pp.96-97.
[42]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ed.Adam Philli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6-37 (Part I, 7).
[43]Anthony Ashley Cooper,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from Characteristicks, cited in Ashfi edl and de Bolla, p.72.
[44]同上,第76—77页。
[45]沙夫茨伯里对海洋小说的抨击值得详细引用,不仅因为其抨击的言辞激烈,而且因为他的批判道出了海洋小说的所有细节特点:“我们对随便哪位冒险家的旅行回忆录都那么着迷,想象自己成为书中的角色,或是变成全知全能的天才。书还没翻几页,我们就对书中描写的事情兴奋不已。作者或是在泰晤士河岸乘船出发,或是把行李先送到格雷夫森德,总之我们的注意力是被他吸引了。如果要走得远点,那么他会到欧洲转一圈。耐心一点,我们就会听到各种旅店的名字、各种船只的名字和各种天气情况。此外,还有作者的一日三餐、生活习惯,以及陆地上和海洋上遇到的危险和不幸。就这样,我们随着他一起,充满了热情和希望,直到他遇到了大事情,比如巨大的鱼或怪兽。除了妖魔怪兽,他们的笔触还指向那些更可怕的人。因为这一类作者往往把自己写得无所不能,最要命的是,他们都会讲那些最离谱、最可怕的事情。”Anthony Ashley Cooper,Earl of Shaftesbury, “Soliloquy: or Advice to an Author,” in Characteristicks of Men, Manners,Opinions, Times, London: John Darby, 1711, pp.1346-1347.
[46]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and intro. J. H. Bernard,New York: Hafner Press, 1951,pp.110-111, “Analytic of the Sublime” 29.
[47]拉班认为艾迪生提出的“令人苦恼的大海”是一个例外,他将之称为“现代浪漫主义海洋的鼻祖。突然间,海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出现在画面的前景部分”。Jonathan Raban,“Introduction,” The Oxford Book of the Sea, ed. Jonathan Rab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8.
[48]见Alain Corbin, The Lure of the Sea: The Discovery of the Seaside in the Western World 1750-1840, trans.Jocelyn Phelps,New York: Penguin, 1995, p.53. 柯尔班指出,17世纪的荷兰海洋绘画一方面传递各种海上信息,另一方面把海洋视为危险的源头。
[49]George Gordon, Lord Byron,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i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Lord Byron,Boston: Houghton Miffl in, 1905, p.82.
[50]George Gordon, Lord Byron, The Corsair, i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Lord Byron, Boston:Houghton Miffl in, 1905, p.338.
[51]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 p.85.
[52]彼得•威尔逊是哈基姆•贝的知己,他也写有关海盗和逃犯的故事。
[53]Addison, The Spectator, 1712, cited in Raban, p.81.
[54]Marie von Kugelgen, letter to Friederike Volkmann, June 22, 1809. 英译文见艺术画廊网址:http://www.wga.hu/frames-e.html?/html/f/friedric/1/105fried.html (2008年1月)。德语原文见Hilmar Frank,Aussichten in Unermessliche: Perspektivitat und Sinnoffenheit bei Caspar David Friedrich,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4, p.8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