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 鹏
内容提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权力和利益基础之上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权力”与“利益”的增减发生着动态的变化。若中央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内敛,则产生中央集权关系;若中央政府“权力”、“利益”均内敛,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则产生地方分权关系;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则产生协作伙伴关系。本文在分析上述三种动态关系的基础上,运用跨域治理的基本理论,对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关系提出若干协调路径。
关键词:跨域治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动态关系;协调路径
一、引 言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的态势。以往学界大多以全国疆界的“中央集权”或辖区割裂的“地方自治”作为探讨如何解决公共事务的基础,地方政府在实践中也是基于单元行政区域界线,遵循“画地为牢”和“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甚少关注行政区划边界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2]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信息剧增的影响下,传统人类现实社会生活结构已发生改变,致使现今公共问题与社会需求日益复杂。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跨域公共服务供给,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运行同向,协调一致。然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中央政府在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决策制定等方面未能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实施起来必然遭遇阻碍,招致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重重挑战乃至抵制。2007年5月爆发的太湖“蓝藻危机”和随后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动的“流域限批”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推向极致。[3]因此,现阶段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调节失衡的问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远期和当前、整体和局部的利益冲突的反映,而利益博弈的结果必然对跨域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在当前大力强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背景下,面对与地方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相悖的、容易出现“集体行动逻辑”尴尬后果的跨域公共服务供给,有必要从跨域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关系,以有助于破解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共同难题,推动我国提升跨域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
二、跨域治理的基本内涵
面对全球化与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世界各国政府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无不致力于充分整合自身资源,大力提升政府的治理绩效。因此,诸如政府再造、地方分权自治及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参与等议题,成为政府公共事务运作的重要改革方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结构功能亦随之发生改变,在“全球性思考、本地化行动”(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的思维架构下,地方分权与自治等概念逐步落实于府际关系的权力划分中,中央政府开始下放若干支配权力,并扬弃过去相对优越的上下互动关系,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限,以此提高地方政府解决日益复杂化的跨行政区域公共事务与问题的能力。
然而,上述府际关系的权力相对位移,以及地方政府自治权力的增大,并不意味着“区域公共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地方政府必须摆脱过去本位主义的僵化思维,超越各自行政区域的范畴限制,依据自身禀赋进行跨域合作协调,才能够克服“区域公共问题”的外溢效应。因此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有效的协力合作,进而解决复杂的跨域公共事务,将是未来府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跨域治理即是在如此的环境转变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地方政府采用的新型治理途径。
跨域治理(across boundary governance)的内涵包括了地理空间上的跨政区联合行动,组织单位中的跨部门交流,传统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民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横跨各种政策领域的专业化合作,是一种超越分歧、跨越边界、以协同互动为目的的新型治理模式。[4]在本质上,跨域治理区别于传统意义上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模式,而倡导一种多元和整体治理的模式,一方面可以通过地方民众和当地团体“自下而上”所形成的意见,扩大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规模,另一方面适当地引进民间的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可以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5]具体来说,政府将改变长期以来对于资源配置及提供公共服务处于垄断地位的单中心统治结构,通过职能与角色的制度性安排,下放权力至市场或公民社会共同分享和承担之后,最终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所组成的多中心治理网络格局。[6]
跨域治理融合了多层次面向的治理形态,强调中央政府扮演中立调解和宏观资源配置的角色,与其相似的概念有美国的“都会区治理”、日本的“广域行政”、英国的“区域治理”和“策略社区”等。跨域治理的对象具有公共性,它的实施有利于推动政府间合作、部门间协作以及政府与民间的协同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跨域治理是地方政府的迫切要求,也是未来公共治理的发展方向[7]。
跨域治理建立在区域治理的基础上,后者是一种以协力(collaboration)为中心的治理机制,其实践不仅是跨域行政区域的实际空间范畴,更是具体整合政府部门、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事务权责,据此建构虚拟空间的协力合作与互动伙伴关系。[8]主张协力合作是跨域治理的有效方式,不同的协力方式与治理角色,将产生不同的治理形态。表1显示的是跨域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协力关系,其互动方式是从非正式到正式,组织结构是从松散的网络到严密的科层体制,供给者之间的合作规则是从彼此的共识趋向于明确订定的组织规范,而治理的效果分别是网络、伙伴关系、联盟与整合等四种跨域治理形态。
表1 跨域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协力关系

资料来源:Sullivan H,Skelcher C.Working Across Boundaries:Collaboration in Public Service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权力和利益基础之上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方式[9]。由于政治域中政府的行动取向没有普适性法则,为适应动态的行政环境,政府会采取权变的行政策略,其策略选择的背后就是各种“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博弈过程。因此,本文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权力”与“利益”的增减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具体来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关系包括中央集权关系、地方分权关系和协作伙伴关系三类。若中央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内敛,则产生中央集权关系;若中央政府“权力”、“利益”均内敛,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则产生地方分权关系;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则产生协作伙伴关系(见图1)。
(一)中央集权关系
中央集权关系源于美国政治的Hamiltonian传统,其意在追求一个具有强大行政组织的积极政府,并认为公共行政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实现公共目标[10]。传统中央集权制(centralization)视国家政治为一整体,一切权力与一国治权皆为中央所有或为中央政府所掌握,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分设的派出机关,其存在的功能仅为听命于中央处理或执行事务的代理角色。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看,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和过度的经济差距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加以解决,市场竞争只会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地区发展更加迅速,而落后地区则更加落后。[11]同时,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很难自动发生有效的协调机制,仅依靠地方政府自身无法解决区域差异性问题。因此,必须依靠中央政府和中央集权来宏观调控与统筹发展,平衡各地方的财政能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图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关系
中央政府通常通过提高中央征税集权程度来扩大其“权力”和“利益”。从静态角度看,税收的征收率决定于征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乘积;但从动态角度看,税收努力对征收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税收努力及其征税比重,可以构建政府体系的总税收函数[12]:

其中,TEt、 (*)、
(*)、 (*)分别表示第t期政府总税收努力、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和中央政府税收努力,αit、βt分别表示第t期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收比重,
(*)分别表示第t期政府总税收努力、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和中央政府税收努力,αit、βt分别表示第t期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收比重, (*)表示第t期中央政府对第i个地方政府的评分函数,cpit表示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强度,
(*)表示第t期中央政府对第i个地方政府的评分函数,cpit表示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强度, 表示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标,并且
表示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标,并且 。
。
中央政府由于和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因而税收函数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中央政府通过加强征税集权( (*)),将总税收(TEt)在不同地区间进行分配,尽力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将总税收(TEt)在不同地区间进行分配,尽力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地方政府官员为实现政治晋升,则会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的考核指标。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会在保持基层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财政手段,通过减税和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加快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以便提高其政绩,增加中央政府对其考核的分数(
)。地方政府官员为实现政治晋升,则会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的考核指标。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会在保持基层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财政手段,通过减税和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加快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以便提高其政绩,增加中央政府对其考核的分数( (*))。但这种“诸侯争霸”的行为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cp it)越激烈,其税收努力(
(*))。但这种“诸侯争霸”的行为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cp it)越激烈,其税收努力( (*))就会越低,从而不利于征收率的提高。
(*))就会越低,从而不利于征收率的提高。
因此,加强中央集权,增加中央政府的征税比重(βt),可以提高政府体系的总税收。中央政府的征税集权程度越高,其对税务机构征收能力建设的规划和实施能力就越强,并会通过“示范效应”来促进地方政府加强征收能力建设。例如我国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出于成本等考虑,往往不会积极进行征收能力建设,导致政府体系的税收努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征税集权并建立了直属的税务机构,各地的征收能力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对于贯彻落实征收能力建设的遵从程度也相应提高。
可见,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扩大其征税权限而实现了“权力”和“利益”的外扩,地方政府则“被动”地接受征税权限的缩小,从而促使“权力”和“利益”的内敛。在短期内,中央政府通过提高政府体系总税收努力的方式来提高征收率,在长期则通过对征收能力建设规划和实施能力的增强来提高政府体系的征收能力,并导致征收率的进一步提高。从跨域治理的决策角色看,中央政府发挥着“跨域公共服务输送”的统筹功能,其所采取的政策工具是通过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但这样的集权设计往往使中央政府面临“制度的危机”(crisis of institution),中央政府在统筹不同行政区域时无法面面俱到,不仅容易丧失因地制宜的跨域治理机会,而且可能产生政府专制或个人独裁。另外,由于中央政府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地方政府官员容易陷于唯命是从的被动地位,态度消极而保守,不易发挥创新与自发精神,从而导致行政官僚化和工作效率的降低。
(二)地方分权关系
地方分权关系源于美国政治的Madisonian传统,其对中央政府的行为有所保留,主张权力和利益应分散于多元利益主体中。地方分权关系是在经济社会完成快速增长、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的背景下产生的。当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的时候,就需要通过重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地方分权制(decentralization)有利于克服传统中央集权制所面临的制度性危机,即不再视国家政治为一整体,而倡导将权力和治权的一部分授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仅处于监督的地位。
地方分权主要表现在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上,也即地方政府逐渐拥有了对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赵志耘和郭庆旺的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是纵向府际关系演进的世界大趋势,但在不同类型国家,其诱导机制却不尽相同。[13]发达国家推行财政分权是为了在“后福利国家”时代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务;在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财政分权源于人民追求民主的政治压力;在非洲国家,推行财政分权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统一;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财政分权旨在挣脱治理无效、宏观经济不稳定和低经济增长的陷阱;经济转型国家倡导财政分权,则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直接结果。一般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和公共服务提供成本,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权有助于强化地区间竞争和公众政治参与,从而有助于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提高效率。[14]另外,政府效率提高会导致公共服务需求增加,且公共服务若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效应,或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公共池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那么财政分权也会导致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加。[15]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官员的激励形成的。激励不仅来自政治晋升的诉求,而且来自其可支配“资源”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追求。[16]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和以GDP增长为政绩考核的政府竞争这两种体制约束下,各地区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加强烈的扩大预算外收入的激励,于是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支配。[17]事实上,由于各地区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不同,财政分权下各地方政府所受激励和约束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形式的变化也会使得地方政府表现出“掠夺型”(predatory)、“勾结型”(collusive)和“强化市场型”(market-augmenting)等多样化的行为类型,而地方政府行为的多样性将导致各地区市场制度发育和改革创新的差异,进而对各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上述地方政府不同的行为类型,主要取决于生产资源的分布状况。如果某一地区生产者之间很难达成合作抵制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将可能导致“掠夺型”地方政府行为的出现;如果生产资源在该地区分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并且地方政府从不同类型的生产者之间所取得的财政政治收益也不相同,那么将会导致“勾结型”地方政府行为的出现;如果一个地区生产资源分布相对平均、有效,并且该地区生产对于产权保护程度非常敏感,地区生产者之间在界定和保卫产权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将导致“强化市场型”地方政府行为的出现。[18]
虽然财政分权通过对官员的激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但对地方公共服务却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地方公共服务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其涉及范围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即“物质性基础设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即“社会性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19]。Holmstrom和Milgrom的研究认为,面对多重任务委托,或者面对多维度工作,代理人往往会强烈关注那个最容易被观察、最容易显示绩效的工作,而忽视其他工作或者工作的维度。[20]由于在我国政治体制中采用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晋升考核形式,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促使政府官员的利益更加能够代表政府利益。[21]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去把更多资源配置到物质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方面,从而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获得晋升机会,而关系到民生福利的、属于“隐性政绩”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却因难以用硬性指标衡量而不受重视。
图2显示的是最优(first-best)、财政分权与财政集权(fiscal centralization)三种配置情形下,地方政府投资物质性基础设施(P)与社会性基础设施(S)的比较示意图。其中,P和S相加等于政府支出E,即P+S=E,ES和E H分别表示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下的政府支出。对于各个地方政府i,从最优配置( ,
, )、财政分权下的配置(
)、财政分权下的配置( ,
, )和财政集权下的配置(
)和财政集权下的配置( ,
, )可以明显看出,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S)是最少的(
)可以明显看出,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S)是最少的( )。财政集权下,虽然地方政府对物质性基础设施(P)的投资是最少的(
)。财政集权下,虽然地方政府对物质性基础设施(P)的投资是最少的( ),但由于中央政府掌握了较大的财政权力,从而保证了一定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但由于中央政府掌握了较大的财政权力,从而保证了一定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但
,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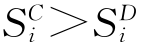 )。
)。

图2 三种配置情形下地方政府对物质性基础设施与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较
资料来源:Qian Y.Y.,Roland G.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Vol.88,No.5,pp.1143-1204.
以财政分权为代表的地方分权,主张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提供适合于当地居民的地方公共服务,并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进行财权的划分,这是符合效率条件的。但现实中地方公共服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过度的分权还造成国家分离主义的兴起以及地方自治能力不足的治理失败情形,并且地方政府往往只关注本行政区域内的问题,对于跨部门、跨区域事务着实无法单独处理与解决。[22]究其原因,一是没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收入自主权,转移支付体制也不完善和规范;二是省以下各级政府财政权责划分不清,基层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只能一再压缩地方公共服务的支出规模;三是高度垂直集权的政府行政体制,对地方公共服务财政体制上的分权形成阻碍,导致下级政府更重视上级政府的命令而忽视民众的要求;四是权力和利益的扩大,使得地方政府获得超常规发展的动力,从而滋生“政府企业化”和“政府逐利化”等变异行为。[23]因此,在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均有失灵问题的方法上,强调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跨域治理的伙伴关系,以及加强地方政府的自治能力尤为重要。
(三)协作伙伴关系
协作伙伴关系是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所形成的。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权力持续下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地方主义”的兴起,面对日益增多的跨域性公共问题,垂直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建构紧密的“协作伙伴关系”来加以解决。这种跨域治理的机制最主要的特征体现在“中央控制性”与“地方自主性”之间的张力。在“中央控制性”方面,中央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地方政府利益冲突的协调者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推动者。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其能够从宏观大局出发,对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进行统一规划;同时也可以通过推动偏远地区的合作,使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达到均衡状态,以确保全国一致性政策的推动。
“地方自主性”则强调地方政府能否充分响应当地民众的偏好与需求。中央政府通过采取行政性放权的办法,将经济的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分配给地方政府,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成为辖区内共有经济的真正剩余索取者和控制者,因此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空前增加。地方政府已不再是被动贯彻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附属组织,而是逐渐成为微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和直接控制者,从而导致中央政府相当程度上减弱了自己的总体能力,并且在机制上失去了控制和调节地方政府最为有效的手段。
以上两种力量的推拉之间,架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垂直关系,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限与资源规模,同时也左右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协作伙伴关系中的行为表现。对于跨域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由于各自利益考虑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行为选择。中央政府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社会的普遍利益,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而地方政府有着更为复杂的利益考量,既有与中央政府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又有相对独立性,即最大限度地谋求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利益,并通过扩张行为自主性的方式,突破中央政府的政策性约束。在以目前的财税体制为基础所确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利益格局中,地方政府是一个有着独立的利益诉求和广阔利益空间的“政权经营者”。其利益诉求主要表现为短期内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使得地方政府在跨域治理中会权衡自己的利益得失,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的标准和最终的目的。显然,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极有可能使其偏离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整体目标。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还是存在共同利益的。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关系,它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单独行动达到目标,而需要依靠对方的资源。[24]这些资源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合法性权威、资金、专项技能、知识以及信息等,如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授予,中央权威的稳定有利于地方政府的政治统治;而中央政府必须依靠地方政府来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事务,不可能事必躬亲。从这一角度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利益博弈,而博弈的方式和结果则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控制能力。在相互依赖的情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等方式来寻找互惠的解决方案,获取各自的目标。
需要意识到的是,这种协作伙伴关系只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一种理想状态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应该包括三个层次:责任分担的中央集权关系、财权划分的地方分权关系以及激励相容的协作伙伴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只有责任分担和财权划分还是不够的,因为一种理想化的中央和地方府际关系不仅仅是责、权划分问题,更重要的是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积极、主动的相互配合。而要实现这种互动的协作伙伴关系,就必须提供内恰的激励相容。
所谓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指能够使行为一方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实现合作双方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的制度安排。[2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中央地方府际关系的摸索尝试,我国已经逐渐理清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思路。1994年分税制改革,初步实现了责任(事权)的明确划分和财政的合理分权,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逐步相互依赖。但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内恰的激励相容机制还不够成熟、稳定,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始终围绕着“集权—分权”打转,传统财政体制机制的弊病也逐步显现。这种府际关系失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①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收入权,更没有自主的支出决策权,地方对中央高度依赖。中央政府在信息方面的劣势会增大资源误配置的机会和增大财政运转成本,而且会忽略地方居民的偏好特征。②地方财政收入上缴和实际所得不对称,挫伤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26]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政府权力的认知往往局限于分配性的专制力(despotic power),忽视了权力关系双方通过合作协商完成集体性任务的建制力(infrastructural power)。[27]
表2显示的是政府专制力与建制力的比较情况,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过度集中于专制力方面,将使二者关系变成单一维度的分权关系和纯粹的对立关系,负向的激励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向的激励则趋于萎缩。但是,建制力的“正和”性质,却可以实现权力双方的“相互增权”(mutual empowerment),即双方协作的行为使得各自实现自身意愿的可能性都增大了,也就是双方的权力和利益都扩大了。因此,建制力的相互增权效果使其有助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达成内恰的激励相容,并在信息传递、政策执行等方面转向协作,实现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从而有利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协作伙伴关系。
表2 政府专制力与建制力的比较

资料来源:张欢.突发公共事件下的中央和地方府际关系审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21-131.
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动态关系的协调路径
在府际关系的实践和制度安排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因此,为了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关系,并为其他府际关系的全面重理提供先决性的制度安排,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路径对中央与地方的动态府际关系进行协调。
(一)科学划分跨域治理的事权和财权,建立选择性的权力分配机制
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以来,主要解决了中央政府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责、权、利配置的问题,而对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却远未涉及。在跨域治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多数省级地方政府模仿中央政府与省级地方政府的财权划分比例来处理省级地方政府与地市级地方政府的财权划分。经过一系列分权改革,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了明显扩张,其权力涵盖土地和水资源使用、国有企业改制与转让、城市建设与经营等各个方面。但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官场政治“潜规则”,使得下级地方政府在财权划分比例、税种归属等问题上,很难有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多数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上级政府的财权分配,这样就容易造成财权不断上移,事权却不断下放,基层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基本上陷入了“吃饭财政”的困境。在这样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地方代理者”这一角色上缺位,往往通过权力和资源的运用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并不承担或只是部分承担整个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和不良后果,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积极参与跨域治理也只能是一种奢望。因此,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关系,首先必须改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现象,进一步界定和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务管理范围及相应拥有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政府在跨域治理中的积极性,使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相对称,在承担执行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治理区域经济的同时,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益”。
目前,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收放还具有欠规范的地方,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割呈现非均衡状态。中央政府为确保政令畅通往往偏好于集权,地方政府为保护和扩展自身利益则倾向于分权。中央政府过分集权但不拥有足够的支配权力,而地方政府没有得到处理地方事务的足够的权力,或者是地方政府在事实上得到了一部分权力,但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使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政策变形,甚至完全失效。[28]于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中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一种与中央政府相博弈的力量。显然,在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必须改变当前地方政府权力由中央政府单方意志决定的局面,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一种中央政府选择性集权、地方政府选择性分权的体制,以适应跨域治理的需要。具体可以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将总揽内政、外交、国防和宏观经济调整等职责交由中央政府,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及主导作用;将处理和发展地方公共事务,负责本地区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治安等因地制宜性的职责交由地方政府,真正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动态平衡。为了保证地方政府用好下放的权力,跳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在建立和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选择性分权机制的同时,还应健全地方政府的约束机制,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力运用的监督与控制。
(二)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合理确定中央政府的激励强度
前文已述,地方政府官员为实现政治晋升,会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其行为和决策是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在此假设下,社会利益最大化不是地方政府决策的根本目标。从现实来看,传统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是“以经济增长论英雄”,具有明显的“GDP导向型”倾向,即政绩多少看产值,贡献大小看税利,至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如实际收入、就业水平、住房条件等情况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上级政府的青睐而在有限任期内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并且形成了“经济目标为主导的压力型体制”。为此,必须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矫正和克服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改变单纯以经济增长指标为导向的考核标准,取而代之以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质量、公众满意度、居民幸福感、人民是否得到实惠等作为衡量和考核标准,进而从根本上纠正地方政府博弈行为的出发点,减少和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
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重视物质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视难以用硬性指标衡量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其根源还在于中央政府的激励制度。中央政府根据不同行政区域的经济绩效来给予地方政府官员不同的待遇,由于后者知晓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即知晓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增长率会给自身带来何种待遇,因而会选择适当的努力程度使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一个特定的水平。[29]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应当精心设计激励制度,合理确定激励强度。当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时,地方政府官员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动力会充分膨胀,往往不惜一切代价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此时中央政府应当缩小激励强度,防止经济出现过快过热增长,危及社会各种安全。反之,如果中央政府的激励强度不足,则在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官员考虑到本地区经济增长过快会对自身待遇产生不利影响,于是倾向于碌碌而为,内敛其“权力”和“利益”,并且缺乏足够动力发展当地经济,其所在行政区域的经济增长率必然要小于没有中央政府激励时的增长率。
(三)构建利益主体合理博弈的均衡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地方利益表达渠道
在跨域治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考虑。中央政府是在全国范围内总揽国家政务的机关,它在国家的政治管理体系中处于最高、最核心的地位,关心整体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而地方政府是在国家特定区域内,依宪法或中央法令规定,自行处理局部性事务但无主权的地方统治机关,追求本区域的最大经济利益。同时,地方政府在行为中通常要考虑跨域治理的外部性问题。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跨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具有外部性,可以转嫁给其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而其收益也具有外部性,可能让其他地区“搭便车”。中央政府则必须面对全国的跨域治理难题,对于地方政府不能或不愿供给的跨域公共服务,也无法转移和逃避。[30]因此,为了解决跨行政区域所衍生的公共事务与民众需求等问题,需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理博弈的均衡机制,协调和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和控制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的基础上,尽量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得到满足,以保证相互之间建立起紧密有效的协作伙伴关系。
从利益的角度看,没有一种大体保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就很难建立起来。目前,利益主体之间出现利益博弈失衡是客观存在的,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关系,实际上也是处理和调整跨域治理中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利益日益凸显出来,势必产生利益表达的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渠道表达,就会造成暗箱操作、地方向中央个别部门寻租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等一系列负面现象。毫无疑问,为了杜绝这些负面现象的发生,消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权限划分上的不明不暗的“灰色地带”,促进中央与地方动态府际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也为了实现中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加强中央与地方协作伙伴关系的纵向制衡和权力制约,需要建立顺畅的地方利益表达渠道,铲除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地方利益寻租化的土壤,在制度层面上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五、结 语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府际关系的核心,这种关系直接决定着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权力范围和活动方式,从而也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体系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层面看,单一制的政治制度是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而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则要求地方政府有适度的自主权,政治和经济的不同诉求,导致中央政府在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上面临着结构性的两难困境: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两者能否兼得?从实践层面看,中央的高度集权有利于维持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发展,但可能不利于地方政府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于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争夺“权力”和“利益”的动态博弈局面。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前没有或不打算在责任分置的原则上达成广泛共识,那么它们很可能长期纠缠于“权力”的集权和分权的循环中,并陷入“利益”竞夺的泥潭中相互角力。[31]
同时,在跨域治理理念的发展趋势下,民众参与公共议题的意识逐渐萌发,民间社会力量亦大幅增强,致使政府的主导力量愈显薄弱,传统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政策制定路径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尤其是涉及诸多社会大众利益的公共议题,政府更无法单向地制定政策,而必须与利害关系人协商沟通,整合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后,才能制定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政策。在中央权威体系中,对于比中央政府权力更为薄弱的地方政府来说,要应付处理利害关系人众多且彼此目标冲突的结构不良问题(ill-structured problem)时,必然会面临跨域治理的困窘和局限。若事事依靠中央政府的协助而不思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会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扭曲,并严重影响地方自治的立意与精神。所以,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不仅需要改变传统意义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也需要调整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关系,更凸显出地方政府与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建立互利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王鹏,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202141);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项目(37714001004);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B070300096)。
[2]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61-67.
[3]余敏江,刘超.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J].江苏社会科学,2011(2):147-152.
[4]Agranoff R,Mcguire M.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New Strategies for Local Governments[M].Washington D 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3.
[5]Stoker G.Transforming Local Governance:From Thatcherism to New Labour[M].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4.
[6]李柏谕.公私协力与小区治理的理论与实务[J].(中国台湾)公共行政学报,2005(6):59-106.
[7]马学广,王爱民,李仁岩.城镇密集地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研究[J].热带地理,2008(2):144-149.
[8]李长晏.迈向府际合作治理:理论与实践[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
[9]吴爱明.当代中国政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Isett K R,Megel I A,Leroux K,et al.Network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larship:Understanding Where We Are and Where We Need to Go.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11,21(suppl 1):i157-i173.
[11]孙彩红,余斌.对中国中央集权现实重要性的再认识[J].政治学研究,2010(4):33-42.
[12]王剑锋.中央集权型税收高增长路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7):45-52.
[13]赵志耘,郭庆旺.论中国财政分权程度[J].涉外税务,2005(11):9-13.
[14]Bardhan P.Decentralization of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4):185-205.
[15]郭庆旺,贾俊雪.财政分权、政府组织结构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J],经济研究,2010(11):59-72.
[16]Li H B,Zhou L A.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0):1743-1762.
[17]王文剑,覃成林.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J].管理世界,2008(1):9-21.
[18]高鹤.财政分权、经济结构与地方政府行为[J].世界经济,2006(10):59-68.
[19]西宝.基础设施网络整合与跨区域治理[J].公共管理学报,2007(4):17-30.
[20]Holmstrom B,Milgrom P.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Incentive Contracts,Asset Ownership,and Job Design[J].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91(7):24-52.
[21]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2]罗伟卿.财政分权理论新思想:分权体制与地方公共服务[J].财政研究,2010(3):11-15.
[23]马学广.从行政分权到跨域治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变革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1):49-55.
[24]参见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5]Bergemann D,Vlimki J.The Dynamic Pivot Mechanism[J].Econometrica,2010,78(2):771-789.
[26]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1):75-108.
[27]Mann M.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Ⅱ):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1760-1914[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28]高燕妮.试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J].改革与战略,2009(1):29-30.
[29]王孝松.中央政府的激励机制与地方经济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2009(2):11-15.
[30]余敏江.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府际间协调: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2):148-156.
[31]陈国权,李院林.政府职责的确定:一种责任关系的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3):69-7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