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百年的历程,2007年的医学和1917年的医学已大不一样。医学的百年演变,既包括在技术上的进步,也包括它所付出的人性化的代价。
在19世纪末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有四大巨人:病理学家及院长韦尔奇、外科教授霍尔斯特德、内科教授奥斯勒、妇产科教授凯利。
相对应地,也有人称协和内外妇儿这几个科也有着“四大天王”——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诸福棠。而刘士豪、邓家栋、许英魁、冯应琨、钟惠澜、陈志潜、王季午、吴英恺、曾宪九、黄萃庭、金显宅、关颂韬、胡传揆、李洪迥、罗宗贤、吴阶平……这些医学大家的相继涌现,照亮了20世纪中国的大半个医学天空。
但是21世纪已不是产生大家的时代,划时代的发现也越来越少。
如果清点一下目前中华医学会各个专业学会的任职人员,人们会发现那个“协和占大多数”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曾经几乎是由协和人从头创建的中华医学会,至今依然在中国医生心目中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前几年,有人曾经委婉地提议,是否应该在专业学会中,尽可能保存一些来自协和的力量。遭到的反对意见是:协和年代已经过去了。这种说法,让不少协和人一时感到难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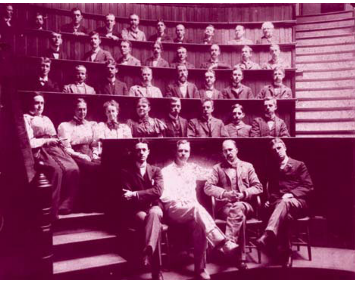
约翰斯·霍普金斯四巨人(前排)

协和1929届和1933届部分毕业生在1979年合影。钟惠澜(左一)、荣独山(左四)、林巧稚(左六)、陈志潜(左七)、施锡恩(左八)、林元英(左十,以上1929届)。邓家栋(左五)与黄家驷(左九,以上1933届)
当年协和初创时,是一个可以树立标杆的年代。那时的中国大地上散落着一些医学院,它们大多由教会办学,有的没有足够的资金,有的没有先进办学理念,有的没有顶级人才,有的没有优秀生源。而协和从耸立在北京东单的那一刻开始,这四个条件一一具备,并且能够靠着许多协和人的智慧和努力,坚持下去,拒绝降格为平庸。
在那个时代,医学的发展刚刚开始有了最初的欣喜,还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峰。所以,沐浴在世界一流学术氛围中的协和人,因为各种条件的幸运,加上自己的内在动力,得以站在了医学的前沿。也是在最黄金的年代,诞生了后来的大家,这其中就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协和四巨人”:张孝骞、林巧稚、诸福棠、刘士豪。他们把尚未成形的科室,变成了专科。那些专科第一个在协和建立,也几乎就是在中国第一个建立。他们毕业后去美国的进修和科研,更打开了这些第一代中国新医学人的国际视野,也让世界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他们在学术水平上,几乎与欧美没有任何差别。
那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注定是可以产生或是培育大家的时代。而在后来的演变中,先是重新调整的全国卫生系统安排。接着,几度的中断使得协和失去血脉的传承。而几场政治运动将许多人曾经视为神圣的东西,一夜之间彻底打碎,经年积累的“协和传统”,顷刻间被踩在脚下,彻底抛弃,变得不值一提。
大破之余能否大立,成为现实的问题。
再到后来,协和独具的四个优越条件:办学资金、办学理念、师资人才、学生生源,逐渐都失去了当年显著的优势。按照老教育长章央芬的说法:在80年代,医科院、协和医大合二为一的领导机制,使得协和医大的管理落后。而中国其他一些医学院校却珍视了这一时机,加强自己的师资队伍,增办新专业,扩建校舍,更新教学设备,教学科研大发展。相比之下,协和医大有“奄奄一息”之感。九十年前,协和的创建,曾经是创新的产物,来自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理念在中国扎根,堪称先进。九十年后,协和并未能顺应时代,敏锐地捕捉全球医界变化,用灵活的机制,继续引导中国医学教育的潮流,相反,它过多受传统所困,面露陈旧之相。而这期间,美国的医学教育在面对新问题时,已开始了如“新路径”(New Pathway)这样的尝试,已开始反思《Flexner报告之后一个世纪的美国医学教育》,已产生关注“教学过程”“教学结果”的新运动。
与此同时,在医院和医学院之外的那个世界,也在飞速变化。价值观的更替,与医生这个职业的最初定位,开始出现了错位。世界的膨胀和变化,还挑战着人们对传统的认识。而这时的医学技术平台,已几乎可以对所有希望接近的业内人士开放。各家医学院或是医院的人,都可以接触最先进的学术会议、最新的学术进展,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交谈、切磋、进修。确切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单独一家医院在技术上全面地独领风骚,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国,按照目前的医疗系统安排,有综合,有专科。当初由协和调出去的专家去领导、建设的专科医院,在技术上,注定会超过协和现在的那个专业科室。
但是除了技术因素,医学还有另外的意义。
这“另外的意义”,就是为医之道,就是医学中的人性化因素。
近百年之间,医学技术在进步,就像一个比喻说的那样,“今日的技术,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巨人”。它在成长和壮大,攫取了人们的注意力,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统一而有计划的大开发,这场开发产生了经济利润,展示的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全新、方兴未艾的领域。人们折服于技术的魔力,似乎再也不能控制那源自更深层本质的东西了。可是,技术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仍然不清晰。广泛开展的无休止的技术变革,使得人们在狂喜、迷乱之间,“在最难以置信和最原始的无助之间徘徊”。
对医学来说,在医学技术与医学面对的人性之间,一开始是拉开了距离,后来变成了鸿沟,进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医疗的形象负面,比如医生这个职业的从业自豪感和自主动力一日日在降低,比如专业化和技术化削弱了医生与病人的感情交流,比如大众对技术的狂热吹捧、对医疗技术高费用又加以无情的贬低,两者矛盾、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今天,医生这个职业,还被无奈地赋予了更多的关系和更庞杂的内容。比起一百年前,这个职业离科技更近,离人性更远;离专门更近,离整体更远。
如果深入到医生这个群体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百年流转中也在演变。从前老少间“传、帮、带”的关系,可以很浓厚,亲密无间,可以像一个大家庭,大家信奉同一种价值观,奔向同一个目标。而在今日,医生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关心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一方面是,自己跟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究竟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从前“老协和时代”那么多的责任和主动。另一方面是,如果老师想“传、帮、带”,这部分如何计算、评估、尊重他们的付出?而年轻一代又会怎么看待老师的付出、苦心、价值观?像“老协和”那样曾经以“无以复加”的严厉、精雕细刻、言传身教为特点的“导师制”,是否能生存在今日的社会土壤上,已经是一个问题。端详“导师制”的导师和学生这两个方面,都会发现今日它们之间的格局已不比从前,在今日的运转必将不如当年那样顺畅和自如。
所有这些,与医学的演变有关,也与社会的演变有关,更与中国这样一个百年间价值观几度翻转、剧变的事实有关。在巴金辞世时,曾有文章这么写:
“一个人走了,中国文学一个时代最后的象征也随之终结。上个世纪30年代就基本建立起来的‘巴、老、茅、曹’并称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豪时代曲终人散,也给当今文坛、读者留下了一片无文豪、巨匠相伴的空寂和青涩……天空已无巨星的光耀、灵翅的扇动。在无尽的追思和缅怀中,中国文坛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文豪后时代’。”
这段感慨,读来发人深思。因为它说的,不仅是某一个领域里的故事。最起码在医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地。
协和曾经的名声和耀眼光芒,确实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一连串可以让同行、老百姓记住的名字,人们把他们叫作“医圣”“医学家”或者“名医”。他们除了精湛技艺——技术上的杰出之外,还有一点也不该忽略——为医做人的精神。他们为病人而生,在病人床边工作,向病人学习,以诊治病人为幸福。他们愿意“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那时的医生,成天泡在病房里,像铁屑被磁石吸引着。当病人终于康复,得到的是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
而现在,他们曾经站过的这块高地上,却已归于寂寥。大师终会陨落,在一个信仰飘零的时代,医学界同样处于自己难以解脱的尴尬境地:医生们难以参与医疗政策,病人和医生之间变形扭曲的不信任关系,医生的收入没有透明的高薪保证,医生职业的冷漠和辛酸……信仰缺失,幸福感低下。在新的时代、新的体系下,需要创造出新的系统来评价医生这个职业。只是,目前一切还处在未定型,一切还需要年轻人持久努力。
吴宁教授1956年自协和毕业,此后她的全部生活一直与协和有关。她的父母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深信生在乱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曾经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委的吴宁,到了晚年说自己其实资质平平,但她这席话却是发人深省:“医学其实是一门不需要太聪明的人来干的工作,只需像我这样资质平平,但绝对是踏踏实实、勤奋肯干肯吃苦的人,它要求必须踏实地练好基本功,一步一个脚印。说到底,医学最终是为病人服务的,是为了切实给病人解决病痛的。”
“像我们当时,起码知道自己在做医生这一行,是在干什么。我是医生,是在给病人看病。现在动不动就必须得搞科研,搞高、精、尖的课题,必须和基因什么的沾上点边。搞着搞着,可能偏离了医学最初、最朴素的目的,一些医生可能会看不起听诊器,忽略了最基本的——为病人治病。我们那时上医学院,将来要做什么?是要做临床家,而临床家,才是病人真正需要的。我们那时碰到的协和上级大夫,就在用自己的言行时刻无声地教育着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好医生。像张孝骞这样的名医,到了八十岁时,仍然自谦,说自己没有资格写书,永远在学习,对病人的病情永远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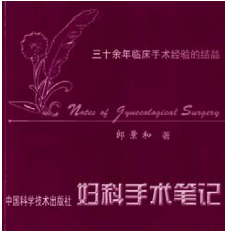
郎景和的《妇科手术笔记》表达了医学人文的思考
对于“良医”的定义,还不仅技术和品德这么简单。也许吴英恺在多年前强调“良医”有多重要时,未能预见到在今天的医疗世界中,医生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和压力。杨秀玉有一次看特需门诊,一个外地患者由于婚后多年不孕,四处求医,在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花了二十多万元。那些医院态度倒是很好,左查右查。杨秀玉看完病人说,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建议先看看内分泌。病人听后破口大骂,挂了一个三百元的专家号,非得现场解决问题,非得看出点毛病来。当时杨秀玉很委屈,但后来想,既然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也只有像她的前辈一样勇于担当,唯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1985年的一天,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那天傍晚,杨秀玉已经上了班车准备回家,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位重病人,在当地已确诊是绒癌。杨秀玉跑到急诊部。当时,病人因脑转移、脑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获得治疗时机。病人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病人母亲又问。一般情况下,医生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和风险,毕竟在此之前没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望。”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教授一起留在医院,等着手术结果。病人后来不仅痊愈,还生了个女孩。作为第一例脑转移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这位病人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良医”。只要有人问到这位病人,什么叫好医生?她会说,一个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愿意承担一定风险。
2006年有一期CCTV《大家》节目里,嘉宾是协和妇产科主任郎景和。这期的题目是《一个医生的哲学》,郎景和1964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已在这里度过了四十多年的光阴。除了是一位妇产科名家之外,他还曾经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写有《妇科手术笔记》。
在节目里,他自言“看去温文尔雅,却是开刀匠人,每天看病、查房,做手术最开心,不知疲倦”。他对医学精神的领悟、他的医学哲学观、他的人文关怀理念,是今日中国医学领域少见的人文风景。在他的《妇科手术笔记》中有一节,说的是“外科医生的哲学理念和人文修养”,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和,是分析问题的智慧和方法。
二、人文修养是医生的基本修养,因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
三、做一个德技双馨、文武兼备的外科医生。
“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文学可以弥补医生人生经历之不足,增加对人与社会的体察;艺术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心境的和谐、美的熏陶;伦理与法律给我们划出各种关系、语言与行为的界定。我们还应该学习一点历史,特别是医学史,我们会从《革命医生》中,体会到山姆维斯(Semmeiweiss)的敏锐和勇气。”
在他看来,当医生有了丰厚的哲学与人文底蕴的时候,便会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时,再追寻与反思医学或外科的目的,则不难理解,治疗(包括手术),显然并不总是意味着治疗某种疾病,而是帮助患者恢复个人的精神心理与生理身体的完整性;医患关系,也不意味着我们只注重疾病过程,更应该考虑病人的体验和意愿”,这样才能将自己“塑造”成为真正的外科医生。这段话让人想起1939年,奥斯勒的一名学生,写了一本叫作《作为一个人的病人》(The patient as a person)的书,警示医学界中“科学的满足”正在取代“人类的满足”,应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治疗,哈佛则在1941年开设了“把病人当人”的课程。
在张孝骞去世时,协和医院曾写了一对很长的挽联,试图概括他的一生,不知是否也在缅怀一个“医圣”时代的终结:
“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茧,待患似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公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
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视学如子,谆谆无厌倦。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宏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
老协和曾经培养的医学大家的相继离去,留下一道道伤口,甚至是发炎的伤口。每一次离去,都是不可再复制的记忆。像张孝骞这样的内科通才,在今日的技术条件限制下,几乎不可能出现。
大师时代已去,良医尚可期待。一个能将医术和对“整全的人”的关注融合在一起的“良医”,可能是今日协和还可能存在的示范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