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发生的可怕一幕,我们都终生难忘,我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仍然激动不已。我还把文章读给我的两位同伴听,他们认为,记录的事实确切,但不够生动。要描绘这样的场景,得由最著名的大作家雨果那样的人出手才行。
内莫船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又是一连几天都没有露面。“鹦鹉螺”号还没有明确的航向,几天以来,一直在随波逐流。尽管螺旋桨已经被松开,但是还是不能转动,这艘船在和大章鱼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之后好像有些疲惫不堪,又好像有了感情一般,不想离开这片吞噬了自己同胞的海域……
10天过去了,“鹦鹉螺”号开始向北方前进,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巴哈马水道的吕卡纳群岛上部,正在沿着海洋中的一股水流行驶,水流有自己的边缘、生存的鱼类品种和自己恒定的温度,这就是大西洋暖流。
5月8日,“鹦鹉螺”号来到横越北卡罗来纳附近的哈特拉斯角,墨西哥暖流流经这里,宽度达到了75海里,深度有200米。“鹦鹉螺”号漫无目的地漂荡着。
在这附近有人类居住的海岸,海上船只来往频繁。它们定期从纽约或者波士顿前往墨西哥湾,还有很多途经此地的帆船,另外岸边还停靠着许多的船只,要是我们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候逃走,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我们有很大的几率被经过的船只搭救,最关键的是,现在“鹦鹉螺”号距离北美海岸只有30海里的距离,而且船员们对我们的监视也很宽松。
但是,现在在这个海域中,暴风雨正在肆无忌惮地横行,飓风和龙卷风时不时光临这里,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我们的计划。事实上,这也不是偶然形成的,是大西洋暖流作用的结果。尼德·兰德的心中非常清楚,要是现在偷偷驾着小艇离开,无异于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尽管尼德·兰德很想逃走,尽管海岸就在眼前,但他也只能咬紧牙关,强忍住逃跑的想法,忍受着思乡之情和逃跑的欲望折磨。
“先生,现在,这场戏真的应该收场了!有一句话,我不得不提醒您:现在内莫船长正要离开陆地向着北方行驶,南极已经让我受够了,我不想再和内莫船长到北极去了!”尼德·兰德找到我说。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办,你应该知道现在的天气不允许我们逃走!”
“我还是坚持以前的想法,我们应该找内莫船长好好谈谈,最好让他放人。船就快到达我的祖国的沿海了,再过几天就能到达和新苏格兰同纬度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海湾——圣劳伦斯河,圣劳伦斯河是养育我的河水,我们就要到我的故乡魁北克市了。每次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十分难受,我很气愤,甚至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先生,我要回家!我宁愿跳进大海,也不想再留在这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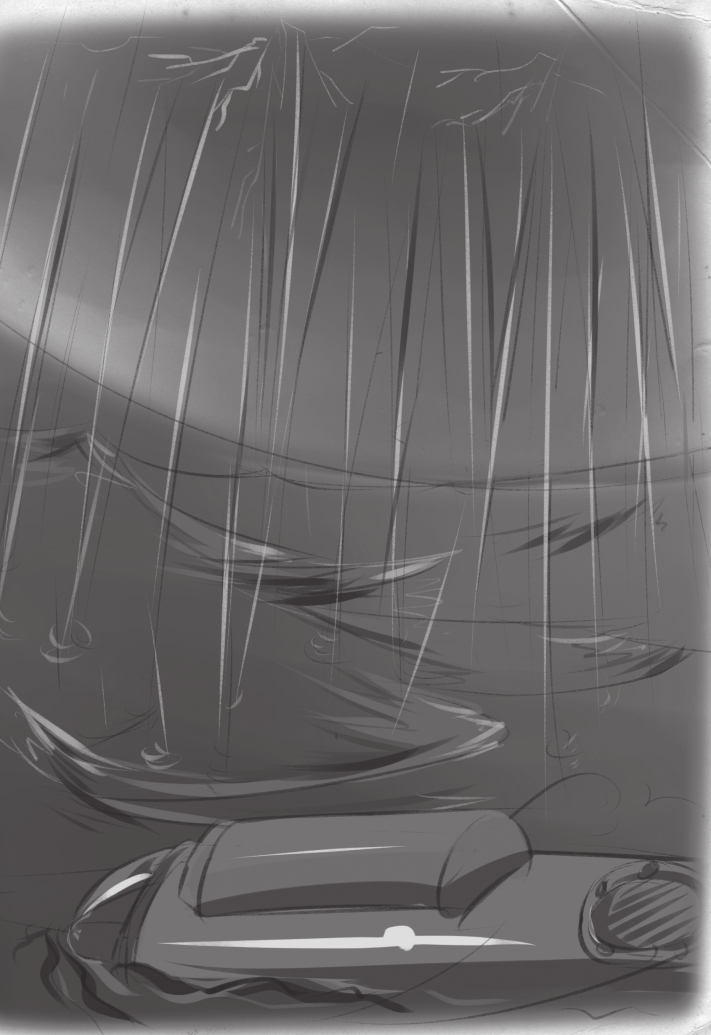
尼德·兰德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他再也无法适应这种无限延长的囚禁生活了。他的身型一天天消瘦,心情好像也越来越忧郁了。我能体会尼德·兰德这种思乡的痛苦,因为曾经的我也被这种感情折磨过。毕竟,我们已经有将近7个月的时间没有得到过陆地上的任何消息了。
我们的讨论结果是由我去找内莫船长。
我来到内莫船长的舱房,他正在伏案工作,根本没有察觉到我的到来。当内莫船长发现了我之后,他的语气变得十分生硬。
“您怎么来了,教授?”
“内莫船长,我想和您谈谈。”
以这样的开头开始的一场谈话,会令任何人都感觉没有希望,但是我还是大胆地将我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我想说,假如您能恢复我们的自由的话……”
“自由!”内莫船长重复道。
“是的,内莫船长,这就是我想要和您商量的问题。我们已经在您的船上打扰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了,我和我的伙伴都想再次问问您:您是不是要永远把我们囚禁在‘鹦鹉螺’号上?”
“阿龙纳斯先生,”内莫船长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今天的回答和7个月前您来这里时的回答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谁,只要来到了‘鹦鹉螺’号上就永远不可能离开!”
“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醒您,我们并不是您的奴隶!”这时候的我,相当的气愤。
“不管您怎么说,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内莫船长恢复了一贯的冷静。
“即便是奴隶,也有恢复自由的那一天啊!只要有机会,奴隶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恢复自由,都愿意恢复自由的!”
内莫船长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在我们谈话的末尾,他义正词严地告诉我,他希望类似的谈话是最后一次,要是下次再有类似的谈话,他听都不会听的。我只好退出了内莫船长的房间。
这次谈话之后,我和内莫船长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回来的时候,我将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的两位同伴,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教授,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尼德·兰德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对这个内莫船长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希望和幻想。现在‘鹦鹉螺’号正向着长岛的方向前进,不管是什么鬼天气,我们还是抓住这个机会逃走吧!”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天气越来越糟糕,好像有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了。天空是压抑的铅灰色,低垂的乌云在风的作用下疾速前进。海浪汹涌,一浪比一浪更高,除了喜欢暴风雨的海燕,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其他鸟类了。
气压表的示数在连续不断地下降,大风暴终于降临了。现在“鹦鹉螺”号和长岛处在同一纬度上,距离纽约河的河道只有短短的几海里。
大风一阵阵疯狂地刮着,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15米,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风速更是达到了每秒25米。这样的风速是典型的飓风。
内莫船长站在平台之上,用绳索捆绑住自己的腰部,在狂风中屹立着。阵阵狂风向着“鹦鹉螺”号席卷而来,船身不停地左摇右晃。下午5点,风速已经达到了每秒45米,这样的风力足够将一座房屋摧毁,或者轻而易举地折断铁栅栏。晚上10点钟,天空中电闪雷鸣,隆隆作响的雷声不绝于耳。
快到第二天早上5点的时候,天空中下起了大暴雨,雨点就像千万个齐刷刷的箭头,向着海面斜斜地射去。看着眼前站在暴风雨中的内莫船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内莫船长现在是不是正在寻找一种和自己的身份相匹配的死亡方法?现在“鹦鹉螺”号摇晃得非常厉害,甚至在船舱内的人都无法站稳。

一直站在暴风雨中的内莫船长,到了后半夜才回到船舱内。“鹦鹉螺”号的储水仓开始蓄水,船身慢慢下降到了水面之下。透过舷窗的玻璃,我能看见很多受到惊吓的大鱼,它们就好像幽灵一般,在探照灯能照亮的范围内出现。船沉到了50米深处,才恢复了平常的宁静。
这次大风暴之后,我们被抛向了东方。在纽约河或者圣劳伦斯河附近逃跑的计划成为了泡影。尼德·兰德简直绝望至极,他像内莫船长那样,整天待在自己的舱房里,而我则和孔塞伊形影不离。
5月28日,现在我们距离爱尔兰岛只有150海里的距离,内莫船长会不会要带我们到不列颠群岛去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内莫船长下令“鹦鹉螺”号南下,回到欧洲海域。
我暗自思忖着:“鹦鹉螺”号敢于深入英吉利海峡吗?自从我们接近陆地之后,尼德·兰德就从自己的房间走了出来,不断地问我,我们的逃跑计划是不是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我们依然看不见内莫船长的身影,上次,内莫船长让尼德·兰德看见了美洲海岸,难道现在他会让尼德·兰德看见法国海岸吗?
5月30日,我们站在“鹦鹉螺”号上已经能够看见终极岛,这个岛从英格兰最南端和索尔林群岛之间的一片小区域穿过。到了5月31日,船开始在海面上兜兜转转,给我的感觉是,现在“鹦鹉螺”号正在寻找一个很难发现的目标一样。中午时分,内莫船长亲自来到客舱记录“鹦鹉螺”号所在的位置。内莫船长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我可以从内莫船长的脸上看出忧伤的表情。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要接近欧洲,引起了内莫船长对自己放弃的故国的深深怀念吗?
6月1日,海上没有一丝波纹,天空也湛蓝无比。在“鹦鹉螺”号东面大约8海里的位置,出现了一艘大船,船上没有悬挂标志性的旗帜,所以我不能确定这艘船的国籍。
内莫船长正在全神贯注地研究着手中的六分仪,以此来确定我们的方位。此时,海水平静异常,对于测量的进行十分有利。当时我也在平台上,听见内莫船长说:
“就是这个地方!”
内莫船长回到船舱,我也来到客舱里。储水仓开始源源不断地蓄水,螺旋桨已经停止了工作,所以船是垂直下沉的,我们很快下沉到海底,深度为830米。
客舱的灯光熄灭了。我透过舷窗向外张望,半海里之内都是一片光亮。我发现,在我们的右侧半海里之内的距离,有一堆高高隆起的东西,在这个东西的表面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贝壳。再定睛观察,我认出那是一艘船的残骸。当年,沉船的时候,一定是船头首先开始下沉的。这些残骸的表面的贝壳是如此的厚,想必它已经遇难很多年了。
这是一艘什么船呢?“鹦鹉螺”号为什么特意来拜访这里呢?难道这艘船不是因为海难沉没的?
正当我自言自语的时候,内莫船长走了过来,他说:“这艘船的名字叫‘马赛人’号,船上一共有74门大炮,1762年下水,曾经参与了很多战斗,立下无数战功,称得上功勋卓越。1794年,法兰西共和国更改了这艘船的名字。今天是1868年6月1日,推算起来,在74年前的今天,就在相同的地点,也就是北纬47°24′,西经17°28′,这艘船与英国的舰队发生交火,在一番英勇的战斗后,船的3根桅杆被炸断,船舱开始进水,船上三分之一的人都失去了战斗力,剩下的人们宁死不屈,不肯向疯狂的敌人投降,他们将自己的旗帜钉在船尾,高喊着‘法兰西万岁!’的口号,全部被翻滚的波涛吞没了。”
“是‘复仇’号!”我大喊起来。
“没错,阿龙纳斯先生,就是‘复仇’号!这是多么伟大的名字!”内莫船长双手叉着腰喃喃自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