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丛报》创刊号
梁启超到日本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为《清议报》。1901年11月报馆失火,《清议报》随之宣布停刊,转年2月,《新民丛报》继而发行。据梁启超解释,“新民”一词来源于儒家经典《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103]引用这个概念的目的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能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104]在梁启超看来,“新民”的目的是为了“新国”,而“新国”的前提必先“新民”,《新民丛报》的创刊宗旨不言而喻,为了《新民说》而创办,可以说《新民丛报》承载了梁启超全部的新民构想和以新民救国的政治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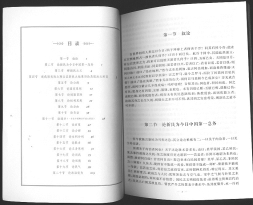
《新民说》
从1902年到1907年《新民丛报》从第1期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梁启超的一系列关于新民思想的论文,一直到第96期,中间以1903年梁启超赴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共计20篇,[105]约12万字,后来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106]《新民说》一直被学界认为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系统体现,也是他本人道德观和政治思想的阶段性反映,欲了解1898—1906年间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的转变,《新民说》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正如狭间直树所说:“把逃亡日本后的梁启超单纯地称为‘政治家’是有失妥当的。但同时也要承认,梁本人绝对没有把自己只看作学者、思想家。他的‘启蒙’文章首先是为其政治实践服务的。他的所有挥洒着报人天分、充满了情感、意在开启民智的灿烂篇章,都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写就的。”[107]关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来源,学术界大略有四种观点:(一)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直观理性主义倾向是孕育新民理论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文化传统”。[108](二)来源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观念深受严复启蒙主义思想影响,而严复的理论均源自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三)来源于卢梭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学说,这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接受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伯伦知理等西方近代著名思想家的学说观点,由此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近代的国家观概念中的“国民”思想。(四)来源于近代民族主义,认为近代民族主义不仅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最终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方案的选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并不把上述这些理论来源作为独立因素,而是将其中的两点或多点融合起来,更加客观和全面。张灏先生就认为:“新民”这个概念在流亡日本前就存在于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到日本后在明治维新的新的思想环境中,当西方的价值观渗透到他已有的儒学观念中时,这种对“新民”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但梁对‘新民’的阐释与《大学》中的‘新民’概念相比,革新更为突出。”[109]张灏先生肯定了新民思想在梁启超思想中的连贯性,不仅在流亡日本时期接触到西方启蒙学说之后,流亡前就已经以儒家的经世观念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过。笔者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在对梁启超的《新民说》进行系统分析后,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于新民思想的来源,笔者提出如下观点:
第一,新民的理念在时间上产生于在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前。在中国最早提出新民思想理念的不是梁启超,而是严复。在严复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所有反侵略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民力已秦”“民智已卑”“民德已薄”,[110]戊戌维新期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观,不仅自然界遵循“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律,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观点曾被当时所有进步人士视为圭臬,梁启超自然也不例外,他在诸多文章中都在颂扬这种进化论观点。那么,如何使中国自强不息?严复说关键在于国民,强国必先强民,“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相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111]集权、练兵是标,“新民”是本,因此在推动进化论的同时,他提出了“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的新民主张。严复是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最早开始接受的导师,严复的新民理念必然给梁启超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他在1896年9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盖当日[112]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113]和严复的观点一致,在《新民说·叙论》中梁启超同样也把“新民”看作国家自强的前提和基础,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固,而身犹能存也;则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14]梁启超在日后提出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和严复思想如出一辙。不过,严复虽然是近代中国新民思想的最早提出者,但明确而系统提出新民之道的人却是梁启超,他继承和发展了严复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讲,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来源,最初来源于严复(或者说是不完全的斯宾塞,因为严复在接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同时也根据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发展了这一理论)是符合事实的。如此,那么学界的第四种观点便不能成立,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起于流亡日本之前的戊戌维新时期,尽管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接触到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给了新民思想新的理论支持,但不能称之为其新民思想的来源。
第二,延续上述思路,在梁启超早期的新民思想中就不可避免地存留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德”的阐释上。在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中,民德是第一位的,要高于民智和民力。梁启超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谙儒学,《论语》中的“温良恭俭让”“克己复礼”“忠信笃敬”“寡尤寡悔”,《皋陶谟》的九德[115]、《洪范》的三德[116]等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德”的概念深植于其思想中。梁启超将“德”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德,梁启超对公德的解释是:“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117]概言之,公德就是促成群体凝聚力的价值观念,强调的是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应尽的各种道德义务。公德有多重要?“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118]第二类是私德,私德与公德相对而言,梁启超说,群体由社会成员的个体构成,公德的实现自然也依赖于社会成员自身道德水平的提升,因而私德指提升个人道德使之完善的价值观念。根据对“公德”和“私德”的阐释,他发现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偏重于私德,公德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几乎没有任何发展,而私德不足以造就国民的完全人格,也不足以巩固群体和国家,因此在最初的“新民德”中他侧重于强调对国民公德的培养。
对中西伦理学的比较使梁启超再次加深了对“公德”重要性的理解。在梁启超来到日本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读到了日本文部省颁发的中学伦理道德课程训令,这个训令使梁启超为之震惊。他震惊于日本仅仅是对中学生提倡的伦理道德课程,居然比中国全部的伦理行为规范还要宽广,它不仅包括了中国传统的“五伦”,甚至还包括中国伦理学家无法想象的对社会和人生这些抽象概念的伦理,相比之下,自诩礼仪之邦的中国,道德体系就过于狭窄了,于是他开始着手为中国设计一套新的、适用于当时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设计思路的来源便是对中国和西方道德价值观念的比较。梁启超看到,中国旧伦理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偏重于“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119]西方的新伦理包括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偏重于“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120]二者相比较,中国的“五伦”可作如下划分:父子、兄弟、夫妇归于家族伦理,朋友归于社会伦理,君臣归于国家伦理,但“五伦”仅仅是西方伦理学中的某些组成部分,二者范畴相差甚远。经过比较梁启超发现,中国“五伦”之中最为完善的是家族伦理,最缺陷的是国家伦理。中西之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他说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道德中偏重私德造成的,因而他的任务便是指出事实,造就中国新国民的“公德”品格。
如是,讨论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新民思想产生的影响,最明显体现就是他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反思和批判。梁启超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是十分了解的,他在对中国积弱的国民因素进行思考时,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中的某些缺陷。有了解才有发现,有发现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创新,1902年3月,《新民说》的重要篇目《论公德》发表,正如梁启超所说,造就中国人近代国民资格,培养国民“公德”首当其冲。
第三,当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不能满足“新民”的需要时,梁启超便着手对其进行革新,革新的体现存在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他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或者说国家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群”到“民族”的演变过程。正如前文刚刚讨论过,1902年梁启超强调“公德”的培养,“公德”的基础是“群”。1897年他在《说群》中首次提出了“群”的概念,这时的“群”仅停留在团结中国人形成一集体的层面上,1898年他呼吁海外商人将自身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商会时,再次提出了“群”的概念,这时的“群”具有组织公民社团的含义。直到1902发表《新民说》的时候,梁启超对“群”的概念已经趋近成熟接近民族国家思想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1902年3月份(《新民丛报》第3号)发表了《新民说》的第6节《论国家思想》以及6、7月份的第11节《论进步》。[121]《论国家思想》中说:“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家者也”,国家是“最上之团体”,[122]这里他将“群”的概念宏义化,明确指向了民族国家。国民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而有国家思想才能称作国民,那么什么是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简言之也就是国家与个人、朝廷、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与朝廷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思想中,朝廷就是国家,“朝民”即是“国民”,国民参与国政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梁启超提出的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国民参政,这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不同的。在梁启超看来,朝廷和国家的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他用了一个有趣而形象的比喻:“国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123]在《论国家思想》之后的第11节《论进步》中梁启超继而讨论了中国群治不进原因,他分析说“中国专制久而民性漓”,表现为“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天下为私,国家是一家一姓之私有财产,梁启超根据西方近代国家思想之精义,大呼“破坏、革命”,以求天下为公。因而可以判断《新民说》发表时梁启超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民族国家思想。
第四,如何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国家?需要自由和权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观点刚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在第6节《论国家思想》中讨论了近代国家思想后,梁启超为《新民说》设计的第8节和第9节分别是《论权利思想》和《论自由》(1902年5月8日—6月6日,《新民丛报》第7—9号)。梁启超把人类的权利和自由从古至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人人栖于一小群之中,人人皆自由,这是野蛮自由时代;二是群与群相竞争,有智勇者为领袖指挥其群,久之成贵族封建制度,这是贵族帝政时代;三是有郡县一统者削平一切贵族封建,这是君权极盛时代;四是人民日渐开明革命夺回政权,这是文明自由时代。由此可见自由权利和竞争密不可分,中国要自强,中国人就要有自由权利的思想,中国人恢复天赋的自由权利,也是为了使中国自强。梁启超感慨说“权利之生涯,竞争而已”。[124]其实早在1899年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梁启超就已经讨论过竞争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竞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组成部分,人类的发展是一部竞争史,从人群开始,中间历经小部落、大部落、种族、大种族、国家、大国家、帝国直至大帝国,这种发展的进程就是竞争的结果。由此推导,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是一部竞争史,今日就是大帝国与大帝国竞争的时代,中国的衰落就是缺乏竞争的结果。这时的梁启超就已经开始运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当时中国的现状进行分析了,但他将进化论思想和西方启蒙思想的国家观进行结合、对国民竞争和国家竞争关系进行深入理解,是在来到日本之后。1902年2月—4月,《新民丛报》在《新民说》之外单独发表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丛报2—5号),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明确断言,竞争是文明之母。梁启超在国家思想的范畴中,按照社会进化论史观,他把国家的演变过程归结为“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125]的过程,最终国家作为最高的团体,也成为“竞争之最高潮”的主体。由此他认为,在国家的形成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类所渴望的,这是西方国家进步的奥秘,也是中国停滞不前的根源。
有一个事实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他的很多政治思想包括新民思想都受到了他所读到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影响。1901年底他完成了《卢梭学案》,他高度认同卢梭的社会契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由权利思想,按照卢梭的理论,人生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即使社会成员按照契约结成国家关系,个人的自由也至高无上,当个人自由被限制时,社会成员有权利通过革命的方式重新夺回自由。众所周之,卢梭的这个理论曾经一度极大地影响了梁启超,成为他在1900—1903年间倡导革命和民主共和的理论支柱。如此,便出现了这样一个矛盾:完成于1902年5、6月份间的《论自由》强调的是民族国家自由的优先性,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梁启超在讨论自由主义时侧重点在国家而不在个人。如何解释这个矛盾?一方面梁启超任何时期的政治理想和行为都是以一个最终目的为出发点——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富强。他将个人视为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只有个人能够自保、自行自由权利,国家的自由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此即使他赞同卢梭的个人自由权利思想,最终也是为了强调民族国家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笔者始终赞同对梁启超在1903年以后政治思想的改变原因持渐进观点,猜测在1903年他访美之前,确切地说在《新民说》发表的同时,他就已经开始怀疑卢梭思想对中国的实用性,转而开始趋向伯伦知理的学说。原因有二:一是与《新民说》发表同时,在《新民丛报》的第1号上,梁启超曾发表另外一篇文章《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他把卢梭立为十九世纪之母,伯伦知理立为二十世纪之母,他说自伯伦知理界定了国家的性质、精神和作用后,国家主义才大兴于世,爱国是国民的第一义务,这是各国进步的原动力,也是十九世界末世界之政治原则。不久,在第3号上继而发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再次明确指出,卢梭的民约论只适合社会而不适合国家。此时梁启超已经开始了对卢梭的批判。二是同样创办于1902年的《新小说》上,梁启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新中国未来记》,其中两个主人公黄毅伯和李去病的对话,也表现了他对基于卢梭的人民绝对自由权利思想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国和基于伯伦知理的人民有限自由思想基础上的君主立宪两种政治方式的犹豫和矛盾,同样能够说明他在访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思想上的改变倾向,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详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