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葬期特点
按照古礼“三月而葬”,时间太长,尸体不易保存,生者也不胜其劳,因而古时候就有所谓“渴葬”“血葬”之说。即七天之内不卜而葬,这种葬法在宋代也不乏其例,但同时也存在很多自死至葬长达数年之久的事例。宋人文集和近代出土的墓志铭、墓表、神道碑、圹记等就反映了这种差异(见表一)。
表一 宋人文集墓志记载部分葬期[1]

从表一中所选的563例葬期可以看出,葬期在10天以内的只有2例,占到总数的0.3%,10日至2月的有8.8%,3年以上的有9.9%,其中葬期在2月至3年之间的合计占到80.5%,说明宋人葬期在2月和3年之间的占主流。但同时还应该看到葬期在3年以上的占到了总数的9.9%,近十分之一的比例。宋代还有葬期长达数年之久的,如苗正伦死于皇祐二年,而到熙宁八年才下葬,前后间隔达25年。[2]冯安园死于元祐二年闰八月二四日,葬于大观元年九月二四日,时间间隔了20年。[3]折惟忠妾李氏更是长达39年,从熙宁五年五月一日到政和元年十月二十日。[4]
宋代文风颇盛,为人写墓志铭、行状成为宋代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传世的宋人文集大部分都有这类吊亡纪念性质的作品。能够邀请文人给自己亲人写墓志铭的,自然不会是庶民,多属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5]在墓志铭的使用上,也有个变化过程。墓志铭起源于《颜延之王球石志》[6],据近人考证,宋初墓志铭的应用还不是很普及,用墓志铭的多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南宋时才逐渐流行于平民阶层,并且不同地域发展还不平衡。[7]这种不平衡性造成了在葬期统计数据的选择上会受到地域和时间局限的问题。因此,用表一来说明宋代葬期的特点是不全面的,只能说明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葬期特点。从表一可以看出,宋人葬期普遍较长,超过三年甚至超过十年的现象也很多,如果再综合其他的一些文献材料,可以肯定这一现象在宋代是较为普遍的。
《夷坚志》记载了一个故事:
平江士人徐赓,习业僧寺。见室中殡宫有妇人画像垂其上,悦之。才反室,即梦妇人来与合。自是夜以为常,未几,遂死。家人有尝闻其事者,至寺中踪迹得之,其像以竹为轴,剖之,精满其中。[8]
这则故事情节完整,落魄书生、女鬼两情相悦,已经具备后世鬼狐故事的雏形,只不过结局较为凄凉,这也是宋代鬼狐故事的一个特点。故事中的女主角是寺中在殡待葬的妇人,在《夷坚志》中还有很多这类待葬之尸鬼作怪的故事,如《莫小孺人》《殡宫饼》等。其中有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故事中作怪的都是待葬的女人。书中还记载了另外一类不葬父母而遭报应的故事,在叙述者的眼里,陈杲、杨公全都是由于不葬父母,有违礼节孝道,而遭到了报应,是典型的因果报应故事。其中不葬父母是因,科举落第为果。将尸体停放在寺庙中或者是很长时间不葬父母,导致的结果必然就是葬期会很长。
《宋史·石介传》记载,石介“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熙宁时,外戚向传范,“宰相子,联戚里,所至有能称。以橐中赀千余万葬族人在殡者六十四丧”[9]。石介丁父母忧,所葬五世未葬的就有七十人,究竟这七十人是士人还是庶民,传中并没有详细说明,不过从这么大的范围来看,应该是士庶兼有。五世未葬,时间跨度较长,葬期至少在五十年以上。向传范所葬的六十四个族人,葬期应该是有长有短。久丧不葬,葬期较长,在宋代的文献中可以找到普遍的例证。
相对于宋代的士庶阶层,史书对于皇帝的葬期记载相对详细和集中一些,表二即为对宋代皇帝葬期的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两宋皇帝的葬期以7个月居多,其中太祖和高宗的较长,前者长达16个月,后者则为17个月。
表二 两宋皇帝葬期[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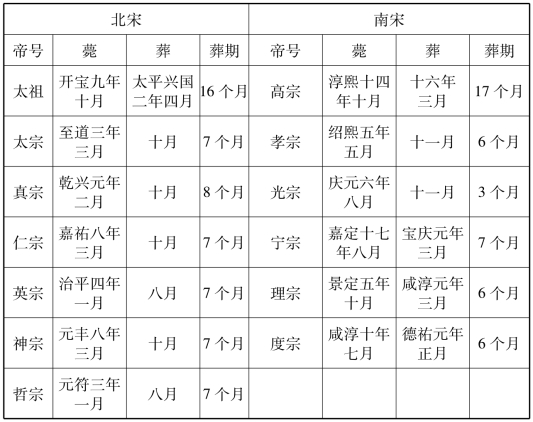
二、影响葬期的因素
从宋代葬期的实际情况来看,影响葬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归葬观念和风水择日习俗。
从古到今,中国人的故乡情结就非常重,如果不是遇到战乱和灾荒,很少有人愿意背井离乡,到异域他方;即使到了异域他方,最后也希望终老能够回到故乡,所谓“叶落归根,狐死首丘”。这种情结也反映在丧葬习俗上。宋代归葬故乡的事例也大量存在,在北宋时,尚有一些人葬在外地,欧阳修葬父于家乡泷冈阡,后又奉母郑夫人归葬家乡,作《吉州学记》盛赞家乡风气之美,最后自己却终老颍昌。这件事到南宋受到了批评,尹直卿有首诗写道:“六一先生薄吉州,归田去作颍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杀青原白鹭洲。”[11]总的来说南宋时不归葬故乡的事例很少。[12]子女在父母逝去后多遵亲命或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将其归葬故乡,归葬故乡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要影响葬期的长短。
风水择日之术也是影响宋代葬期的一个不可忽略因素。儒家在丧葬上强调“入土为安”,并重视对死者尸体的保护,把“慎护先人发肤”作为后人“扬名后世”的行孝方式。选择草木丰茂、土地干燥处来安葬自己的亲人,也符合儒家“孝”的伦理。由于佛教的影响,宋代焚尸而葬的现象比较普遍,“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13]。违背了伦理的火葬必然遭到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古人之法,必犯大恶则焚其尸。今风俗之弊,遂以为礼,虽孝子慈孙,亦不以为异”[14]。“父母死,则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无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与非之乎上,民相非之乎下,盖其习之久也,则至于戕贼父母而无以为不可,顾曰禁之不可也。呜呼,吾是以见先王之道难行也。”[15]如果说儒家的丧葬礼仪是为了逝去的人,那么风水则是为了活人。“地气”魔力巨大,“顺势形动,回复始终,法葬其中,永吉无凶”[16]。一语道破天机。显然风水择日之术里面既有“孝亲”的成分,也有利己的成分。运用风水和择日就要选择风水墓葬佳处,选择适宜下葬的时日,其对葬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外,如丧葬本身需要的花费、战乱等也会对葬期造成影响。
(一)归葬故乡
北宋时苏洵父子的安葬过程很能说明当时人们对归葬故乡的态度。苏轼为人旷达,“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17]。又在狱中写下了《狱中示子由》词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很明显可以看出苏轼对自己身后归葬故乡不甚积极。苏洵的态度显然与此不同,早在嘉祐二年四月,苏辙母亲在四川家中病逝,苏洵父子自京返蜀料理后事。此次回川,苏洵选好了自己百年后的穴藏,指着其“庚壬”的位置嘱咐苏轼兄弟将来归葬于彼。所以苏辙《再祭亡兄端明文》中说:“先垄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旁,自昔有言。”[18]但是兄长的遗命却是葬于嵩山之下,归葬祖茔已与愿违,左右为难的苏辙感叹说:“势不克从,夫岂不怀?地虽郏鄏,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19]最后遵从兄命葬之于嵩山下。
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十五日,苏轼一行尚在北返途中,苏辙的侄子苏千之西归家乡,苏辙写下《北归祭东茔文》托千之祭扫父母的墓茔,其中说:“兄轼来自海南,道远未至,皆以困踬之余,思归未获。如人病躄,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20]苏辙思归故土心情强烈,就像患足疾的病者盼望能健康行走一样。
然而卜葬嵩山并非苏辙的初衷。崇宁五年九月,苏轼去世后五年,苏辙作《颍滨遗老传》,进一步表达了归葬的心声,其言如下:“家本眉山,贫不能归,遂筑室于许。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昔尝约祔于其廋,虽远不忍负也,以是累诸子矣。”在这篇自传中,苏辙明言欲不违父命,希望子孙们待他死后能不辞劳苦,将他运回苏洵藏身的祖茔安葬。因而苏过在《祭叔父黄门文》中悲情地说:“倾一奠而永已,不得执绋,挽公之归葬于西岷也。”[21]自苏轼去世后,苏过几乎陪伴了苏辙整个晚年,“过也昔孤,而归公于许,奉杖屦者十春”[22]。苏过对叔叔的归心知之甚深。苏辙至交张舜民在《祭子由门下文》中说:“传闻治命,返葬眉阳。欲践誓言,颠沛不忘。”因而孔凡礼先生说:“辙遗命返葬眉阳。”[23]不为无据。政和二年九至十月间,僧人智昕回归蜀地,向苏辙辞别。故人的西归,更撩起了垂暮之年的老人思归故土的浓浓情思,苏辙写下《广福僧智昕西归》诗以赠,诗中又一次提到父亲要兄弟俩归葬先茔的遗命和自己归葬故乡的一贯决心:“平生指庚壬,终老投此身。”[24]
虽然苏轼兄弟最终葬于距离故乡千里之遥的嵩山,但是苏辙时刻惦念着身后能够归葬家乡。苏轼葬地名曰“小峨眉山”,这使很多人想到苏轼心中也是有浓浓的故乡情结的,不能归葬故乡,或许本不是他的最终愿望,只是他的无奈之举。
宋代的理学家们对于归葬故乡也有较多的讨论,程颐就说:“古之适异方死,不必归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骨肉归于土,若夫魂气,则无不至也,然观季子所处,要之非知礼也。”[25]但是很多人是难以做到如季子之子那样葬在异乡的。
同时,他又记述到:“(彭思永)未冠,居尚书丧,以孝闻。家贫无以葬,昼夜号泣,营治岁终,卒能襄事。扶丧数千里归庐陵,知者无不咨叹。”[26]这个事情很能说明当时社会是有归葬之风的。所谓狐死首丘,落叶归根,程颐把这件事慎重地记在《故彭侍郎致事彭公行状》之中,说明他是把这件事作为状主一生中的大事,也说明他对彭思永此举的赞赏。
宋代普通人的流动性不强,常年在外的大致有这几类人:官员、游学仕举之人、戍卒和商人。仅以官员为例,北宋初,内外官员仅几千人,到仁宗皇祐年间已达两万多人,到嘉祐年间更“十倍于国初”。这时按20万人来计算,加上亲属役仆,应该不少于100万人。据贾志扬估计,宋代参加科举的人数在11世纪大约为7万9千人,到了13世纪,这个数字则增加到了约40万人。[27]这构成了一支庞大的流动人口。
两宋加强制度建设,禁止官员在本地做官,以防止徇私舞弊事件发生。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宋朝收复东南地区,不久即下诏规定见任文武官“悉具乡贯历职、年纪、著籍以闻”,即要求官员须如实具报本乡籍贯所在,建立档案以便将来差注时有所照。宋神宗时,禁止官员在自己的产业所在地任官,这是地区回避法的延伸。仁宗时,知会稽县曾公亮因其父亲买田境中而被贬官,降监湖州祭酒,这说明了地区回避法更加完备。这些措施加强了宋代官员人口的流动性。
很多官员,如苏轼,常年在京城或者在地方任职。家眷就和他一块颠簸于任上,有些就病逝于路上,如他的妻子王弗于元丰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乳母任采莲跟从其“官于杭、密、徐、湖,谪于黄。元丰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临皋亭”,侍妾朝云也于“绍圣三年七月壬卒于惠州”。[28]
这些在外地任职的官员和其亲属在异乡去世后,很多都要归葬家乡,如高宗时,范如圭就因奉亲柩归葬故乡而向高宗请求离去。[29]归葬故乡必然会影响到葬期,如果这些逝去的官员或者其亲属所在的地方距离故乡较近,那么归葬故乡的时间会短一些,葬期就会短些,反之,葬期就会比较长。
归葬故乡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还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元祐七年,苏轼上书提到刘季孙“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于官所。家无甔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今者寄食晋州,旅榇无归”[30]。
欧阳修在怀念谢公的挽词中也感叹:“前日宾斋宴,今晨奠柩觞。死生公自达,存殁世徒伤。旧国难归葬,余赀不给丧。平生公辅志,所得在文章。”[31]说的也是谢公死后由于没有财力而不能归葬故乡。
为了归葬故乡,经济困难的就只好想办法去筹集费用,有些因之卖掉自己的女儿。马魁的父亲到了中年也没有儿子,于是就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做妾,但是妾总是偷偷地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并且心情沮丧。马魁的父亲就私下里问她原因,小妾告诉他:“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获归葬乡里。母乃见鬻,得直将毕葬事。今父死未经卒哭,尚约发以白缯,而以绛彩蒙之,惧君之见耳,无他故也。”[32]
袁韶的父亲为小官吏时,夫妻近四十岁都没有儿子,便从临安买回一个女子作为妾,“察之有忧色,且以麻束发,外以彩饰之。问之,泣曰:‘妾故赵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殁家贫,故鬻妾以为归葬计耳。’”最后,袁韶父“尽以囊中赀与之,遂独归”[33]。
有的地方官员也会体恤下属,而给予卒于任上的官员以特殊的照顾,使其能够魂归故里。如果没有官府的资助,这些官员的归葬几乎是不可能的。胡石壁在《送司法旅榇还里》公文中写道:
司法到官,未及逾年,遽至于斯。家贫子幼,道阻且长,世无巨卿可以托死,营护归葬,谁其任之?当职辱在同僚,固不敢禁脱骖之赙,然出疆之后,则吾未如之何也已。昔申屠子龙送同舍人伍子居之丧,以归乡里,遇司肆从事于河巩之间,从事又为之封传护送。今司法旅榇将自湘乡登舟,醴陵、安陆二邑皆潭属也,都运、安抚大卿必所乐焉。备申运司,乞行下湘乡与之雇舟,醴陵与之雇夫,凡所费用皆所自备,不敢为两县之扰,特欲借官司之力,以图办事之易耳。王诚既为厅吏,虽万里之程亦当往送,况千里之近乎!如或半途而反,定行决断。[34]
全文情意深长,合乎情理,又将路途事宜一一妥当安排,字里行间表达出了一个官员对下属的关怀体恤之情。
也有借助于友人的力量而还葬故乡的。苏轼有个朋友巢谷,听说苏轼贬谪海南,不顾自己七十岁的高龄,不远万里去看他,结果到了新州就得病死去。苏轼资助其子子蒙路费,让他迎丧。[35]
表三是江西宋代归葬墓主一览表,从中可以看出,有宋一代江西一地归葬故乡的习俗很盛。这些归葬之人的葬期都在2个月以上,有些长达数年之久。
表三 南北宋江西外地归葬墓主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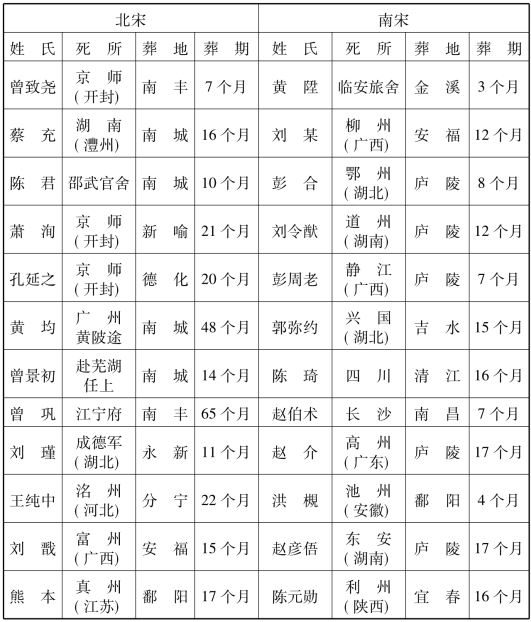
续表

注:本表中的葬地全部在今江西境内,其中加括号的为现在地名。本表采用梁洪生《江西宋代墓志及其丧期考》表5,略有删节。
宋代有很多制度对归葬故乡产生影响,如对于勋戚大臣的诏葬、不许遭贬流放官员归葬以及丁忧制度。
“勋戚大臣薨卒,多命诏葬,遣中使监护,官给其费,以表一时之恩。”[36]宋代施行的情况,大致符合此种描述。这其中有些就是由中使护送归葬故乡的。如杨守一于“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签署枢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赠太尉,中使护葬”[37]。张澹开宝七年六月,“权点检三司事”,不久病死,“太祖闻其无子,甚愍之,命中使护葬于洛阳”[38]。
宋代,由皇帝诏命归葬的人还有很多,高防为“枢密直学士,复出知凤翔。乾德元年卒,年五十九,太祖甚悼惜,赐其子太府寺丞延绪诏曰:‘尔父有干蛊之才,怀匪躬之节,朕所毗倚。遽兹沦亡,闻之衋伤,不能自已。矧素尚清白,谅无余资,殡殓所须,特宜优恤。今遣供奉官陈彦珣部署归葬西洛,凡所费用,并从官给。’”[39]
贬官在外的臣子死后是不许归葬故乡的。赵鼎受秦桧构陷,最后谪贬吉阳,在绍兴十七年“遗言属其子乞归葬,遂不食而死”,直到第二年才得旨归葬。[40]宁宗庆元二年,赵汝愚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在路过衡州时,突然死亡,“诏追复赵汝愚官,许归葬,以中书舍人吴宗旦言,罢之”[41]。吕大防哲宗时贬谪“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在虔州信丰病死。其兄吕大忠请归葬,哲宗许之。[42]
理宗时曾下诏:“吴潜、丁大全党人迁谪已久,远者量移,近者还本贯,并不复用。”但是当吴潜“没于循州,诏许归葬”。后来“丁大全溺死滕州,诏许归葬”[43]。贾似道在其死后,也诏许其归葬。[44]
以上是准许贬官归葬的个例。宋代也曾下诏让在流放地域死去的部分官员归葬。如真宗咸平年间曾下诏:“诏命官流窜没岭南者,给缗钱归葬。”[45]“如亲属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46]理宗时也曾下诏:“诏应谪臣僚终于贬所者,许令归葬。”[47]恩许归葬算是对在外的贬官的恩遇。
这些遭贬流放而死在外地的官员,即使死时不能归葬,也想在一段时间后能够归葬故乡。从上面引到的例子来看,这些死在外地的官员是不被允许归葬故乡的,除非得到诏令允许归葬。哲宗时,刘挚涉连“同文馆狱”,恰好病死,亲属受到牵连,被徙英州三年,死于瘴气的有十个人。一直到徽宗时,才“诏反其家属,用子跂请,得归葬”[48]。刘挚死在英州的十个亲属,在等待归葬的岁月里,可能就是殡在某所等待归葬,时期从“同文馆狱”发生的时间哲宗绍圣四年到徽宗朝,葬期较长。
“丁忧”亦称“丁艰”,是古代遭父母之丧的通称。早在周朝时期,我国就产生了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丁忧丧俗,如《礼记·丧服》所载“三年忧,恩之杀也”,《礼记·三年问》所载“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倡扬重丧,如《孟子·离娄下》阐扬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足以当大事”的丧礼思想。
汉代以降,“丁忧”服丧不仅成为儒家表达孝心、弘扬孝道的礼法制度规定,而且演化成为历代王朝“孝治天下”的强制性法律措施。仕宦官员作为中国古代孝治施政的管理阶层,他们除必须严格遵守上述“丁忧”法律的普遍性规定之外,还必须在三年“丁忧”期间解官去职。“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49],“古者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50],这是先秦时代已经实施的官场成例。从法律角度对官员进行规定的则是唐代的《唐律疏议》,其中规定“诸父母死应解官,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51]。疏议曰:“父母之丧,解官居服,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后代法律中多沿袭此条文。在宋代,诏“在官丁父母忧者,并放离任”[52]。宋代较为重视孝道,宋初时,官员服丧期间,夺情起复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仁宗时夏竦官至知制诰,天禧年间坐事降知贵州,天圣初又被重用。而正当此时其母去世,为了仕途发展,夏竦潜至京师求起复。[53]仁宗朝时,在士大夫的共同推动下,北宋士风大为改观,史载:“当是时,雅惬众心,小使臣往往丧其父母者多矣。不二十年,世变风移,今无睹不愿持丧者。”[54]其后“富(弼)公以宰相丁母忧,仁宗诏数下,竟终丧不起”[55]。一旦士大夫违背了丁忧制度,无论有意无意,都将被舆论所指责。至和年间,益州推官桑泽,由于不知其父已死,投牒自陈,“人皆知其尝丧父,莫肯为作文书,泽知不可乃去,发丧制服”[56]。桑泽后来虽然服丧期满,但仍然被视为不孝,坐废归田,终身不齿于士林。宋代的丁忧制度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弘扬孝道,但是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葬归故乡的风俗,毕竟官员是居家在外的一个庞大群体。因为丁忧制度是指官员为服父母之丧而离职,所以此制度影响的应该是在职官员父母的葬期。小于四十岁而死于任上的年轻官员,由于经济等因素所限,往往不能归葬故乡,而是葬于居官之地,从而葬期较短。有论者指出宋代丧期长短与年龄大小有关,享年不足三十九岁的,葬期多数较短。享年较短被认为不吉,故葬之从速。[57]以此观之,此论未必妥当。
宋代上述的这些制度对葬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丧葬中的择日和风水
丧葬中的择日和风水也是影响葬期的重要因素。
先秦时卜日者有卜人、占者、莅卜等。卜日事前已有意向,卜人等按照既定程序进行占卜,如结果为吉,便从,告知主人,丧葬仪式继续进行;如结果为凶,即不从,需要另择葬日。[58]秦汉时对卜葬日更加重视,已发现的秦汉简牍中有很多关于丧葬择日的记载。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稷辰》,就对可葬的日子和不可葬的日子划分得很详细。[59]丧葬择日的习俗影响深远,宋代朱熹就在《朱子家礼》说,三月而葬,先选好日子再下葬。韩琦死后选择日子下葬,还由此引发了苏轼请求皇帝罢秋宴的札子:“魏王之葬,既以阴阳拘忌,别择年月,则当准礼以诸侯五月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为未葬之月,不当燕乐,不可以权宜郊殡便同已葬也。”[60]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近代。择日而葬的习俗也影响着葬期的长短。
宋代丧葬普遍重视墓地风水的选择。不只是普通百姓,皇帝和士大夫对风水也很重视。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风水的起源应该很早,《孝经》载:“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这是相墓地,是用占卜的方法择定地点。晋时郭璞的《葬书》将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抽出,对风水下了定义,并全面构架起风水理论,奠定了后世风水的基础。他首倡“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被称为风水鼻祖。魏晋南北朝时丧葬就比较重视风水,隋唐时风水之术更盛。宋代陈抟、邵康节、朱熹以及蔡元定等著名易学家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一些风水著作相继刻印,从而出现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随着风水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风水的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九》记真宗乾兴元年八月六日司天监上奏说:“太宗梓宫先下丙地内奉安,按经书壬丙二方皆为吉地,今请灵驾(按:此指真宗梓宫)先于上官神墙外壬地新建下官奉安,俟十月十二日申时发赴丙地幄次,十二日申时掩皇堂。”此处依照当时的风水地理之说。当时此说将姓氏分归宫、商、角、徴、羽五音,与五行方位相配,各姓自有大吉大利的方位。赵宋国姓(皇帝之姓)归于角,利于丙壬之方。赵宋诸山陵当选在吉方(丙壬之方)。
大约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宁宗朝的赵彦卫是魏王廷美七世孙,他在《云麓漫抄》第九卷记载宋代帝陵时说:
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冈阜,不甚高,互为形势。自永安县西坡上观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织,万安山来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计一百一十三顷,方二十里云。今绍兴攒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有上皇山新妇尖,隆祐攒宫正在其下。
1961年发掘的宋代皇室亲王赵 夫妇合葬之墓,从出土的两方墓志可以看到,赵
夫妇合葬之墓,从出土的两方墓志可以看到,赵 逝于元祐三年七月戊申,癸酉殡于正寝的西边,九月甲寅出殡在都城西边的普安佛祠,一直到元祐九年二月乙酉下葬。他的夫人死在崇宁二年,葬在大观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前者葬期为六年多,后者近四年。二人葬期较长的原因是前者“太史言岁月未利”,后者“太史卜远日告吉”,显然,这和相信风水吉日,追求吉利有关。[61]
逝于元祐三年七月戊申,癸酉殡于正寝的西边,九月甲寅出殡在都城西边的普安佛祠,一直到元祐九年二月乙酉下葬。他的夫人死在崇宁二年,葬在大观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前者葬期为六年多,后者近四年。二人葬期较长的原因是前者“太史言岁月未利”,后者“太史卜远日告吉”,显然,这和相信风水吉日,追求吉利有关。[61]
皇帝也将敕葬作为对臣子的一种恩宠和礼遇,但是有时却未必取得好的效果,这里面就有风水的因素。
贵臣有疾宣医及物故敕葬,本以为恩。然中使挟御医至,凡药必服,其家不敢问,盖有为所误者;敕葬则丧家所费,至倾竭资贷,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谚曰:“宣医纳命,敕葬倾家。”庆历间始诏已敕葬而其家不愿者,听之。西人云:“姚麟敕葬乃绝地,故其家遂衰。”[62]
本来风水的理论化就是在一些士大夫手中完成的,一些风水理论也由他们慢慢向民间传播。苏轼死在常州,千里迢迢葬在嵩山支麓。朱熹费尽辛苦预卜葬穴,罗大经感叹道:“余尝怪苏公子瞻居阳羡而葬嵩山,一身岂能应四方山川之求;近时朱公元晦,听蔡季通预卜葬穴,门人裹糗行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63]
宋代关于风水的故事很多,有些是关于上辈葬于好风水而后代得吉利的,有些是关于风水师的。
沙县叶公未第时,求阴宅葬其先人,未得。一日有林玑者谒之,曰:“北距县五里山名罗源,有地可葬,葬后一纪,定出蟾苑客。”因曰:“卧龙欲腾头角起,乃安龙头案龙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孙折桂无穷已。”叶公曰:“本朝自来辰、戌、丑、未年为廷试,何得申、酉耶?”客曰:“五行推迁乃若此。”后国家以寇难多事,廷试忽移戌、申年,是岁叶果登第,计其葬,恰一纪。[64]
风水与后代福祸的因果关系,在人们口头传说和文字记载中得到了应验。葬于风水绝佳之处,则会富及后代,反之,则会祸殃子孙。人们对于风水的记载,应该经过了有意和无意的选择,那些应验了的被作为风水灵验的例子,而那些不灵验的则就湮灭无闻了。“希夷为明逸卜上世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见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后,世世当出名将。明逸不娶,无子,自其侄世衡至今,为将帅有声。”[65]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了事关蔡元度的风水事例:“蔡太师父准葬临平山,山为驼形,术家谓驼负重则行,故作塔于驼峰,而其墓以钱塘江为水,越之秦望山为案,可谓厷矣,然富贵既极,一旦丧败,几于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师之不可信如此。”[66]
葬地和葬日的选择必然使下葬时间后延,可能导致葬期绵延数月乃至数年。
(三)影响葬期的经济原因
宋代,影响丧葬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丧葬本身要消耗一定的物质材料,而且土葬还需要土地。宋代土地兼并严重,宋朝刚建立时,宋太祖就对功臣、亲族、官僚等赐予大量的土地,此外,寺院、道观也占有大量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很多人没有土地。南宋时,土地兼并更加厉害,一批皇亲贵戚、武将文臣逃到南方后大量占有土地。高宗以后,历朝权臣中占地数十万亩的比比皆是。除这些权臣外,其他贵族官僚乃至寺院、商人也大量占有土地,出现了“吞噬千家之膏腴,连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的土地所有者[67]。
大量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使很多庶民失去土地。北宋仁宗时,一半以上的人沦为佃户,南宋时这一比例则发展到三分之二。没有土地的庶民遇到丧葬之事就只能购买殡葬所需的土地,如果临时无经济能力,就只好久死不葬,从而使葬期延长。有些人死后无地可葬,只好改用火葬或者水葬。在宋人的记述中就有“凤州贫民不能葬者,弃尸水中”的事例。[68]这当然是因贫穷而没有可葬之地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因为弃尸入水是不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为当时舆论所不容。
宋代还有许多贫不能葬的例子,如郑獬死的时候“家贫子弱,其柩藁殡僧屋十余年”,一直到滕甫为安州知州的时候,才将其安葬。[69]不能得以安葬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困难,由于贫穷,郑獬的葬期长达十余年,不可谓短。
查道参加科举考试,路过滑台,经过父亲朋友吕翁的家。吕翁去世,家里因贫穷而不能安葬,“其母兄将鬻女以襄事”,查道用亲族为自己赶考而凑的钱全部送给吕翁家,用做丧葬费用,并为其女儿选择丈夫资助其出嫁。[70]这件事详细地记在查道的本传中,作为查道的美德而加以赞颂。
有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也可以使葬期不至于拖得太长,如上面提到的查道资助父亲朋友下葬就是一个例子。有些是同僚资助下葬,如“有尝同僚者死不克葬,子俑食他所,善应驰往哭之,归其子而予之赀,使葬焉”[71],即为一例。
宋代还有相应的制度来资助逝去的官员下葬,“凡近臣及带职事官薨,非诏葬者,如有丧讣及迁葬,皆赐赙赠,鸿胪寺与入内内侍省以旧例取旨。其尝践两府或任近侍者,多增其数,绢自五百匹至五十匹,钱自五十万至五万,又赐羊酒有差,其优者仍给米麦香烛。自中书、枢密而下至两省五品、三司三馆职事、内职、军校并执事禁近者亡殁,及父母、近亲丧,皆有赠赐。宗室期、功、袒免、乳母、殇子及女出适者,各有常数。其特恩加赐者,各以轻重为隆杀焉”[72]。辛炳死后,高宗就下诏:“炳任中执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贫无以葬,赐银帛赙其家,赠通议大夫。”[73]宋朝的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定级别的官员死后因贫不能葬的状况。
对于普通庶民或没达到规定级别、不能接受官助的官员,在亲人死后又不忍心使亲人久不能葬,那就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有卖物葬亲的。牟子才死后,“家无余赀”,其家“卖金带乃克葬”。[74]还有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卖儿卖女的。
有求助于别人的。柳开在大名“尝过酒肆饮,有士人在旁,辞貌稍异”。柳开就询问他,对方回答说,“至自京师,以贫不克葬其亲,闻王祐笃义,将丐之”。[75]吕祖泰丧母无以葬,至都谋于诸公,得寒疾,索纸书曰:“吾与吾兄共攻权臣,今权臣诛,吾死不憾。独吾生还无以报国,且未能葬吾母,为可憾耳。”“尹王(赵)柟为具棺敛归葬焉。”[76]
《宋史·孝义传》中记载了几则颇为感人的事例,如刘孝忠在母亲死亡后,“佣为富家奴,得钱以葬”[77],又如“(田)颜无子,不克葬,(侯)可辛勤百营,鬻衣相役,卒葬之”[78]。
在《华阴侯先生墓志铭》中,程颐记载了墓主生前的一件事:侯可的好友申颜“谋葬其先世而未能,颜死无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图,不足则卖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时方天寒,先生与其子单服以居”[79]。
苏轼记载了另外一件事:进士董传父子死,“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谋口腹不暇,决不能葬。轼与之故旧在京师者数人,相与出钱赙其家,而气力微薄,不能有所济,甚可悯矣。公若犹怜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传者足矣。陈绎学士,当往泾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赐之,轼且敛众人之赙,并以予陈而致之宋,使葬之,有余,以予其家”[80]。
至于因贫穷而不能葬其亲,而又于心不忍却不能得到资助的,就只能如李豸那样,“三世未葬,一夕,抚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学,而亲未葬,何以学为!’”[81]
(四)影响葬期的其他因素
葬期是习俗、法令、现实条件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除去前面提到的影响葬期的两个因素外,另外几个因素也不容忽视。
葬期和风俗有关,厚葬的社会风气也必然会影响到葬期。宋代的厚葬风气虽不如前代,并且有不得厚葬的禁令,但是还是有人在言论上提倡厚葬,如宋太宗时的李昉从“孝道”出发,要求对厚葬加以开禁:“子孙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亲,全尚朴素即有伤孝道。其所用锦绣,伏请不加禁断。”[82]在民间也有很多厚葬的事例。
也有人为了尽“孝道”而使自己的父母双亲久殡不葬,如朱云孙在母亲病时“血指书祷”,“剔骨”为食,其母“丙辰除夕前两日”亡,于“其岁壬戌其月癸卯”下葬,中间经历了很长时间。[83]
迫于战乱而仓促下葬的事例主要集中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以及南宋末年。这段时间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侵,受此侵扰的地区,葬期就会相应比较短,如邓柔中于建炎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亡,“诸孤以寇盗未戢,襄事不可缓,即以九月二十一日葬公”[84],其葬期不超过四周。还有宋朝宗室赵仲湮,于建炎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死,十二月四日葬,葬期只有九天。[85]这些人的葬期不能说和战乱没有关系。
在佛教等宗教影响下,两宋火葬也极为盛行。在北宋时期,河东和汴京两地盛行火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86]。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也说河东人众而地狭,民家有丧事,“虽至亲,悉燔热,取骨烬寄僧舍中。以致积久,弃捐乃已,习以为俗”。据近代考古发掘发现,其他地方也存在火葬的遗迹,1953至1955年,在成都就发现很多例子。[87]1952年,在绵竹发现很多骨灰罐,上面都有文字记载,其中有一个记载:“浴室院,熙宁八年五月内寄骸骨,不知姓名,崇宁三年十二月七日葬,甲字第三十八字号。”[88]这些就是在焚尸后将骨灰罐寄存在寺庙中,由寺庙集中埋葬的案例。
王庠的父亲为官正直,因受到同僚的排挤而丢官,在他死时,王庠的母亲手扶其父灵柩对王庠兄弟发誓,要等到其父获赠官后才归葬。[89]在宋代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古者将葬,请谥以易名,近世多槁殡或已葬而请谥”[90]。其中有些殡而不葬的恐怕就和王庠之父类似,是为了给死者请到一个谥号,以便风风光光地下葬。
三、待葬于寺庙
从表一统计的563例葬期数据可以看出,六个月以上下葬的有352例,占到一半以上,其中一年以上的有232例,超过三分之一。不能及时下葬的骨骸都要暂时寻找一个处所放置起来,一般以寄放在寺庙为多,也有一些放置在家中或者其他地方。
两宋皇帝死后,多殡在宫中待葬,如太祖和太宗均殡在“殿西阶”。“殿西阶”的范围就在宫内。而皇后嫔妃死后有些是殡在宫中,如真宗妃杨淑妃,景祐三年无疾而薨,年五十三,殡于皇仪殿,“帝思其保护之恩,命礼官议加服小功”[91]。但其多数是殡在寺庙中,如太祖宋皇后,“至道元年四月崩,年四十四。有司上谥,权殡普济佛舍”[92]。章懿卒,先殡奉先寺。[93]太宗李皇后,景德元年崩,年四十五,谥明德,权殡沙台。仁宗生母李宸妃薨,其初,章献太后想用宫人的礼节葬在外面,丞相吕夷简反对,最终用一品礼,殡洪福院。[94]庆历六年七月洪福院失火,仁宗随即下诏将寺院的庄产、邸店赐给章懿皇太后家。[95]这个事例证明洪福院和皇家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者本来就是皇家的专有寺庙。真宗生母李氏死于太平兴国二年,葬于普安院,真宗即位后才将其改葬。此外,真宗封禅、祀汾阴前后均到普安院辞行或恭谢。[96]南宋时,周密也提到:“旧瑞龙寺,后为安穆、成恭、慈懿、恭淑四后攒所。”[97]这些事例说明两宋有专门提供嫔妃殡所的寺庙,这些寺庙和皇家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上上述殡所,也有嫔妃殡在宫中,真宗郭皇后在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崩,二十五日殡于万安宫的西阶。[98]还有殡在家中的,熙宁九年仁宗沈贵妃薨,神宗“许出殡其家”。[99]
一般的士大夫及庶民死后若不能短时间内下葬,也以殡在寺庙中的居多。
洪迈《夷坚志》记述,县令毕造的长女死后殡在京城外僧寺,寒食节的时候全家去扫祭,二女儿发现菆室的旁边有士人居住,在其居所发现有大姐的铜镜,从而发现大姐和士人的奸情,大姐的回生之术因此遭到破坏,于是施法致死二女儿。故事本身只可作为一个传说,不过里面提到死后殡在寺庙中应该是当时人们熟悉的一个场景。[100]陆游的幼女夭亡后,“菆于城东北澄溪院”[101]。
吴材老曾对洪迈讲述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吾居余杭县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与僧饮酒歌笑,旁若无人,通衽席之好”[102]。李椿字寿翁,洺州永年人,“父升,进士起家。靖康之难,升翼其父,以背受刃,与长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殡佛寺,深竁而详识之。”[103]
洪迈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邵武光泽县天宁寺多寄菆。行者六七人,前后皆得痴疾,积劳悴以死。唯一独存,亦大病,自谓不免。已而平安,始告人曰,每为女子诱入密室中。幽牕邃合,床褥明丽,缔夫妇之好。凡所著衣履,皆其手制。如是往来且一年久。一日,土地神出现,呼女子责曰:“合寺行者,皆为汝辈所杀,岂不留一人,给伽蓝扫洒事,自今无得复呼之。”女拜而谢罪,流涕告辞。自此遂绝,始能饮食,渐以复常。念向来所游处,历历可想,乃邑内民家女菆房,白其父母发视。盖既死十年,颜色肌体皆如生,傍有一僧鞋已就。两手又抱只履,运针未歇,枕畔乌纱巾存焉。父母泣而改殡。[104]
这个故事发生地点是邵武光泽县天宁寺,是个地方小寺,自不能和上文中提到的京城外僧寺相比,但是也存有很多待葬之柩。
宋代佛教兴盛,南宋人记述当时的杭州“凡佛寺,自诸大禅刹如灵隐、光孝等寺,律寺如明庆、灵芝等寺,教院如大传法慧林慧因等,各不下百数所之外,又有僧尼庵解院庵舍,白衣社会道场,奉佛处所,不可胜纪”[105]。
这些寺庙往往很大,宋英宗治平三年规定“诏应无额寺院,屋宇及三十间以上者,并赐寿圣为额;不及三十间者并行拆毁”[106]。秀州精严寺“凡为秀王祠堂三间,戒坛一所,廊庑三十四间,法堂一十一间,僧堂六间,两花堂五间,前资寮、行堂共一十三间,旃檀林后架二十间”[107]。宋神宗熙宁末年,“天下寺观、宫院四万六百十三所,内在京九百十三所”[108]。
这些寺庙已经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像救济灾贫、施药治病、挖井修路等,停放待葬之柩是其社会功能的一部分。
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绍兴十五年,许中叔步入某寺,见“藏院后列殡宫十余所,皆出木牌书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后曰提辖林承信”[109]。这个故事带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其中的场景一定是当时人非常熟悉的,绝对不会向壁虚构。从本书中还可以看到其他的例子,“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后皆墓域。僧寺两庑,菆柩相望,风雪阴雨。辄闻啾啾之声,盖鬼区也”[110]。从中可以看到宋代有些寺庙已经设置有专门的房间,给不能下葬的人作为停柩之所。寺庙提供这项服务是否向事主收取一定的费用?从现有资料来看,这应该是一种义务,是寺庙诸多社会功能中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也有的停放在家中,庄绰记载宋代有些人“又信时日,卜葬尝远,且惜殡攒之费,多停柩其家,亦不舍涂甓,至顿至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111]。也有暂时存放在其他地方的,如“青田县吏留光死,家贫未能葬,殡于城隍祠前。次年,冢为雨所坏”[112]。
【注释】
[1]宋人卒葬日期部分据《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荣丽华:中华书局,1993年)的宋代部分所载近年来出土墓志铭、墓表、神道碑、圹记,部分根据宋人文集包括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朱熹、叶适、夏竦、黄庶、李觏、刘敞、曾巩、王安石、王安礼、黄庭坚、曾肇、惠洪、谢逸、吕南公、汪藻、刘才邵、胡铨、汪应辰、周必大、曾丰、陆九渊、杨万里、文天祥、包恢、徐元杰、刘辰翁等人。其中时间推算依据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4年,宋代部分)。按,本文所有涉及日期推算均依据此书,不再一一作注。
[2]《宋赠太常丞苗公墓志铭》,转引自荣丽华主编:《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87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3]《宋故宣德郎冯君墓铭》,转引自《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第202页。
[4]《宋故福清县太君李夫人墓志铭并序》,转引自《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第194页。
[5]以苏轼为例,其传世文集中,墓志铭和行状有范景仁、滕甫、张文定、王子立、李太师、司马光、苏廷评,这些人都属于士大夫阶层,宝月大师、陆道士为作者友人,刘夫人出身世家,王氏、任氏、杨氏、朝云或为妻,或为保母,或为乳母,或为侍妾,均与作者有特殊关系。
[6]赵令畤:《侯鲭录》卷六《石志起颜延之王球石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3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7]按,现在发现最早使用“墓志”一词的是北魏刘贤墓志,见赵超《古代石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但是墓志应用较早,可追溯到汉代。宋及其前代的士人多用墓志,从《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即可看到此规律。
[8]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九《僧寺画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6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9]脱脱等:《宋史》卷四六四《向传范传》。
[10]此表依据《宋史》各本纪制作,北宋除去徽、钦二帝,南宋除去恭、端二帝,共计13帝。
[11]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一《仕宦归故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12]梁洪生在《江西宋代墓志及其丧期考》中(《南方文物》1989年第1期,第94页)指出其所列41种宋人文集中,江西人葬外地的20例,北宋18例,南宋仅2例。参照《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的宋代部分,从整个地域来看,也是南宋葬在外地的比北宋少。
[13]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三《民俗火葬》,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14]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二下《伊川先生语二》,第58页。
[15]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九《闵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8页。
[16]郭璞:《葬书》,《中国历代奇书》全新校勘图文珍藏版,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179页。
[17]苏轼:《苏轼全集》文集卷五六《与王敏仲八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42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18]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三苏全集》,第18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480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19]苏辙:《栾城集》《再祭亡兄端明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90页。
[20](宋)苏辙:《北归祭东茔文》,《三苏全集》,第18册,第478页。
[21]苏过著,舒大刚等校注:《斜川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558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22]苏过著,舒大刚等校注:《斜川集校注》,第557页。
[23]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158页。
[24]苏辙:《广福僧智昕西归》,《三苏全集》,第16册,第559页。
[25]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三《二先生语三》,第58页。
[26]程颢、程颐:《二程集》卷四《故户部侍郎彭公行状》,第489页。
[27]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出版公司,1995年,第35~36页。
[28]苏轼:《苏轼全集》,第962页。
[29]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一《范如圭传》。
[30]苏轼:《苏轼全集》卷三五《乞赙赠刘季孙状》,第1318页。
[3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谢公挽词三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6页。
[32]何薳:《春渚纪闻》卷一《马魁二梦证应》,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33]脱脱等:《宋史》卷四一五《袁韶传》。
[34]佚名辑:《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二《送司法旅榇归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35]苏轼:《苏轼全集》卷五六《与孙叔静七首(之六)》,第1835页。
[36]脱脱等:《宋史》卷一二四《凶礼三》。
[37]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七《杨守一传》。
[38]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九《张澹传》。
[39]脱脱等:《宋史》卷二七《高防传》。
[40]脱脱等:《宋史》卷三六《赵鼎传》。
[41]脱脱等:《宋史》卷三七《宁宗一》。
[42]脱脱等:《宋史》卷三四《吕大防传》。
[43]脱脱等:《宋史》卷四五《理宗五》。
[44]脱脱等:《宋史》卷四七《瀛国公二王附》。
[45]脱脱等:《宋史》卷七《真宗二》。
[46]王栐:《燕翼诒谋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
[47]脱脱等:《宋史》卷四五《理宗五》。
[48]脱脱等:《宋史》卷三四《刘挚传》。
[49]《礼记·王制》。
[50]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八四《丧葬部总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1]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2页。
[52]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五七《丧葬部汇考二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5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35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54]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75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55]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忠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页。
[5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631页。
[57]按,梁洪生在《江西宋代墓志及其丧期考》持此论点。综前所述,葬期与当时归乡葬及丁忧制度有关,官员对于逝去的父母由于有制度保证,可以从容还葬故乡,而对于去世的仆从和早逝的妻儿只能匆匆下葬或是暂殡某所,等到有机会再返柩故里。这些人的葬期或者很短,或者很长。《夷坚志》记载,袁从政偕妻子陈氏赴官任,“既之官,未满秩,陈亡,不能挈柩归,但殡道旁僧舍之山下”。
[58]《仪礼·士丧礼》。
[59]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72页。
[60]苏轼:《苏轼全集》卷二九《论魏王在殡乞罢秋宴札子》,第1196页。
[61]周到:《宋魏王赵 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年第7期,第352~353页。
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年第7期,第352~353页。
[62]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63]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06页。
[64]委心子撰:《新编古今分门类事》卷一七《叶公阴宅》,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0页。
[65]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9~70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66]陆游:《老学庵笔记》,第79页。
[67]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备对札子》。
[68]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69]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一《郑獬传》。
[70]脱脱等:《宋史》卷二九六《查道传》。
[71]脱脱等:《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
[72]脱脱等:《宋史》卷一二四《凶礼三》。
[73]脱脱等:《宋史》卷三七一《列辛炳传》。
[74]脱脱等:《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传》。
[75]脱脱等:《宋史》卷四四《柳开传》。
[76]脱脱等:《宋史》卷四五五《吕祖泰传》。
[77]脱脱等:《宋史》卷四五六《刘孝忠传》。
[78]脱脱等:《宋史》卷四五六《侯可传》。
[79]程颢、程颐:《二程集》卷四《华阴侯先生墓志铭》,第505页。
[80]苏轼:《苏轼全集》卷五《上韩魏公乞葬董传书》,第1669页。
[81]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四《李豸传》。
[82]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五《凶礼四》。
[83]杨万里:《诚斋集》卷一《夫人刘氏墓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84]刘才邵:《溪居士集》卷一二《邓司理墓志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85]荣丽华主编:《赵仲湮墓志铭》,《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第281页。
[86]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五《凶礼四》。
[87]刘志远等:《川西的小型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第92~98页。
[88]洪剑民:《我们对〈川西的小型宋墓〉的一点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第68页。
[89]脱脱等:《宋史》卷三七七《王庠传》。
[90]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第28页。
[91]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二《杨淑妃传》。
[92]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二《沈贵妃传》。
[93]王铚:《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页。
[94]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二《李宸妃传》。
[9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466页。
[96]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436页。
[97]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揽》,杭州:西湖书社,1981年,第67页。
[98]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三《凶礼二》。
[99]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二《沈贵妃传》。
[100]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七《毕令女》,第237~238页。
[101]陆游:《陆游集》之《山阴陆氏女墓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12页。
[102]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十《余杭宗女》,第264页。
[103]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九《李椿传》。
[104]洪迈:《夷坚志》乙志十八《天宁行者》,第336页。
[105]耐得翁:《都城纪盛》,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101页。
[106]曾巩:《隆平集》卷一《寺观》,明万历二六年刻本。
[107]徐硕:《嘉禾金石志》卷一八《精严禅寺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6988页。
[108]方勺:《泊宅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页。
[109]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二《莫小孺人》,第200页。
[110]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一一《芝山鬼》,第461页。
[111]庄绰:《鸡肋编》上卷《近时婚丧礼文亡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页。
[112]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六《范子珉》,第410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