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斯皮沃克与霍米·巴巴
赛义德之后,后殖民主义经过一批印度裔学者一系列复杂的争论和演变,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流派的理论方法,逐渐形成了三种理论风貌:以斯皮沃克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派,其主要著作有《在其他的世界》(In Other Worlds)等;以霍米·巴巴为代表的精神分析派,其代表作有《文化的场所》(The Location of Culture)等;以莫汉迪为代表的女权主义派。当然,还有五花八门的许多流派,但主要的,就是这解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三大家。如果用一句话去概括后殖民主义理论,我们可以说它延续了赛义德所提出的一个理论主题,即西方对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文化再现”。

盖娅特里·斯皮沃克
印度裔的斯皮沃克原是美国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英文系的教师,后来因翻译并长篇作序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一举成名,成为美国的主要解构主义阐释家。后来她又涉足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为后殖民主义的掌门人之一,自己也步步跃入美国学术界主流和中心,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不折不扣的学术明星。她的个人经历、学术训练和思想演变,也正是“充满了异质性”,与她的理论立场一致。“对异质性的解构”原本是解构主义的绝技。斯皮沃克运用起来是得心应手的。她分析种种极其复杂的殖民地国家的文化现象,的确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不过斯皮沃克也像赛义德一样,对于印度今天的文化发展和未来,从不关心,更不用说关怀印度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了。这样反过来看,她对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不关心现实政治的指责,也满可以用在她自己身上。当然,斯皮沃克会否定这一点。她会说,她实际上是在关心并且积极参与像美国这样的第一世界大国的文化政治。
斯皮沃克试图去寻找出一种方式或策略,来再现殖民地人民的经验、感受和思想。在此之前,这些本土的、民族的独特文化,被普遍化的殖民话语所压制,从而消失或者变形了。她应用解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自己独特的批评策略,在遗留下来的殖民话语的文本中,寻找某种模糊性,以此来解构殖民话语中的普遍主义。这是一个极复杂的文本读解过程。斯皮沃克对待殖民话语坚持一种解构的立场,并自认为在方法论和批判策略上有重大突破。如她的代表作《贱民能说话吗?》一文之中,就重点讨论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斯皮沃克运用解构主义方法,重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再现”和“代表”的论述。她认为,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论述,讨论了政治意义上的“代表”,和文化与意识形态意义即修辞上“再现”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两个词在英文里都是representation,但有不同含义。斯皮沃克的解构式重读,把马克思的论点阐释得更加复杂难懂。但我们仍能从中找到某些线索,来把握她的意思。她一方面批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脱离政治实践,从不关心社会实际问题,一方面又借马克思的口,来说明政治代表与文化再现之间的差异、错位,从而论证她的一项基本原则,即“被殖民化的贱民主体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异质性”。
霍米·巴巴解释他的政治立场,基本上也是如出一辙。巴巴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把殖民话语看成为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模拟”。弗洛伊德的后结构主义传入拉康,强调语言不断地错位、变换和替代它的“指涉物”或“所指”,就像人的“意识”不断压抑、转换“潜意识”。通俗一点讲,拉康说的也就是“指鹿为马”的意思。但指鹿为马并非全都是骗子的勾当,我们在日常语言行为里,就常常会作出这样的举动,我们的动机有时根本不是要骗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语言行为是下意识的。巴巴认为,殖民地的模拟性话语,就具有这种特点。在模拟殖民者话语的时候,掺进了异质成分,从而就把原来的殖民者的文化和语言搞混了,并且带有了某种颠覆、反抗的色彩。巴巴似乎是在说,你指鹿为马指多了,鹿也逐渐变得形象模糊起来,成了非鹿非马的四不像了。这四不像就是他所谓的“杂糅”,在巴巴看来,又有反抗性,但又不那么立场鲜明,正好是殖民地“模拟”文化或话语的特征。这种不确定、含混、割裂了的话语,听起来颇有点荒诞不经,但的确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巴巴等生活在西方的后殖民知识分子的心理上又困惑、又自视甚高的状态。我们如果问他:你模拟来模拟去,一头鹿难道就真的被你变成了一匹马吗?巴巴会告诉你,他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话语陈述的主体性问题,与指涉物无关。换句话说,殖民地的人民每天吃喝拉撒的实在问题,也就是你看到的究竟是马还是鹿的问题,并不在巴巴讨论范围之内。他要讨论的,只是谁在说和用什么语言来说的问题。当然,所指究竟是什么东西,的确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把说话人的主体性、社会地位和立场的问题牵涉进来,就更加复杂了。再套用指鹿为马的典故来看,你前面站着一头马,殖民者如果说那是一头鹿,你也许只好跟着说鹿,不能说那是马,即使你有心反抗殖民者。但你模拟他的“鹿”时,有意无意地使你的发音向“马”滑,你的语言就会构筑起一头四不像的形象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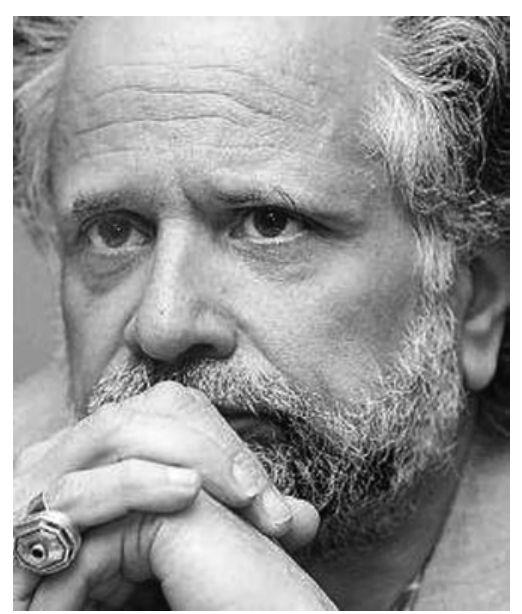
霍米·巴巴
我们也可以把巴巴的“杂糅”看成是对某些问题的遮蔽。回过头来看,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妨说是具有强烈政治逃避主义色彩的学院性理论话语。60年代西方轰轰烈烈的文化与社会革命失败之后,左翼知识分子纷纷回到学院书斋。当年的政治反叛青年,现在成了文化精英。因此,革命和改变社会的实践也就渐渐演变成了一种纯理论的话语活动。从政治实践上看这是一种退却,但从理论战场上看,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进取,用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的话来说,他们是“书斋里的革命家”,正进行着理论和话语的革命活动。诚如阿尔都塞之一再强调,理论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但是,这种话语革命毕竟是以遮蔽和忘却了政治经济问题为代价的。我们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两方面遮蔽或转移了问题。
第一是对其一个重要理论来源的掩盖和修正。这个理论来源,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开始于卢卡契,经过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等人的发展,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西方思想和知识界影响深远的流派。这些理论家在两个层面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一是否定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同时也批判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普遍人性论、本质论。第二方面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要害,是从未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思维方式上的局限。列宁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非人道的一面,即对广大第三世界和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而斯大林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继续了沙皇俄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是,西方许多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却回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尖锐批判。福柯把一切归结于话语中的权力问题。利奥塔和波德里亚等人,则只谈所谓修辞、叙事、话语等问题。
第二方面的遮蔽,就是所谓的“后学”理论几乎都不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亦即商品化的问题。在西方文化批评界,一谈商品化问题,就会有许多帽子:“简单化”、“教条化”、“经济决定论”或“简约化”等等。但资本主义的痼疾和要害,就在于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商品化的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化、商品化,已经全面渗透到第三世界和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人类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当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此基本上是回避和保持沉默。按理说,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商品化问题应该更为敏感。因为当代社会商品化在文化领域里特别严重,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前殖民地国家,艺术、审美的商品化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代名词。但是,所有这些“后学”都把这么严重的问题转换成语言和心理意识的问题。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的语言、潜意识的问题,无所不在。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客观上转移了文化批评对当代社会问题关怀的视线。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美国的人文学术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多半是印度裔的学者,印度的文化问题也就受到相当多的注意。与此相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众传媒对印度这样的国家却是忽视得厉害。在美国,普通老百姓一般对今天的印度这个所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制国家”,很少有兴趣去认真了解。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极为严重,宗教派系、种姓等级和不同族裔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增无减。印度人口估计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赶上中国。这将给印度本来就难以自给自足的经济造成更严重的危机。然而,对于印度社会的现实问题,那些印度裔学者们基本上是置若罔闻。这比较赛义德对阿拉伯解放事业的热情关怀,是可见出明显差异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