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历代方志爬梳——写在第二轮市志修编之时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明嘉靖《保宁府志》影印件
方志,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域文化,既有悠久的传统历史,又有非常独特的人文内涵。纵观历史,除了“盛世修志”这一现象得到认同与赞颂外,凡有所作为的良吏,莫不与一地之方志有种种不解之缘。史家们亦早有“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国无史,一代勋业弗彰;邑无志,一方典型不著”等说。有清一朝还特别规定,凡新知县上任须奉行32项“莅任初规”,其第三项即为“览志书”。可见,编修和利用方志均为从江湖到庙堂由来已久的大事。国史、家谱和方志,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的三大基本历史文献,就连西方的李约瑟博士也不无感叹地说过:“要研究人类文明,必须研究中国的地方志。”
方志者,乃地方之志也。方,指地方、方域;志,即纪,是记述或记载的意思。方志就是以某一特定区域为记述对象,全面记录该地方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及沿革等的资料和书籍。诚如近代方志学大家朱士嘉所言:“一方之总览”所载内容“则不外地理之沿革,疆域之广袤,政治之消长,经济之隆替,风俗之良窳,教育之盛衰,交通之修阻,遗献之多寡”。无论何种版本的方志,原则上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来均被视为繁博丰赡的文化瑰宝,是涵盖一个地域方方面面的“大百科全书”。
为追溯阆中方志脉络,窥其沿革概貌,笔者仅其视野所及,不揣作一爬梳,以就教于斫轮高手:
一、【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编《保宁府志》。
督修:分巡川北道蒲州进士杨瞻。
纂修:安岳县教谕杨思震。

挡得住数百年水啮,却挡不住“现代化”步伐的防洪堤坝“鱼翅”
作序:赐进士通议大夫巡抚延绥等处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郡人任维贤。
该志共计14卷, 2040页, 45万多字,插府属地域图1幅,郡治图1帐,州县图10幅(当时府领剑州、巴州、阆中、苍溪、南部、广元、昭化、江油、梓潼、通江、南江11州)。
2004年初夏,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古籍珍本室看过缩该微胶卷,封面正上方押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篆印,据了解原本现可能藏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南京、成都、阆中等地有复制件。 1993年版的《阆中县志》中也载明:“明嘉靖前所修阆州志、保宁府志均已失传”。
二、【清】初(按:年代不详):“始有李钟峨太史录《保宁府志》一册,然未付梓,其书不传。”(见道光《保宁府志》序)
巴蜀才子李钟峨,四川通江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后提督福建学政。曾主持《国史分韵》《大清一统志》等编修,在主编《盛京志》时写出《保宁府志》初稿,该志为研究巴山蜀水的风土人情留有珍贵史料,可惜不传。
三、【清】乾隆晚期,阆中训导毛于逵【简州人,乾隆己亥(1779年)举人】,尝手辑《阆中县志》十卷,搜罗废遗,一邑之文献以资。
四、【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曾纂修过一次《保宁府志》,因记载不详,亡佚后内容无从查考。
五、【清】道光元年(1821年),修《保宁府志》。
总裁:分巡川北兵备道盐运使衔湖南龙阳附贡黎学锦。
参阅:保宁知府徐双桂。
总纂:癸酉科拔贡史观等49人。
该志共62卷, 1334页, 48万多字,插图15幅,木刻本,成书列名46人。时府领剑州、巴州、阆中、苍溪、南部、广元、昭化、通江、南江9州县。
该志现保存完好,除本市图书馆、档案馆有存,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等亦有全套馆藏。
六、【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保宁府志·艺文志》七卷,《保宁府志·金石志》,史观辑。
七、【清】咸丰元年(1851年),知县徐继镛,延宫赞李惺等编修《阆中县志》。
李惺(1787年-1864年),号西沤,重庆垫江人,历任翰林院检校、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国子监习业等,著有《西沤全集》等。后以祖母年老为由辞官归蜀,掌成都锦江书院长达二十余年。《阆中县志》(共8卷,前6卷分24门、后2卷为志余,共629页,木刻本,插图4幅)即为这期间所修,现本市图书馆有藏。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等亦有全套馆藏。
八、民国15年(1926年),县知事岳永武聘郑钟灵、刘文选等重修《阆中县志》,分8卷30门,共330页,石印本,插图7幅。
九、民国37年(1948年),杨诚恭、李镜芙、孔震生编修《阆中县志稿》,共37志及大事记、文征、志余,计1215页,插图1幅。因时局动荡未能付梓,原稿现存四川省文史馆,本市图书馆有复印本。
十、 1958年版,编写《阆中地方志略》,计6章19节。
十一、 1959年版,编印《阆中县并地方志略》,计7章22节。
(按:以上两版均为缩写本,可能系为了解县情所需的普及性读物)
十二、 1981年版,由县志编修委员会编纂并出版《阆中县志》(帝制时期)。同年,《阆中县志》(民国时期)也已编纂成稿。后因要求县志编纂改“分时期记述”为“横分事类,纵述始末”,原计划停止实施。当时各部门、各区乡也开始修志,故县志办工作重点便转向指导部门和区乡修志。
十三、 1985年版,这是建国后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篇幅最多的一次修志活动,要求一般上限自1911年、下限为1985年。从1981年算起,共历时12载,九修篇目,六易其稿,全书1089页,计143万多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志下限虽为1985年,但定稿付印却已在1993年年底。

古城内现仍保存的一段明代老城墙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1983年-1990年)县属30多个部门编写了部门(专业)志, 7个区、 53个乡镇编写了区乡志。其中由当时的县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和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联合编纂出版了《阆中地理志》(沿革地理、自然地理),于1987年7月出版。这本专志虽仅限于内部发行,但它对1985年版的县志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这也是阆中第一部专志,曾获得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十四、 2005年版《阆中市志》,也即正在进行的第二轮方志编纂工作,本次编修明确上限起于1986年,下限断至2005年,初定于2010年年底出版,但方志的版别不同于其他普通出版物,窃以为还是应按断代年限表述为宜,若按常规称其为“2010版”,则必定从称谓到起讫年限都将带来混乱。
本次偏修时间跨度虽然只有20年,但这20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文化大创新、国际大接轨的重大变化的时期。完全可以预料,这部市志将会有以下特点:一是法律意识最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已于2006年正式颁布实施,各省、市也有了相应的细则规章,因此,“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作用将更加突出和彰显。二是行政区域特色最明显,昔日只有府志、县志,这次名正言顺称之为“市志”。可见“县”与“市”之概念不仅从根本上弄清理顺了,而且正在转化一种自觉的意识融于各项事业之中。三是时间最短而内容最为纷繁庞杂。从2007年12月正式启动算起,到2010年12月要求出版,仅用3年要完成5个阶段39个专志、至少将超过150万字的“市志”,仅此一点,也可堪称本地修编方志的“吉尼斯之最”。
综上10多个不同版本的阆中地方志(有的为分志)来看,咸丰元年(1851年)以前均为“府志”,之后为“县志”。但在此前后郡州府道治所同在阆中,方志中却鲜见“州、县志”,这与历史上的“附郭县”(指府治所在的县,县衙和府衙同城)现象有关,也即是在一般情况下,有了府志的附郭县就没必要再编纂县志。但据新发现的一些线索似乎也有例外:一是中国川剧官方网站《中国川剧网》《川北灯戏古今谈——巴文化的遗韵》文载:“明嘉靖壬午岁(1522年)刊印的《阆中县志》载:‘五月十五日瘟祖会,较诸会为甚,旧在城隍庙,会移太清观,醮天之夕,锣钹笛鼓,响遏云衢,演灯戏十日,每夜梵香如雾,火光不息,其所谓灯山者亦如上元时’”。可见,这条迄今为止最早的阆中方志记载【比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编《保宁府志》还早21年】恰好是“县志”,但因其出处不详,故未列入前文。二是民国15年(1926年)重修《阆中县志》附录有载:清乾隆年间阆中训导毛于逵“手辑《阆中县志》十卷”。同样值得探究的是此书不知何故既未刊刻出版,亦未在文献史料中被记录下来。此外,从道光元年(1821年)黎学锦主修《保宁府志》后,至民国2年(1913年)废府,其间还有近百年的府衙历史找不到记载,出现了不该有的“府衙空白期”。
我国“方志”始见于春秋时期《周官》,到西汉魏晋时已成雏形,隋唐已出现官修志书,宋元时期体例已大致定型,明清为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参见林衍经著:《方志学著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由此可见,方志的演变过程始终与历史发展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再具体一些说,汉魏六朝时期的早期“方志”形态为“地记”,本身数量不少,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现也仅存《襄阳耆旧记》中的人物部分了。隋唐纂修方志已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并有了一系列相关的章程制定和颁布实施,所以此时期为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四川地域来看,三国时蜀汉儒学大师和史学家谯周(巴西郡西充人,其当时县治在今阆中市天宫乡宝珠村),官至光禄大夫、散骑常侍等,编纂过《益州志》《兰白记》《巴蜀异物志》《三巴记》等;晋代常璩(今崇州市三江镇人)又撰写了我国现存最早以“志”为名的《华阳国志》,被通认为也是最早的四川通志;西晋史学家陈寿(巴西郡安汉县——今南充顺庆人,曾师承谯周)不仅著有《三国志》,而且还撰成《古国志》《益都耆旧传》(后者即为有关古代四川人物专志)。再从民间藏书情况来看,阆中远在“宋元中祐,雍子仪家于阆州将相坊建会经楼。贮经史子集三万余卷”(载《舆地记胜》)、“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建敕书楼”。加之这一时期没有连绵不绝的战争、瘟疫、天灾等,因此,估计至迟到宋朝,阆中应该有方志的雏形出现。
此后由于历史变迁朝代更替、战争绵延灾祸不断,特别是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阆中作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屡遭兵戈扰攘和铁蹄蹂躏,能有明嘉靖版的府志传世(虽不是当地保存下来),已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笔者曾看过中国民间最大的藏书楼宁波“天一阁”出版过一本《历代散失珍本孤本书籍目录》,其中有《保宁府志》 1~13卷,可惜未能明确是何版本,但据“天一阁”创始人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1506年-1585年)活动时间推算,该阁收藏后又遗失的有可能即为明嘉靖版本《保宁府志》。当时的天一阁藏书楼,仅明代各省府州县志书就多达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辑录的还要多。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尤重方志。
近代阆中地方文献损失最为惨重的至少还有两次:一次是在1941年7月27日至8月31日,日军先后四次出动90多架次飞机对古城进行狂轰滥炸,其中8月29日中午,当时“县政府设在天马寺街的疏散(临时)办公室遭受敌机轰炸,档案资料全部被毁”(见《四川抗战档案研究》,李仕根主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当时具体炸毁了哪些档案资料,迄今未见有人回忆疏理。另一次是在1946年5月15日凌晨,当时的县政府办公室被人为纵火,将财政科、教育科、社会科、军事科及优委会的文书档案悉数焚毁。十年动乱中,虽未发生直接对地方文献集中毁损的事件,但相关史料的灭失也是不容低估的,如据城东近30公里的金城山金城寺,历代颇负盛名,有世代相传《金城寺志》,当年红卫兵从11代主持释兴荣家搜出后即被烧毁。如此等等,致使近代许多珍贵史料毁佚无存,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虽很厚重但却模糊不清,甚至扑朔迷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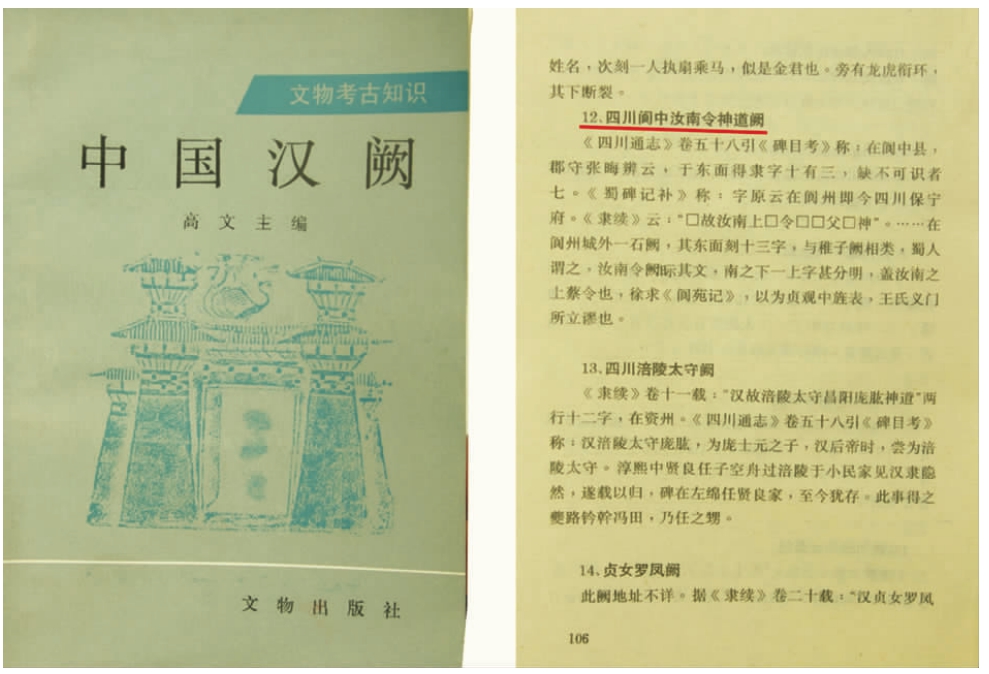
早已失忆的阆中汉阙
回溯阆中历代方志,从纵向看“源头”模糊,横向看“府县”残缺,加之历代区划隶属调整频繁、灾祸战事不断等诸多原因,致使脉络粗犷,诸多史事语焉不详。如从战国自南宋这一阶段姑且不论,从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到民国2年(1913年),其间长达630多年均为保宁府所治,有多少“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史马迁语)的大事,有多少名宦良吏信史业绩,有多少珍贵的数据资料,现在都不知所云。历代纂修方志都特别注重“补史之阙、续史之无”“旧志续修、旧志正误”“志详史略、志近史远”等,后人则一概重新编,轻纂修,这大概也是当代方志工作中的通病所在。
仅以当代人物情况为例,解放后的第一部县志(含以后的文献资料)记载了诞生过的九位红色将军,而唯独缺少“国军将领”的史料,这不仅不符合有此就有彼、有矛必有盾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也不符合修志需遵循“详今略古”“志属信史”等基本原则,其以论代史的痕迹随处可见。据笔者所知,本籍人物中的国民党将军要员至少有侍卫室副侍卫长、军统元老之一、陪都重庆警察局局长陈善周;国防部次长雷开煊,黄埔军校毕业的将官范龙襄、李元之;抗日将领第22集团军370旅副旅长汪潮濂等都可以写上一笔的。否则,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那天,人们只能叹息当年的历史记录者太短视和狭隘了。又如,志书从来就强调“存史资治”“经世致用”的功能,但翻开历代方志,几乎全是“盛事”而无“憾事”,对各时期的决策失误和重大教训除归责到大环境外,几乎未触及值得总结借鉴的任何事例,讳言禁忌太多就难免因“失真”而以讹传讹。古人有“隐恶扬善”的习俗,而今倡导“实事求是”,但对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事连“述而不作”的春秋笔法也很难看得见。还有,从前的民族工商业记忆、当今的工业遗产保护,这些都是阆中地域中最具个性化、最重要的历史特征,如果说过去着墨不多是囿于“左”的缘由和认知水平,现在再留下遗憾就难以对历史作出交代了。
行文至此,欣闻西华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不久将着手点校《保宁府志》(嘉靖本),这不仅对院校文史学科建设有重大科研和学术价值,而且也将极大地推动地方挖掘、重视、利用、传存文献资料并服务于现实社会,使之真正成为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和无法估量的人文资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