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和存在之间具有一种差异(Differenz)。这一差异使得超离日常所忙碌的现成之物成为可能。我们与他人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不是物。而且,世界敞开了我与他人以及我与物之间的自由空间,一个从来不能对象化的自由空间。尽管差异在欧洲哲学传统中被视为需要严肃对待的现象,但主要是同一的确立(A=A)被断定为思想的最终目标。相反,海德格尔阐述道,不是同一或者总体,而是差异乃是自由的开端,这样他便离开了这一传统,并首先给予伦理学以新的启发。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海德格尔思想中三个最关键的基本概念。海德格尔的思想围绕着“存在”、“存在者”以及——作为一种“卓异的存在者”的——“此在”这些概念。显然,它们共属一体,构成一个统一体,但同时也显示出区别。“存在”不是“存在者”。海德格尔将这种区别称为“存在学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这一区别构成了其哲学真正的基本结构。在接下来的评述里我将致力于探讨这一对其思想至关重要的结构。因为下面的评述看起来围绕的是一种单纯的思想形式(Denkform),所以不时会让读者略感头痛。但对这一首要的也是最终的差异的考量无法回避,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一差异支撑着整个欧洲思想。
海德格尔在马堡的讲授课“现象学之基本问题”,“哲学导论”以及他的论文“论根据的本质”传达了他关于“存在学差异”,即“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的最初辨析。在1927年的马堡讲授课上有这样的话:
存在一般与存在者之区别的问题并非毫无理由地处于首位。因为对这一区别的探究会首先明确地并且方法上可靠地使得如下做法成为可能,即将不同于存在者的存在视为主题并加以研究。存在学,亦即作为科学的哲学的可能性依赖于足够清晰地贯彻这种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别的可能性,以及随后实行一种跨越——从对存在者加以存在者层次(ontisch)的考察向在存在学层次上(ontologisch)以存在为主题跨越——的可能性。(全集卷24,第322页)(67)
“存在之意义”问题不将任何“存在者”纳入视线。不过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曾断言,为了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对一种“典范性的存在者”的分析开始。但若那样,从对“存在者”的分析到真正地“在存在学层次上以存在为主题”的“跨越”怎么发生呢?作为“存在学”的哲学不是单单关于“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关涉到“存在”的“存在者”的科学。通过这一区分,海德格尔似乎要改造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próte philosophía)思想。第一哲学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乃是诸科学的科学,因为正如他在其《形而上学》讲稿(1025b,1)中阐述的,第一哲学不单单研究感性“存在者”,而且研究其原理和原因(haì archaì kaì tà aítia)。
按照《存在与时间》在方法上的设定,如此这般的存在学以探究一种特定的“存在者”亦即“此在”为起始。《存在与时间》所强调的此在的“存在方式”扎根于“时间性”(Zeitlichkeit)之中,所以辨析“存在学差异”问题的第一步在于对“此在”特别的“存在方式”,即“时间性”或者说“时间状态”(Temporalität)(全集卷24,第402页)(68)进行考察。
对海德格尔而言,在阐明关系到“此在”的“时间性”时显示出这样一种必要性,即探究“认识存在者以及领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同前,第402页)(69)。在进行这番探究时,他引用了柏拉图在《政制》(Politeia)(70)第六卷中的日喻说。日喻说表明了“从对存在者加以存在者层次的考察向在存在学层次上以存在为主题跨越”触及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善(das Gute)尚要超越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处于“存在之彼岸”。所以海德格尔可以说:“我们所寻找的是epékeina tês ousías(71)。”(同前,第404页)(72)回到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对阐明“存在学差异”而言甚为重要。保罗·那托普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柏拉图的理念说》中将关于“存在之彼岸”——依海德格尔则称作“存在者之彼岸”——领域的思想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概念”(73)联结起来,这在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学差异”的思考中留下了痕迹。我以为,马堡时期的海德格尔相信,通过对柏拉图和康德的辨析能够完成对作为“存在学”的哲学的奠基,这并非偶然,而是受到那托普著作的影响。
使得“此在”不仅仅理解“存在者”而且理解不存在的“存在自身”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乃是有一个超越“存在者”,并首先在“存在者之彼岸”敞开自身的领域。海德格尔会将这样一种“存在者之彼岸”的“存在”领域,称为“世界”。在马堡时期的另一门讲授课“哲学导论”上,海德格尔解释了“存在问题”在什么意义上与世界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全集卷27,第394页)。如同“此在”“总是”处于“一种存在领会(Seinsverständnis)之中”(全集卷24,第420、421页)(74),“此在”也总是具有“对世界、对意蕴的一种先行领会”“此在”游弋于一个超脱了现成“存在者”的运作空间(Spielraum),这一理解本身是“超越(Transzendenz)真正的存在学意义”(同前,第425页)(75)。这意味着,“在世界之中存在”之中的“此在”能够超出自身,“超逾”(übersteigen)(全集卷9,第137页)(76)仅仅现成之物。
况且柏拉图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显示出与“存在学差异”思想的一种结构性类比。最先在对话录《斐多》中成为主题的概念chorismós(77)(斯特方本67d),表明了灵魂与身体的分离和区别,灵魂与一个显然会朽坏的身体相联系,而这一概念使得断言非肉身性的灵魂的不朽成为可能。“存在学差异”这一概念仿佛是柏拉图理念存在学(Ideenontologie)中的这一基本差异的一个回音。chorismós,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epékeina tês ousías,是“超越”的一个条件。通过超越敞开了一个空间,此在能够“超离”现成“存在者”,将其抛诸身后,进入这个空间。
海德格尔想要明确地理解这种被思考为“超越”的东西,他的理解同时从康德出发又一反康德对“先验”(Transzendentale)的规定。康德在“先验”概念中“认识到的正是一般存在学的内在可能性问题”,不过康德所采用的“先验”概念“根本上的”“批判性”含义阻止了他“以一种对超越之本质的更彻底和更普遍的把握”来为“存在学以及形而上学之观念的更为原初的制订”(全集卷9,第139页)(78)奠定基础。在此没有必要进一步阐明海德格尔如何解读康德,要明确的仅仅是,在“存在学差异”的含义第一次形成时,海德格尔与柏拉图和康德这两位思想家进行了争辩。
“存在学差异”的第一个规定,亦即其所有进一步变化的出发点已然明确。海德格尔在“论根据的本质”中颇具指引意义地写道:“存在学差异的这一根据,我们……称之为此在的超越。”(同前,第135页)(79)“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敞开了“存在之彼岸”的领域——世界的维度或者说“此在”的超越。
海德格尔对“存在学差异”的澄清在当代具有一种认识论的功能。他如此感兴趣于为作为一种“关于存在的绝对科学”(全集卷24,第15页)(80)或者一种“普遍的存在学”(同前,第16页)(81)的哲学奠基。这一“绝对科学”即“先验的科学”(同前,第460页),因为它的对象是世界或者说作为“此在”之敞开状态的“存在”,即超越。而这种科学的方法应该是现象学(同前,第27页以下)(82)。
将“绝对科学”规定为现象学或者反过来将现象学规定为“绝对科学”对于20年代末期的海德格尔哲学来说毋庸解释。在这一规定中道出的是从亚里士多德的theoría(83)直到黑格尔的“绝对科学”所传承下来的哲学之自我理解。在《存在与时间》中“基础存在学”就已经被思考为对所有关于“存在者”之科学的奠基(全集卷2,第14页)(84)。然而,处于海德格尔思想这一位置的一种科学的哲学计划显得有多么明确,也就会多么明确地认识到如下问题:这一计划的危机会被什么所引发。这个问题隐藏在作为存在学的“绝对科学”的特性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其对象之中。海德格尔将“存在”视作这一“绝对科学”的对象。“存在”能够被弄成这样一种科学的对象吗?
创立一种“关于存在的绝对科学”是成问题的,因为“存在”如何存在的方式具有“隐逸”(Entzug)或者“遮蔽”(Verbergung)的特性。1923年海德格尔已经注意到:“以自我—隐藏(Sich-verdecken)和自我—遮掩(Sich-verschleiern)的方式去存在属于作为哲学之对象的存在的存在特性(Seinscharakter des Seins),并且这种存在方式绝非无关紧要,而是依据存在的存在特性,这一点一旦凸显出来,就得真正严肃地对待现象范畴了。”(全集卷63,第76页)海德格尔强调,“现象范畴”,即自在的显现,在一种“自我—隐藏”,一种不显现(Nichter-scheinen)发生的地方才变成一个哲学问题。这个思想是一个悖论,它再次转向了《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在那里写道,现象是某种“恰恰首先并通常不显示自身的东西,与首先并通常显示自身的东西相对,是某种被隐蔽的东西”(全集卷2,第47页)(85)。显现时的这种“遮蔽”,这种“自我—遮掩”,察觉这种现象是现象学的根本任务。如果超越是作为现象学的“先验科学”的对象,那么这个对象——一种非对象(Nicht-Gegenstand)——就是一种非现象(Nicht-Phänomen)。
现象中的这种隐藏(Verdeckung),存在的“自我—遮掩”是“存在学差异”的主要标志。“存在学差异”如何分开或者区别现身的“存在者”和自我遮掩的“存在”,它就如何把现身(Vorliegen)和隐藏整合为一个统一体。显现与隐藏在“存在学差异”的中心构成某种张力,20年代末,当海德格尔将差异作为超越来思考时,他就想让上述事实成为一种“普遍存在学”的对象。但恰恰是“存在学差异”,会将创立作为“关于存在的绝对科学”的现象学的可能从内部给摧毁掉。
“存在学差异”即区分两个思考空间的差异,一是关涉“存在者”的“存在者层次的”思考空间,一是关涉“存在自身”的“存在学层次的”思考空间,后者因为关涉“存在自身”才真正成为哲学的思考空间。通过探究“存在学差异”而迈向“先验科学”之奠基的步伐对处于其哲学思考之根本变革中的海德格尔而言,显得是一个必要的错误。这个错误可以被追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存在学差异”与海德格尔哲学摆脱这个失误之后的进一步变化可以被诠解为“形而上学之克服”。创立“关于存在的绝对科学”的尝试必然被证实是一种冒失,因为它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存在本身”的规定,即存在不是可被客体化的“存在者”。
《存在与时间》最后的段落已经触及到一种观点,这个观点激发了“此在之超越”的“存在学差异”这一基本的思想调整。在那里海德格尔谈到“演历之动变(Bewegtheit)的存在学谜团”(同前,第514页)(86),谈到“历史”的“存在学谜团”。历史之“动变”的神秘促使海德格尔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解的基础上重新反复思考“存在学”的奠基。在这里他产生了如下怀疑,即这一哲学理解能否与他思想的真正意图相契合。这个怀疑促使他表达出一种争取克服西方的哲学理解——作为关于第一因的科学,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理解——的思想。由“形而上学之克服”(参见第三章第三节)这一论题域出发,“存在学差异”的显著变化将得到阐明。不过,上述事实的特殊意义恰又造成如下情况:“形而上学之克服”规定了还有待解释的“对存在学差异之克服”,还是相反,这仍旧悬而未决。
“形而上学之克服”这一独一无二的尝试,亦即尝试将西方思想的整个历史引领向一条崭新的、不同的路途。将这种尝试付诸语言的两份伟大且意蕴深远的证明即《哲学论稿》(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及紧接而来的《沉思》(Besinnung)(87)中的探索。《哲学论稿》中以自我批判的方式涉及到“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这一区分从《存在与时间》开始被把握为‘存在学差异’,并且是出于这样的意图,即确保存有(Seyn)之真理问题免于各种混淆。但这一区分立刻被推回它所源出的原位。因为在这里存在状态(Seiendheit)让自己作为‘ousía, idéa’(88)发挥效用,紧接着使对象性作为对象之可能性的条件来生效。”(全集卷65,第250页)如今,海德格尔在思考“存在学差异的起源本身,也就是其真正的统一”(同前,第250页)的领域,对作为“此在之超越”的“存在学差异”的清理还没有达到这个领域。固执于“存在之存在状态”,固执于“所有存在者之共相”(同前,第425页)的表象始终错置了“存在本身”(现在海德格尔称之为“存有”)。海德格尔第一次试图澄清“存在学差异”时,一方面以柏拉图关于epékeina tês ousías的思想为导向,另一方面则是康德的“先验”理论,那时,他的思想要前往的地方,即“存在学差异”的起源——海德格尔现在将其描述为“存有之本质现身”(Wesung des Seyns)(89)(同前,第465页)——就从他那里隐逸而去。
柏拉图和康德的思想错置了“存在学差异”的“起源”或者说“真正的统一”,所以现在海德格尔拒绝它们,在澄清自己的哲学意图时,他切入到更早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时期。他指出,欧洲哲学的这些奠基者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患有一种奇特的“遗忘”。欧洲哲学已经不再能够将存在作为它本身而非作为一种特别的“存在者”来理解。这种“遗忘”并非归咎于哲学家的失忆症,而可能缘于自我隐逸、自我遮蔽的存在,这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思想之一。
这样的解说可能造成如下印象:随着存在学基础主义(Fundamentlismus)的发展,海德格尔现在想要干脆地用一种“纯粹”的形式恢复这一“差异”。其实当海德格尔思索“存在学差异”的“起源”时,他仅仅修改了“存在学差异”的结构。这绝不是说将区分的两方面,“存在”和“存在者”,“纯粹”地分离开来。“存有之本质现身”作为差异的“起源”是那种位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东西(全集卷9,第123页)(90)。这关系到对某种第三者的认识,至今还完全未被注意。对“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的考察既无关“存在”也无关“存在者”,而是关乎居于两者“之间”的领域。
通过对这一“之间”(Zwischen)的发现,海德格尔到达了一个维度,在这个维度常见的存在学阐释范畴几乎不够用了。因此哲学家直接谈论起一种“作为差异之差异”(Differenz als Differenz)(91)。这种差异是“形而上学本质之建构的基本框架(Grundriss)”,但它无法作为差异本身由形而上学来思考。随着对这一“基本框架”的揭示,“形而上学之克服”找到了它的主导性思想。
为了完全理解“作为差异之差异”思想的确切含义,我们必须更准确地考察“基本框架”一词。一方面,海德格尔想要根据他关于“存在学差异”的解释——如我们所见,最初他可以将“存在学差异”与柏拉图和康德的思想联系起来——指出,在欧洲哲学史上,“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为超感性之物与感性之物的区分提供了“基本框架”。因为有“存在学差异”,在哲学史上才可能,比如说,区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不过“基本框架”一词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说“更字面的”含义。我们必然作为“此在”在“存在”之“根基”(Grund)上生存,这一根基被赋予一种裂隙(Riss)的特征——或者说“根基”即“裂隙”。(92)凭借“作为差异之差异”的思想,海德格尔想要指出,有一种不可统一的“差异”一般,这一点多么出乎寻常。这种“差异”不能再归属于“同一”——欧洲哲学的传统一直如此尝试——而是只要有存在者,它就在人的一切所做所思中起作用。如果想要让“裂隙”消失在“根基”之中,就必须否认整个哲学史上的“基本框架”。
这似乎只是个语言游戏,但对当代思想意义深远。在“作为差异之差异”这种假设的单纯形式性的思想中特别蕴含着一种伦理学上的潜在意义,即便一开始不容易认识到这一点。雅克·德里达在其1972年的演讲“延异”中已经注意到,思考“存在学差异”,这一由海德格尔提出的艰巨任务,遗憾地“几乎依旧没被听进去”。(93)五年前他在“暴力与形而上学”一文中针对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指出,在什么意义上没有“存在学差异”和“存在之思”就不可能发现任何伦理学,更别说列维纳斯意义上的伦理学。(94)德里达批判地强调说,“存在学差异”与相对他者的“差异”相比是一种“更原初的差异”。(95)“作为差异之差异”被思为“根本裂隙”(Grundriss),使他者相互分离又聚集在一起。
如果回顾一下近十年来的哲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海德格尔将“存在学差异”作为主题,最后又将其发展为“作为差异之差异”的思想,它们首先在(广义上的)法国现象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间尤其激发了伦理学方面的思考。不同于自柏拉图以降的欧洲哲学传统,这样一种“差异”思想的伦理学意义在于,“差异”在与“同一”的关系中不能再被理解为亏缺的(defizitär)。古典欧洲哲学一直把他者(Anderen)和他样(Andersartigen)现象理解为某种在最初和最后的“同一”中,在将一切整一化的“总体性”(Totalität)中必须被克服的东西。可以看到,这一洞见不仅仅在德里达和列维纳斯的思想中留下了印记。接受海德格尔“差异”思想的另一个例子是受弗洛伊德的法国学生拉康影响的露茜·伊莉盖瑞(Luce Irigaray)所写的《性别差异伦理学》(96),她也在寻找自己的研究与海德格尔差异思想的相近之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97)的多元式“实用主义”也受到海德格尔影响。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愿意放弃理性之普遍效用要求的思想,比如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思想,就与海德格尔反对欧洲思想的普遍主义,解放“差异”的尝试扞格难置。
————————————————————
(1) Lebenszeit日常意为“一生,终身”,字面上由Leben(生活,生命)和Zeit(时间)组成,此处译法为了突出Zeit(时间)一词的含义。——译注
(2) 1916年海德格尔出版其教职论文,离1927年《存在与时间》发表共11年,中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参书后附录“海德格尔年表”。——译注
(3) 于尔根·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著作与世界观”(Heidegger-Werk und Weltanschauung),维克多·法里亚斯(Victor Farías)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前言,美茵法兰克福,1989年,第13页。(《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中译本可参见郑永慧译,时事出版社,2000年。——译注)
(4) 埃米尔·施泰格,“回顾”(Ein Rückblick),见Otto Pöggeler编,《今日海德格尔——解释其作品的多样视角》(Heidegger heute. Perspektiven zur Deutung seines Werks),科隆与柏林,1969年,第242页。
(5) 《存在与时间》中译文基本根据陈嘉映、王庆节先生的翻译,间或有改动,特别改动处有注明。此处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三联书店,2006年,第8页。——译注
(6) 此处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三联书店,2006年,第14页,原译文中“与”(um)一词的斜体未经标示。——译注
(7)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73页。——译注
(8) 《存在与时间》中译本译为“别具一格的”。——译注
(9)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0页。——译注
(10)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09页,译文略异,原译文中“多样性”(Vielfältigkeit)一词的斜体未经标示。——译注
(11) 同上,第271页。——译注
(12) 同上,第20页。——译注
(13)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494页,中译本译为“存在的视野”。——译注
(14) 同上,第132页,原译文中“谁”(wer)一词的斜体未经标示。这里作者给出的页码经查是《存在与时间》单行本页码,全集本页码为第152页。——译注
(15)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132页,译文略异。——译注
(16)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145页。——译注
(17) 同上,第140页。——译注
(18) macht sich keine Sorgen,意为不忧心、不担心,这里根据上下文试译为“杞人忧天”。——译注
(19) 这里是动名词做副词,表示一种状态。——译注
(20)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22页,译文略异,原译文中“操心”(Sorge)一词的斜体未经标示。“先行于自身已经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就是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原文为“Sich-vorweg-schon-sein-in-(der-Welt-)als Sein-bei(innerweltlich begegnendem Seienden)”。——译注
(21) 这里所称的概念、区分指的是后文所说的“人们”(Man)。——译注
(22)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148页。——译注
(23)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151页。——译注
(24) Man在日常德文中可作无人称主语使用,海德格尔将其大写作为一个重要的基本词语加以使用。《存在与时间》中译本译作“常人”,过于概念化,且已经表现出某种价值评判,不合海德格尔将之作为一个中性范畴使用的本意,也脱离了Man在日常德文中的含义,因而借鉴张祥龙先生的译法译作“人们”。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第103、104页。——译注
(25)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150页。——译注
(26)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13页。——译注
(27) 原文即后文的“沉沦态”,因为verfallen在日常德文中有陷入、沉迷、迷恋于的含义,在此处为了文句晓畅译作“迷恋”。——译注
(28)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15页。——译注
(29)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16页。——译注
(30) 同上,第216页。——译注
(31) 同上,第216页。——译注
(32) 此句原文为Das, wovor wir »Angst« haben, ist eigentlich »nichts«。“nichts”在日常德语中表示没什么,什么也不是,相当于英文的nothing,而在海德格尔思想中作为一个概念,即表示“无”。——译注
(33) 参见《存在与时间》(06年修订译本),第216页。此处没有采纳陈嘉映先生的译法将Nirgends译作“无何有之乡”,nirgends也是德语中一个日常词汇,做副词用,表示“不在任何地方”,为了与其副词含义保持一致,译作“一无所在”。——译注
(34) 彼得·汉克:《世界的重量——一段旅程(1975年12月至1977年3月)》[Das Gewicht der Welt. Ein Journal(November 1975-März 1977)],萨尔兹堡,1997年。
(35)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16页。——译注
(36)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17页。——译注
(37) 此处使用了短语sich um etw. ängstigen,意为“为某事担忧”,不过ängstigen与Angst同形,前者在sich um etw. ängstigen中意为担忧,后者为畏惧,中译难以体现两者之间的微妙联系。——译注
(38) 在德语中有vor etwas ängstigen和um etwas ängstigen,以及vor etwas fürchten和um etwas fürchten的用法,分别表示对……有所畏惧,为了……有所畏惧,对……害怕和为了……害怕。“所对”(Wovor)和“所为”(Worum)的差异便是基于介词um与vor的区别来谈。——译注
(39)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305页。——译注
(40)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94页。——译注
(41) 同上,第303页。——译注
(42) 同上,第348页以下。——译注
(43)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反对、祛除锁闭,后文有时也取《存在与时间》中译本译法译为“下了决心的”。——译注
(44)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83页以下。——译注
(45) 马科斯·舍勒:《晚期文集》(Späte schriften),Manfred S. Frings编,慕尼黑,1976年,第294页。
(46)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Gott, der Tod und die Zeit),Peter Engelmann编,维也纳,1996年,第22页。(可参见中译本,余中先译,三联书店,1997年。——译注)
(47) 原作引文为vorausspringend-befreiende Fürsorge,为vorspringend-befreiende Fürsorge之误。参见Heidegger, Sein und 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7, S164。——译注
(48)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142页。——译注
(49) 同上,第276页。——译注
(50)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494页。——译注
(51) 此处译名参见第三章第一节译注。——译注
(52)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3页。——译注
(53)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434页。——译注
(54) 同上,第436页。——译注
(55) 同上,第3页,译文略异。——译注
(56) 同上,第436页。——译注
(57) 同上,第434页。——译注
(58)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442页。——译注
(59) 同上,第443页。——译注
(60) 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分布在欧洲、北非和西亚一带。——译注
(61)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25页。——译注
(62) 指Geschichte des Seins(存在历史)中的Sein(存在)作为第二格使用,而这里既可以把Geschichte(历史)理解为主词,也可以把Sein(存在)理解为主词。——译注
(63) 参见维克多·法里亚斯首先是出于复仇心理而写下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美茵法兰克福,1989年。
(64) 汉娜·阿伦特/卡尔·雅斯贝尔斯:《1926年至1969年通信集》(Briefwechsel 1926-1969),Lotte Köhler与Hans Saner编,慕尼黑与苏黎世,1993年,第84页。
(65) 参见《存在与时间》(06年修订译本),第442页,译文略异。——译注
(66) 雅克·德里达:《海德格尔的沉默》(Heideggers Schweigen),载于Günther Neske与Emil Kettering编:《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Antwort. 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äch),弗林根,1988年,第160页以下。(可参见中译本,陈春文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译注)
(67) 《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引文正由译者翻译,待全部译出后,丁耘先生翻译的中译本出版。译者不惴简陋保留了自己的翻译,聊以丰富翻译的可能性。读者另可参见丁耘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此处参见第305页。以下均注明中译本的相应页码,以便读者查对。——译注
(68) 参见《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388页。该处原文并没有讨论时间性问题,引文页码可能有误。——译注
(69) 同上,第388页。——译注
(70) 译者采纳了友人程炜的译法,将柏拉图对话录Politeia译作《政制》。参见程炜:《〈读柏拉图〉译后记》收于斯勒扎克(Thomas A. Szlezák):《读柏拉图》(Platon lesen),程炜译,译林出版社待出版:“下来再看看柏拉图的代表作‘Politeia’,笔者取《政制》之名,而不取流行的《理想国》、《国家篇》、《共和国》或刘小枫先生的新译《王制》。《国家篇》与《共和国》之误差前人多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这里仅欲对《理想国》与《王制》二书名略加辩证,因其立意实近似,失误却也相同。从文本内部而言,柏拉图之“理想国”即为“王制”,此毫无疑义。二者之别不过在于前者之语今,以泰西政治哲学为背景;后者之语古,以我国传统经学为援。其误则有四:一、以一书(可能)之主题改一书之标题,不顾作者之原名。二、即使以主题审之,Politeia一书也难以“理想国”/“王制”概而论之,仅就政治层面而言,其卷七到卷九便涉及他种政治体制,其余偏离两名处多有,而毋需遍举。三、所谓“理想国”与“王制”据希腊文应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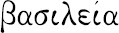 ,而非
,而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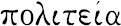 。仅据柏拉图原书的论述中,
。仅据柏拉图原书的论述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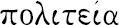 实包括王制
实包括王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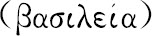 、贤人制
、贤人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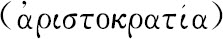 、荣誉制/斯巴达或克里特制
、荣誉制/斯巴达或克里特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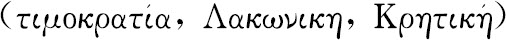 ,寡头制
,寡头制 ,民主制
,民主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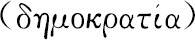 与僭主制
与僭主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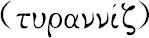 (544c以下,也参《政治家》291d以下,所举略有变化),其可谓政治制度之通名。四、据亚里士多德,
(544c以下,也参《政治家》291d以下,所举略有变化),其可谓政治制度之通名。四、据亚里士多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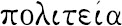 除通名用法,亦可谓与民主制相对好的多数统治(《政治学》1279a35以下,也参《尼各马可伦理学》1159b35以下,所解略异),或者某种结合寡头制与平民制好的混合政制(《政治学》1293b32—35, 1295a25—31等)。在
除通名用法,亦可谓与民主制相对好的多数统治(《政治学》1279a35以下,也参《尼各马可伦理学》1159b35以下,所解略异),或者某种结合寡头制与平民制好的混合政制(《政治学》1293b32—35, 1295a25—31等)。在 特殊用法中,中文常译为“共和制”。概而言之,如果其作为一种特殊政体,则或与贵族制或与民主制或与寡头制均有亲和处,却离一人君主制——无论是王制还是僭主——颇远。”在此感谢程炜君惠赠文稿。(翻译临近定稿时,程炜的译作已经出版,参见:《读柏拉图》,斯勒扎克著,程炜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译注
特殊用法中,中文常译为“共和制”。概而言之,如果其作为一种特殊政体,则或与贵族制或与民主制或与寡头制均有亲和处,却离一人君主制——无论是王制还是僭主——颇远。”在此感谢程炜君惠赠文稿。(翻译临近定稿时,程炜的译作已经出版,参见:《读柏拉图》,斯勒扎克著,程炜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译注
(71) 古希腊文,在存在另一边、超越存在。——译注
(72) 参见《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390页。——译注
(73) 保罗·那托普:《柏拉图的理念说:通向唯心论的一个导引》(Platons Ideenlehre. Eine Einführung in den Idealismus),汉堡,1994年,第463页。
(74) 参见《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405、406页。——译注
(75) 同上,第410页。——译注
(76) 参见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9页。——译注
(77) 古希腊文,分开,分离。——译注
(78) 《路标》所收文章翻译据孙周兴先生译本,间或有改动。此处参见《路标》,前揭,第162页,译文略异。海德格尔全集卷9,第140页的原文为“eine ursprünglichere Ausarbeitung der Idee der Ontologie und damit der Metaphysik”(一种对存在学以及形而上学之观念的更为原初的制订),而本书引文为“eine ursprünglichere Ausarbeitung der Ontologie und damit der Metaphysik”(一种对存在学以及形而上学的更为原初的制订),遗漏了原文中的Idee(观念)一词。——译注
(79) 参见《路标》,第156页。——译注
(80) 参见《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13页。——译注
(81) 同上,第14页。——译注
(82) 同上,第24页以下。——译注
(83) 古希腊文,理论。——译注
(84) 参见《存在与时间》(2006年修订译本),第12页。——译注
(85) 同上,第42页。——译注
(86) 参见《存在与时间》(06年修订译本),第440页。bewegt是动词bewegen(使运动,推动)的过去分词,字面上是被推动之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成熟形态的西方形而上学最终要考察一个第一推动者,即所有运动、所有存在者的第一因,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神。而海德格尔强调存在、历史自在的、无主动被动之分的发生性,并以此为着眼点试图克服形而上学。Bewegtheit在此便指称存在、历史的这种自在的发生状态。——译注
(87) 海德格尔的这两部作品,前者已由孙周兴翻译,尚未出版,后者据译者所知尚无中译。这两部作品尤其是前者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非常特殊,书名似也别有深意,难有定译。前者从孙周兴译法,后者暂译为“沉思”。——译注
(88) 古希腊文,实体,理念。——译注
(89) 海德格尔把传统哲学的Wesen(本质)一词作动词使用,用以表示“存有之真理的发生”(参见全集65卷,第287、288页),Wesung是作为动词使用的Wesen的名词化形式。——译注
(90) 参见《路标》,第142页。——译注
(91)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Identität und Differenz),弗林根,1957年,第37页。
(92) Grundriss在日常德语中是建筑蓝图、框架、构造、草图的意思,在字面上由Grund和Riss两词组成,前者意为根基、基础,后者意为裂缝、裂隙,这个词也随语境译为“根本裂隙”。——译注
(93) 雅克·德里达:“延异”(Die différance),见氏著:《哲学的边缘》(Randgänge der Philosophie),维也纳,1988年,第48页。
(94) 雅克·德里达:“暴力与形而上学”(Gewalt und Metaphysik),见氏著:《书写与差异》(Die Schrift und die Differenz),美茵法兰克福,1976年(巴黎,1967年),第208页。(可参见中译本,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译注)
(95) 同上,第138页。
(96) 露茜·伊莉盖瑞:《性别差异伦理学》(Ethik der sexuellen Differenz),美茵法兰克福,1984年。
(97) 参见理查德·罗蒂:“哈贝马斯、德里达与哲学的任务”(Habermas, Derrida und die Aufgaben der Philosophie),见氏著:《哲学与未来论文集》(Philosophie und die Zukunft. Essays),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第26页至第5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