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的闪光轨迹:村田幸子对“回儒”的解读与阐释
美国学术界对“回儒”的研究在近2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文明对话的时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推动和鼓励下,美国的一些学者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比较研究教授村田幸子,于2000年出版了《苏非之光的汉文折射》,在学术界获得了热烈反响和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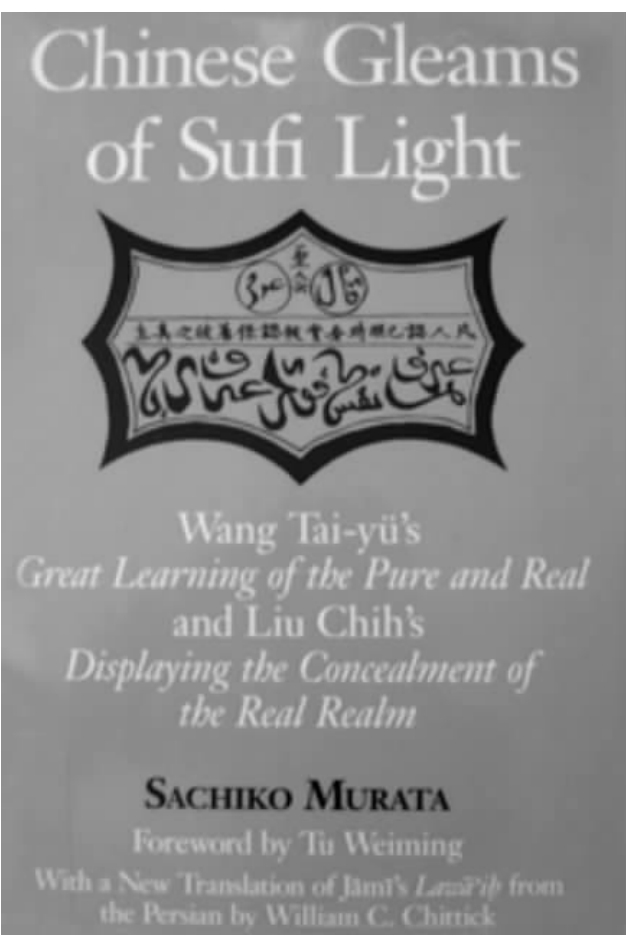
村田幸子著作封面
关于该书的缘起,作者作了一些背景性介绍。1992年,村田幸子出版了《伊斯兰之道》,当时她对中国伊斯兰的知识了解甚少。但她决定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当代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的指导下,开始阅读汉语文献,研究新儒学思想。而且在1994~1995年,她申请到了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奖学金,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宇宙论。但是1995年的一次国际会议改变了她的学术兴趣。1995年3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召开了“伊斯兰和儒家:文明的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思想史专家李焯然(Lee Cheuk Yin)教授,对她提供了一篇有关中国穆斯林第一位思想家王岱舆的论文。村田幸子教授在学术交谈中被深深吸引。后回到美国后,就立即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图书馆查找到有关王岱舆的著作,还有刘智等其他穆斯林汉文译著家的珍藏著作,从此她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的研究,并发表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
《苏非之光的汉文折射》(Murata,2000)全书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17~18世纪第一次出现穆斯林写的汉文著作,介绍了两个主要的中国穆斯林思想家,王岱舆和刘智,描述了穆斯林学者把伊斯兰教著作翻译成汉文的努力。第二部分详细介绍王岱舆的著述情况。第三部分描述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探讨它在中国和伊斯兰教学问中的地位。第四部分是王岱舆《清真大学》的英文翻译。第五部分解释加米的波斯文著作《勒瓦一合(Lawā’ih)》的重要性,描述刘智怎样把它翻译成汉文,题为《真境昭微》。第六部分由村田幸子的先生威廉姆·柴提克(W.C.Chittick)把加米的《勒瓦一合》从波斯文重新翻译成英文。第七部分是把刘智的《真境昭微》翻译成英文。该书第一次将“回儒”的哲学思想的根源上溯到伊斯兰文明的原典和古典哲学源头,主要是伊斯兰苏非主义思想的权威经典对中国“回儒”著述与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对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思想对“回儒”哲学思想的研究,以及两大文明的哲学思想的融会与合流,进行了比较详尽而具体的阐释。对我们从哲学思想的根源上理解“回儒”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可贵而独到的理论视角,对促进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比较研究,开展深层次、宽领域的文明对话,产生了积极的世界性影响。
关于本书,当代著名的儒家哲学思想研究专家、国际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进行了高屋建瓴式的评价和解析。他写道:“先知穆罕默德教导:‘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从修辞学意义上来说中国只是遥远的代名词,对广大穆斯林们来说,由于经济、政治或社会原因,中国是个遥不可及的国度。因此,伊斯兰教在唐代(618~907年)由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一代追随弟子传入中国,确实是一件举世瞩目的事件。”
然而,一直到17世纪初,特别是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在穆斯林相对封闭的宗教学术界,那种具有勃勃生气、思想深邃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才开始出现,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宗教学者通过创作高质量的汉文译著,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精神生活。为何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穆斯林学者才感到需要一种明确表达在他们自身所属的群体和主流社会之间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的范式,而且,这一范式是在儒家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下形成的?的确,这一领域引人入胜,成为历史学家、比较宗教学家和东方宗教哲学家神往的研究课题。近年来,这一领域又引起了伊斯兰教学者,特别是有关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在回答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探究是什么因素在这些穆斯林学者中间产生了这一创新想法,并最终真正表述了他们的哲学思考,还有他们是怎样回答这种理解的需要的?这种探究承担着共同一致的努力方向,就是去认识、理解、欣赏文化产品中的精髓,这些文化精髓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仍然是适用的。文献整理、文本分析、传记考证、思辨性研究和翻译都是接近初步阐释的必要步骤。村田幸子通过艰苦的考古学式的挖掘和专心致志的钻研,极大地开拓了这一研究领域,并积极使其推广到国际学术界。我特别荣幸和感谢,从一开始,我就和她的这一研究课题相联系,这是一段让人在知识上不断得到充实,在精神上不断得以升华的难忘经历。
相比较而言,中国穆斯林中的伊斯兰学者对新儒学的思想方式有着成熟的把握,他们从哲理角度解释新儒学所关心的核心内容:理解万物,提炼知识,检验真知,净化心灵,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达到教化穆斯林群体成员信仰的目的,他们通过共同的教义和自我思考来阐明伊斯兰思想的根本信条,这与其说是为了倡导宗教,不如说是在进行自我反省、互相学习。新儒家的价值系统蕴涵于他们理性的阐述中,并且是其不言而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儒学的道德规范构成中国穆斯林信念、义务和善行中极有价值的部分。但他们没有进行调和伊斯兰教义学适应新儒学范式的尝试,也没有更好地参照新儒学的框架以使他们的教义学概念迎合中国主流社会更多人的趣味。他们在新儒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氛围中处境艰难,以至于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文化”为穆斯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这将会造成误导,形成中国穆斯林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把新儒家和伊斯兰教经过简单整合而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的印象。实际上,第一代中国穆斯林思想家们正是在经过对形形色色的压倒性强势思想中,在哲学阐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王岱舆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特例,作为被广泛赞誉的第一代中国穆斯林思想家的代表,他至少撰写了三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并被认为是兼通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佛教)的学者,同时,他从伊斯兰教的视角,潜心于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他在同非穆斯林学者们进行广大范围内的对话和交流过程中所显示的丰富学识,使他赢得了“真回老人”的声誉。
然而,王岱舆并非出身于中国书香门第,他甚至从没受过正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出生于中亚穆斯林后裔的名门世家,并在青年时代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当时,社会上没有有关伊斯兰教教义的汉文文献,中国人不能阅读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更不能直接阅读神圣的伊斯兰教经典及其经注。王岱舆的伊斯兰教研究是建立在深入理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无法具体考证当王岱舆面对讲汉语的众多穆斯林时,他是如何在这一特定的象征意义的思想界范围内实施他的研究计划的。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证实他遇见过天主教传教士,即便他后来用“清真”一词同所命名的寺坊相联系,并与他同时代的瑞塞(Ricci)在南京的传教基地相比邻。
根据王岱舆的自传可以看出,他是从青少年时开始学习汉语的。显然,这是现实的需要,尤其当他同身处中国大社会的穆斯林同胞和学者讨论伊斯兰教丰富内涵时,需要具备和精通足够的语言学知识,这也似乎说明他经过不断地努力而成为一位在汉文化中熏陶出来的学者的真正价值。在瑞塞(Ricci)事例中没有看到被观察或理解到的工具理性;他人无法与王岱舆为创作他的著作向宗教界上层权威解释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相比,作为引导穆斯林生活的宗教阶层中怀有抱负的一员,他的追求真知和经历的富有信仰生活从未因他那富有说教的著作而得到评判,也未能明确地以此来评价他的伊斯兰教信条和原则。确实,他的家庭,他的老师,南京的穆斯林社会,中国的伊斯兰教,天主教的信仰在中国儒学界的广泛传播,佛教和道教的流行,民间传统的生机、活力,以及一些非宗教的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王岱舆的人生阅历产生过影响。
但是,毫无理由怀疑王岱舆对儒家学说的赞誉,而且把它作为提高自身修养的一部分,成为在儒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做一个优秀穆斯林要求日臻完美的必经之路。王岱舆凭借自身渊博的“个人知识”和经过研究新儒学道德的形而上学所获得的“内心体验”,能够明白无误地用汉语习语表达伊斯兰教思想的真谛,他在建构汉语伊斯兰教知识视野时的创造性对新儒家思想也是一种原创性的贡献。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并没有用儒家的术语来表述他的终极关怀。更确切地说,通过将他自己的超然的视野体现在本土化的知识中,他精微地描述了伊斯兰教的真知在儒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是能够被具体地加以认识的。他不是倡导独辟蹊径,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双向互动。他接受了儒家的人本主义学说,并作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来丰富生活于中国国际性大都市中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一员的日常生活经验。他对伊斯兰教哲学的广泛深入理解,并能不断扩大认识范围,如从一种新鲜的视角与那些富有思想的儒士、高僧、道长进行谈话和交流,增加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和视野。
在我们这个多元宗教的世界里,王岱舆作为中国穆斯林中的一员是易于归类为儒学出身的。从各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一角度看,在哈佛大学和吉隆坡召开的会议证明了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相互参照、交流的成果和相互真正真诚合作的确实可行性。当我们为21世纪的到来而从事这一项工作时,我们开始构想在北美和东南亚地区形成的这一具有创造力的综合体的发展态势。王岱舆单方面地奋斗有力地证实了这项工作能够做好。而且,他沿着一条富有系统性和责任感的道路,在付诸实践的具体过程中,将伊斯兰教研究的核心内容与儒家丰富的学说思想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如果没有对于他的伊斯兰教信仰和日常的宗教功课以及他在勤奋阅读、沉思冥想和写作中所获得的知识加以了解,就不能完全理解他拥有的坚定信仰和儒学智慧,更无法想象他能进行那样鼓舞人心的实践。《清真大学》是王岱舆一生钟爱的事业、努力奋斗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令人注目的是,王岱舆在17世纪中叶开创的各宗教之间对话在后来的新生代中继续发展壮大,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被桑田六郎(Kuwata Rokuro)、安慕陶和其他学者称为“回儒”(回教)的学者。这一进程在18世纪初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其中中国伊斯兰历史上最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刘智(1662~1730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化的伊斯兰教的复兴。在他的学术思想中,人主合一的思想尤其深奥。《五功释义》的主旨是刘智对认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显著特征的讲解。在《五功释义》中关于人类参与宇宙生成的宇宙人类学,构成了刘智一种将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融会贯通的新思想基础:
只有那些至诚至忠至真的人,才能完全认识自己的本性;
只有完全认识自己本性的人,才能完全认识人类的本性;
只有完全认识人类本性的人,才能完全认识万物的本性;
只有完全认识万物本性的人,才能参与天地万物化育的进程;
只有参与天地万物化育进程的人,才能与天地合一。
刘智对真主/人类、自然/命运、物质/功能的解释是完全儒化了的。但是,通过在苏非教义中建立话语,他展示了一种通过伊斯兰教学识来达到“完人”的学说思想,如果不把儒学中有关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方面的理性概念明智地、最大限度地转换成伊斯兰教的方式,他是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他的苏非思想显示出存在单一论、永恒论和宇宙均衡论的观念,并能够欣赏儒家所尊奉的有关上天和人类亲密关系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村田幸子教授开创性的探索,将艰深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加以阐释,拨云见雾,揭开了这一在宗教比较学研究领域中尘封已久的秘密,使苏非之光重现,为世人所了解。它对于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宗教、东亚思想和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具有重大启示,它也将儒学———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对话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从而使中国的宗教分类比传统三大宗教的划分更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同时,让人们了解伊斯兰教在传统中国的研究概况。
发轫并逐步形成于17世纪的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是中国穆斯林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也是对世界伊斯兰文明的一大贡献。因为自7世纪初伊斯兰文明传播开来,阿拉伯语、波斯语一直是伊斯兰文明的两大主要语言载体和交际语言。但是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家们,则以汉语为文化载体,书写、阐释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伊斯兰的教义、教法以及道德伦理思想,使更多的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能够通过汉语了解和认识伊斯兰的基本价值观、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和文化观等,然而他们的贡献从来没有引起世界伊斯兰学术界、文化界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所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正是这些汉文译著家,以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丰富了东方伊斯兰的思想和文化宝库,也证明了伊斯兰文明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中扎根、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具有的生命力,即高度朴素而统一的原则性和予人便利的灵活性,使伊斯兰文明能够在不同的地区、族群和地方性观念中生根、开花、结果。同时,汉文译著家们及其代表作,也深刻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性、包容性,能够将不同的文化包容吸纳,并且在中华文明的主流中实践“万物相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文化精神,使中国穆斯林的汉文译著家们在明清以来的文化建设中大放异彩,影响深远。
中国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伊斯兰教的一个支脉,历史的发展轨迹显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两大文明的源头和交汇:即以阿拉伯—波斯—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之源,以及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以儒释道互补融汇的中国文明之源,这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生存发展基础,也决定了伊斯兰文化能够不断获得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流的泉源和重要文明参照。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扎根并走过了1300多年的历史岁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伊斯兰的一个支流,在坚持和坚守伊斯兰教正统信仰原则前提下,始终是立足和面向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现实处境,来求得穆斯林在中国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和微观的充满多样性的地方性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生存与发展,并以此来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民情和文化观念的时代潮流中中国穆斯林的文化发展和建设道路,这是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穆斯林的历代先贤和有识之士乃至一般民众,都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并前进的历史轨迹。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在经堂教育的发育和传承过程中,培植出了后来居上、兼通中阿的汉文译著家群体,在挖掘、阐释和发扬伊斯兰文化积极而整体的价值方面,筚路蓝缕,不遗余力。特别是他们在谙熟伊斯兰教原典精要的基础上,第一次开展了群体性的,以汉语为文本书面语载体,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释道融会互补的宋明理学的中兴,以及晚明以来的王阳明的“心学”的倡导,并将儒学、道家、佛教的一些哲学思想和文化术语,拿来为我所用,结合伊斯兰的认主学、宇宙论、认识论、价值观的深刻内涵,用汉语话语(Chinese Discourse)把以正统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记载的伊斯兰经典的微言大义表达出来、书写出来、阐释出来,并记载下来得以流传至今。这是一种中国穆斯林特有的将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和尝试,也是中国穆斯林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正如当代著名的新儒学大家杜维明先生所言:“这个现象(汉文译著)给一些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哲学而对中国没有太多认识的学者带来非常大的震吓。因为国际伊斯兰学的大师大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伊斯兰神学的发展在19世纪之前只有用阿拉伯文或者与阿拉伯文较相近的波斯文来表述,没有其他的可能。而17世纪的王岱舆和18世纪的刘智、马德新则是用古代汉语,通过儒家哲学的理念把伊斯兰教的经义展述出来。我个人认为,从儒家的立场上看是绝对成功的,但在伊斯兰神学上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考虑的疑问”(杜维明,2003:34)。总体看来,以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的译著文本,作为中国穆斯林探索中国文化和汉语语境下对伊斯兰教博大精深的内涵进行表述、开展文明对话的精神资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适合中国穆斯林学习和了解伊斯兰文化的需要,也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文人士大夫阶层和一般读书人的理解水平和思维方式。这种探索道路反映了中国穆斯林具有文化自我继承与综合创新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对时代发展的积极应对能力,尽管这项思想文化工程的努力尝试时至今日,有见仁见智的评说,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尝试、探索和践行对今天的我们,都会是一种经验的启发和教训的借鉴。
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的汉文译著家群体流传下来的文本资源中,明末清初的刘智(1660~约1730年,字介廉,号一斋)可以说是伊斯兰文化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进行融会和文明对话的集大成者。从刘智等代表人物的译著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基本的几个特点:其一,他们大都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以《古兰经》《圣训》为中心的经典要义的学习和训练;其二,对中国的诸子百家、儒学传统、宋明理学的时代主流思想和文化传承有比较具体而深入的把握;其三,汉文译著家们的伊斯兰哲学思想中,在拥有对伊斯兰经典的敬畏的理解和原则的守护前提下,大量吸收了伊斯兰哲学思想中苏非派的主要学说和思想,特别是自14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伊朗伊斯兰苏非派哲学家、思想家的深刻影响;其四,汉文译著家们的文本作品,代表了当时穆斯林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群体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水平、探索路径、心路历程和表达方式,他们对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的本土和中国的大文化环境下,进行固本融通的文化发展和振兴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参照。
在刘智的作品中,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思想的痕迹非常明显,其影响非常深远,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天方性理》《真境昭微》《天方三字经》等作品。而从《天方性理》到《真境昭微》中,始终贯穿着伊斯兰教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苏非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伊本·阿拉比和其继承者贾米等思想家、实践家的苏非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刘智在借鉴和吸收过程中,在对阿拉比和贾米的著作进行解读、翻译和表述过程中,却用中国的汉语的语言的思维方式、中国宋明理学的传统哲学思想的内涵、概念和术语来进行转换,在忠实原著原义的基础上,又用中国的哲学概念和术语进行适应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思维观念的汉语方式来表达和呈现,这是刘智的最大贡献,也是在继承传统、融通传统、会通中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勇敢探索和文化表述,还有他能出入百家、躬身践行的心灵体验,以及读尽万卷书、游学万里路的胸怀壮志和穆斯林学者的人文情怀。

刘智的《真境昭微》
《真境昭微》是刘智对伊斯兰教哲学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阿布德·热哈曼·贾米(Abd al-Rahman Jami,817~898/1414~1492)的《勒瓦一合》(Lawa’ih)的译介。刘智在《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中的采辑书目中列出了阿拉伯语音译名“勒瓦一合”,而对应的汉语意译名为“昭微经”。此外,刘智还列举出了贾米的另一部著作《额史尔》(Ashi’at allama’at),汉语意译名为《费隐经》(今有[波斯]贾米著、软斌译、康有玺校:《光辉的射线———艾施阿特·拉姆阿特》,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刘智在《天方性理》中曾经择译引用了《额史尔》中的9段论述,来对伊斯兰教的认主“独一论”、苏非的心灵和超理性体验与儒家的宇宙观、天人观进行比照和相互吸纳,以彰显伊斯兰哲学中对绝对存在的理性思考和把握。而《真境昭微》一书,则按照原著的顺序体例,刘智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和提炼加工。 《真境昭微》的汉译本由刘智完成,该书“卷末有乾隆乙未年(公元1775年)所作之序,最早刻板问世时间不详,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北京清真书报社将其再版重印,全书约6000字”(余振贵、杨怀中,1993:83)。贾米的《勒瓦一合》(Lawa’ih)作为15世纪伊朗伊斯兰哲学史上苏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对后来东西方的哲学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贾米的《勒瓦一合》及其他作品也被翻译到西方。如1906年由威费尔德(E.H.Whinfield)和米尔扎·穆罕默德·卡扎威尼(Mirza Muhammad Kazvini)合译了《勒瓦一合》的英译本,该版本被再版重印了好几次,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1982年彦安·瑞查德(Yann Richard)翻译出版了《勒瓦一合》的法文版,而这些版本比中国的刘智译本晚了将近300年,而且每个翻译者在忠实原著的同时,其译本又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译者自身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背景的烙印。
《真境昭微》全书共分三十六章,每章有一百字到几百字不等。第一章至第十二章,主要阐述认识独一真主的重要性,并说明求道修道的意义;第十三章至第三十六章主要说明“真理隐著之义”。该书的宗旨是:“《真境昭微》一书,系天方大贤查密氏所著,盖言其境,无境不真;言其真,无真不微;而究其微,又无微未昭。要之唯真也,故能微,唯微也。为能昭,亦唯实体乎真境也,方能满乎真之微,而昭乎微之微。余玩书,总计三十六章,前十二章,言求道体道之功,后二十四章,明真理隐著之义。”(刘智,1925)刘智对贾米的《勒瓦一合》的译介中,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润色和加工。在译介的过程中,他完全采纳了宋明理学的许多哲学概念,比较恰当地表达了贾米原著中伊斯兰哲学和苏非哲学的真谛,并将伊斯兰哲学与宋明理学的哲学理念在二者的比较、鉴别中,进行融通和互补,将伊斯兰深奥的哲学理念,特别是苏非主义的直觉体验绝对存在和修炼真道的内涵和方式,用汉语的学术术语加以表达。在这方面,刘智的努力和尝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如他把贾米的《勒瓦一合》的三十六章内容都加以标题,而且在贾米的原著中是没有这些标题的,只是每章冠以“xx Gleams”(隐现之光)字样,但刘智的《真境昭微》却别出心裁,将三十六章每一章冠以精当的题目:如第一章“一心”;第二章“聚分”;第三章“见道”;第四章“变灭”;第五章“全美”;第六章“研究”;第七章“蕴积”;第八章“克己”;第九章“克克”;第十章“归一”;第十一章“提觉”;第十二章“慎守”;第十三章“真有”;第十四章“有”;第十五章“体用”;第十六章“名拟”;第十七章“化原”;第十八章“统序”;第十九章“妙蕴”;第二十章“更变”;第二十一章“通碍”(上);第二十二章“通碍”(下);第二十三章“理象”;第二十四章“名分”;第二十五章“真品”;第二十六章“实物”;第二十七章“世界”;第二十八章“象拟”;第二十九章“显”;第三十章“理”;第三十一章“能为”;第三十二章“善恶”;第三十三章“知能”;第三十四章“实物合”;第三十五章“体用合”;第三十六章“辨义”。刘智在对原著的理解上,将每一章的大义进行高度概括,然后以意蕴之词命名。这些命名词语的过程,更为重要的凸现了刘智运用心智的创造性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对原著在汉语语境中的“再创作”。刘智在考虑、仔细推敲过程中,运用当时占时代主流的儒家宋明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和哲学概念来进行对应转换,同时也折射出刘智除了对主流思想的把握之外,还对道教、佛教等其他宗教有相当的理解和认识,而且还包括刘智的求学背景、人生阅历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刘智的译著中,都深层地反映着他的这种综合的创造性心智过程和精神探险之旅。
《勒瓦一合》作为贾米的代表作之一,是对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神秘体验和理论实践的记述,是探讨如何认识“独一”的真主,如何求得苏非主义的正道并进行修炼的韵文体著作。贾米的《勒瓦一合》和《光辉的射线》自从流传到中国以后,被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作为“受论的经典”,而加以研习和讲解。特别是在西北地区,贾米的这两部著作对穆斯林学习和理解苏非主义思想、实践和体验苏非主义的精神内涵,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贾米的《勒瓦一合》原著是诗歌体和韵文体的混合文本,引经据典,论述缜密而文风活泼,才情横溢,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心灵体验的独特表现,可以说,该书是贾米以苏非主义思想和修行的代言者(“Speaker”)的总结之作,正如贾米在序言《隐秘的祈祷者》中说:“这部命名为《隐现之光》的著作是关于神智论科学‘gnostic science’和意义的阐释。”(Sachiko Murata,2000:134)。但刘智在翻译过程中,却将原著中每一章中都出现的四行诗(波斯语为ruba’iyat,即“鲁巴亚提”,英文为quatrain)省略掉,按原著来看,是一种“去文学化”的、理性的、哲学文体的翻译,而更侧重于对原著的哲学内涵和形而上学的意义指归的汉语翻译、推敲和恰当的阐释。这正是刘智在翻译过程中,能够既忠实原著,又超越原著的创造性翻译的价值之所在。
阿布德·热哈曼·贾米的(Abd al-Rahman Jami,817~898/1414~1492),是15世纪伊朗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一生创作了超过55部之多的著作,而且研究兴趣和涉及面极为广泛。诸如阿拉伯语语法、波斯语语法、先知穆圣的生平、伊斯兰哲学等,特别是对苏非理论和实践、音乐及文学的关系方面,有独到而深刻的探讨、研究和记述。贾米的《纳法哈特·阿伦斯》(即“隐秘的瞬间”)是对伊斯兰教早期苏非思想和实践的记述,作为最著名的波斯语苏非名著,对后来的苏非主义贤者传记的描述影响深远。贾米也被认为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波斯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诸如大量的颂诗、抒情诗、四行诗、双行诗等著作,而以《勒瓦一合》为代表作的韵文体著作,将哲学、诗歌艺术、文学才情和苏非的心灵体验融为一体,兼有感性、理性和悟性。同时,贾米作为一位在伊斯兰世界至今仍然富有影响的乃格什板迪苏非教团的追随者,他早先跟随萨德尔·丁·喀什嘎里(d.860/1456)后来成为所有乃格什板迪苏非教团中最有政治影响力的筛海·乌白德·阿拉·阿合拉(d.895/1490)的弟子,并在苏非哲学的理论总结和修行方面,影响深远。
综合起来看,刘智在译介贾米的过程中,以及在进行《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的创作过程中,将伊斯兰的哲学范畴和思想图式进行了汉语语境中“格义”式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对外来文化思想的“格义”由来已久,早在魏晋时期,中国的高僧们就对佛教经典采取了“格义”的方法,即以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哲学概念或词汇为“格”(即格式、标准、体系框架等),以之比称或对比佛经中的名相,从而使中土人士能够明白和理解其意义。刘智作为明末清初的穆斯林译著家,他取舍的是当时宋明理学的主要哲学概念和儒释道互补鼎立的思想主流体系。他把贾米的伊斯兰哲学传统和苏非主义的思想、实践传统,经过这种“格义”式的创造性转化,投入到汉语的语境和哲学体系中,使中国的主流的文人士大夫和一般读书识字者能够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给予伊斯兰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的终极思考以及理念的认识、理解和接纳。刘智的努力和尝试是成功的。更为重要的是,刘智在他的译著和理论创作中,与王岱舆(约1570~1660年)、马注(1640~1720年)、马德新(1794~1874年)等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一道,为中国穆斯林建构了汉语话语体系中的一套伊斯兰的价值体系和意义体系。这一体系是立足于伊斯兰的原典和经训典籍的权威诠释,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相关范畴和概念,来恰当而精要地解释伊斯兰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和性命论的。但刘智的译介不只是翻译的“信达雅”,而是翻译过程中对中国宋明理学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超越和成功转化。
宋明理学受禅宗和道教的影响,在追求内在超越性方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进路。儒家讲求的内在超越的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更多的是关注现实中的人性的自身的成长和完美发展。但佛学、禅宗和道家对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中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道家的“道法自然”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影响很大,还有禅宗的“明心见性”、“人人皆可成佛”,强调发挥个体自主性、能动性作用,对后世中国人追求内在超越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就儒家而言,儒家的经典《中庸》就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作为“天下之大本”,孟子提倡“尽心知性知天”的说法,而陆象山则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儒家所具有的内在超越性特征和思想追求,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人道既不是神中心的,也不是人中心的。毋宁说,它指向了天人之间的一种互动性。由于坚持天人之间的互动,人道一方面要求必须使人的存在具有一种超越的依据,另一方面也要求天的过程得到一种内在的确认”。所以,具体地讲,儒家的“中”这种对人性中原本的宁静状态的体验“不仅只是一种对于这些基本感情出现之前的平静状态所进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体验,而且还是一种对终极实在所作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体验”(杜维明,1999:4~6)。儒家的追求内在超越的重点既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古希腊传统,也不同于东方的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内在诉求进路。而是关注当下、关注现实、关注此生中个体人的道德的完善,不言后世和灵魂不死的问题。所以说,儒家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一种提倡由己推人,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群主义和天下主义的人文理想,这种由内向外的超越始终只是伦理的、经世致用的对现实的有限超越。
苏非主义在坚持彻底的认一论的前提下,注重开掘心灵世界,反求诸己,通过对处于世界中的人本身的自我观照,通过一定身体力行的功修和实践行动,不断净化心灵、升华精神,不断超越人自身的各种局限,以实现和达到对绝对实在的认识、接近,使外在的超越和内在的超越达到互通。苏非主义思想对刘智的哲学思想影响很大,其最具代表性的《天方性理》中,就不时闪现着苏非主义哲学思想的光芒。在译介《真境昭微》中,刘智认为,人要认识真一本体,必须认识到“真主无时无地而不临观万有之表里也”,但人的自身局限性却往往使人难以明白个中道理。故他说:“嗟乎尔人,不见其见,且见他物,不道其道,且道别途”(见《真境昭微·见道三章》);在苏非主义看来,作为生存于现世的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所以人是有义务、有责任和有灵性有智慧,能够积极地去认知终极实在、接近实在的。所以,人既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又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所以,贾米和刘智认为:“人身虽浊,其性最灵。因形而受状,遇物则染也。达者有云:‘人性苟能体真理而见象,则象不能碍矣!合真象而成形,几与天地同体矣!……慎守之士,亡我亡物,究体研真,明夫万有之品,皆其华美流传之处,众物之阶,皆其全能显露之所,至道真脉,于此得手,玄功妙致,于此用力,喜己喜物之心化矣。存己即存主,喻己即喻主,碍者通焉!’”(《真境昭微·研究六章》)人必须通过自身的磨炼、修行,开掘内心世界的深广度,开启心灵世界的深层体悟,不断攀升精神的高峰,不断提升自我的觉悟,才有可能取掉各种自身的遮蔽,达到最终浑化的“凡纳”(Fana)的终极境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超越,实现伊斯兰苏非主义哲学所倡导的至高、至美的诗意境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