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与超越的危机:长时段的历史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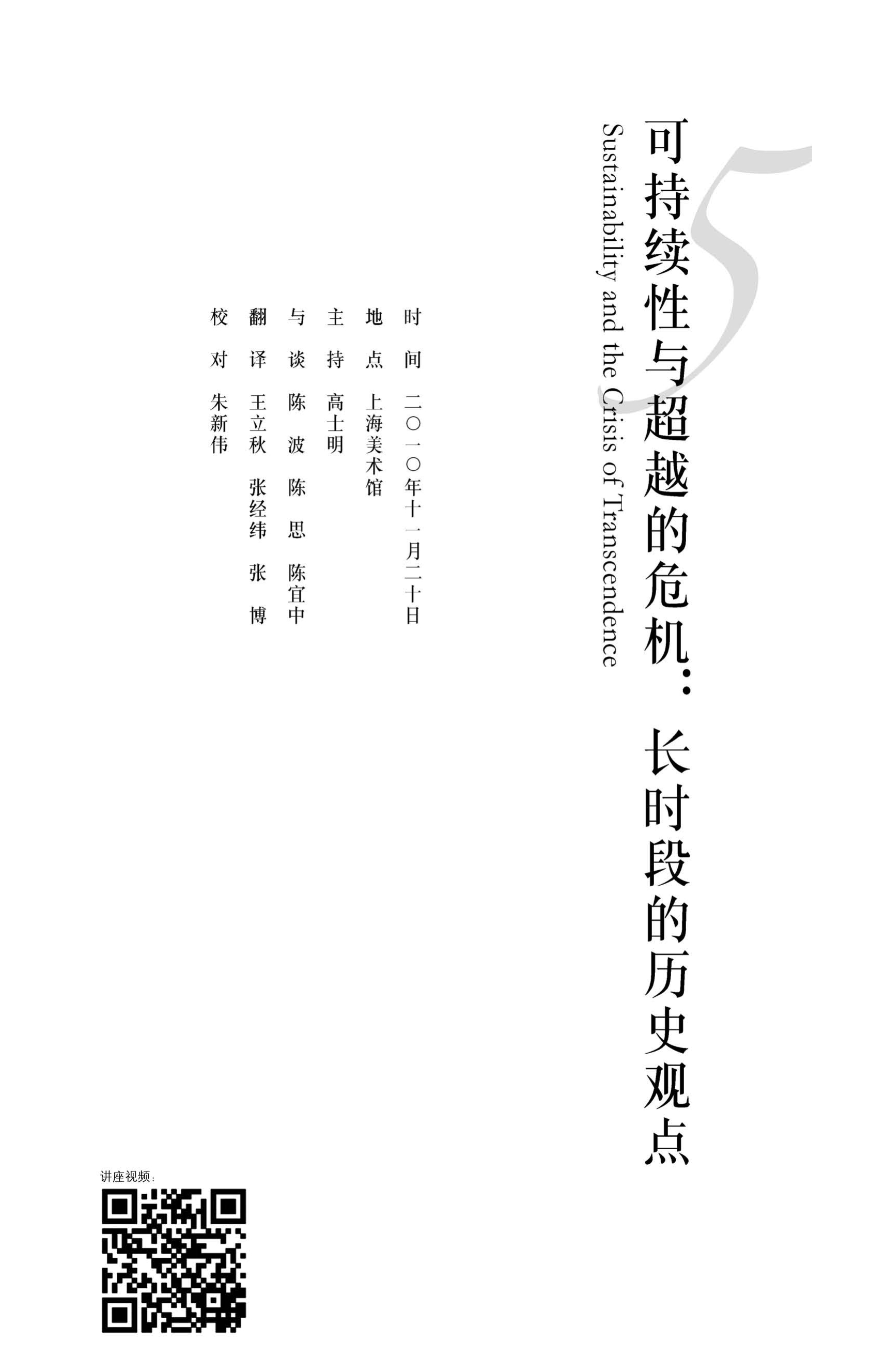
在各个复杂社会的历史中,人类对超越的渴求——超越苦难、不平等的境况,并在人类世界中实现一种未知境况——一直存在。众所周知,这种境况是一切世界宗教的基础。今天的世界也许比以往更需要直面现实、脚踏实地的拯救。毕竟,在现世永久地实现这个超越世界,乃是人类从古至今的目标。
讨论轴心时代的宗教,是评价超越性在人类历史上之作用的方式之一。尽管“轴心时代”这个术语有些蹊跷,但这个词所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却非常重要。轴心时代的关键在于超越与世俗之间的分裂。这些文明的目标都内嵌于一个神圣的超越世界。因此,尽管这个世界与人类世界并不相连,也没有人——包括国家——能够完全在此世实现其目标或意志,但人们却不倦热望着它的实现。轴心文明代表一种新的反思,表现了一个不同于此时此地的另一个世界的景象。一旦这个景象建立起来,超越世界也就成了宗教中的普世伦理的本体论基础。其中包括组织社会的更好方式,以及对自我牺牲的要求。
在所有轴心文明中,职业神职人员群体(教会、牧师、僧侣、阿訇)独立于国家制度,他们阐释了超越的世界并限制了国家的道德权威。因而,他们支配着一个不受制于国家的领域。由于轴心社会超越的目标及其实际成就之间存在差距,它天生有一种挑战现存神职人员和国家,并寻求新的个体和制度的变革手段,以实现超越世界目标的动机或倾向。亚伯拉罕宗教和印度教——佛教传统(如方济各会、新教、佛教、苏菲主义和巴克提运动)中,周期性的改革运动以反对现存知识阶层为目标,反抗权威,并召唤超越世界,试图在此世重新创造一种新秩序,实现超越世界的理念。当然,这些运动可能过多专注于彼世的诉求,或者,常常为统治秩序所挪用。但社会和制度诉诸了超越世界的能力,在这些社会的历史中起到了重塑和改变——即便这种重塑和改变是以永恒回归的名义进行的——的推动作用。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尽管轴心时代的中国兴起了各种学派的思想,但从未发展出一种强有力的超越理念。人们一开始可能会认可韦伯的观点,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帝制国家的强大力量组织了儒家和其他民众群体接近上天的超越力量。法律上,只有天子才被允许供奉上天,并阐释它的旨意。然而,这些障碍却很少能阻碍儒家思想各种的潮流和流派——尤其是泰州学派——对上天的诉求,以及对圣人的效法。而这表现了对现行秩序的反抗。而且,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一种取自佛教和道教观念、混合了儒家伦理的超越的混合观念在大众文化中相当流行。通过诉诸超越的理念,这些运动挑战当局、引领历史——无论是通过民众的抵抗,或是通过对个体或群体行为的伦理典范的拥护。
当然,由于世俗主义崛起——比如在过去的100年间——我们已看到许多非宗教运动也为引导社会而提出了伦理规范。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曾成功地把许多人的行为导向了原本属于宗教的、受难、自我牺牲和殉道的目标。但这些运动并不是超越的,或者说它们的超越注定受到“自我与他人”对立的世俗观念的局限。每一个运动都受竞争环境的影响,把获取越来越多的世俗资源当作其目标。甚至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想也从属于工具理性,并最终为工具理性的逻辑所埋葬。今天,在冷战终结、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之际,连要求人们为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而略尽绵薄之力的民族主义,似乎也已力不从心。
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世界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阶段:即便有诚意,也很难解决民族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然全球化,但同时又几乎没有有效反思社会价值和目标的权威机制。因此,无论我们谈论恐怖主义,无论生物、经济还是环境的危机,都已经到了一个为维持民族国家,不得不去超越民族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阶段。换言之,我们不是为了抛弃民族国家而召唤超越,相反,是为了继续维持民族国家而召唤超越。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全球资源可持续性问题。以全球水资源为例。水和超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注意到,天上的尼罗河,海神巨人俄亥阿诺斯,中国的龙王(创造天、地及所有河流之神),以及关于龙的禁忌。
如今几乎每个亚洲主流社会都存在水资源危机,都亟需跨国解决方案。地区之间的公共资源需要协调综合处理。不单水资源,气候变化、公共健康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是如此。
但水资源的问题最为紧迫。印度与巴基斯坦、印度与孟加拉、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印度,这些地区之间都存在水资源共享引发的诸多问题。亚洲有10条主要河流经过喜马拉雅山脉。湄公河上有3座大坝,若干东南亚国家还在计划建造更多的大坝。许多组织已经站在东南亚国家的立场上抗议水流和生态变化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恰当的协调机制,让一个跨国机构来独立、透明地检测每个国家国境内的水流状况。
最近,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他对作为现代社会充足基础的交往理性的信心。根据这种延续启蒙遗产的理解,人类的理性有能力在自由开放的沟通机制下,在不同群体和社群的各种价值主张之间进行协商,并由理智的或有效的理性标准来加以判断。就在这种交往能力中,理性具备创造共识权威的潜力。在哈贝马斯的早期作品中,这种理性的基础与宗教权威有着明显的对立关系,后者,则为前启蒙社会提供了道德基础。
过去十年里,哈贝马斯写了许多论文——这些论文的英译本在2010年初也出版了。在他这些论文中,程序理性不足以充当社会内聚和伦理引导的基础。某种程度上,这标志着回归到二战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观念。两人对作为大屠杀和世界大战的现代理性和技术基础的工具理性发起了批判。他们谴责技术理性的权力与角色——包括无所不至的官僚制和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消灭了对西方古典思想传统来说非常重要的关于目的与终极目标(telos)的公共讨论。世俗社会没有任何质疑其理性程序之结论与结果的手段。
哈贝马斯认识到能够以用来指导技术理性与社会的伦理规范来引导现代社会的具体目的与终极目标,他承认历史上的宗教在实现这一作用上所取得的成就:“在现代社会中,只有那些能够在世俗领域引入其宗教传统的本质内容——这些内容指向纯粹属人的领域之外——的社会,才有能力拯救人的(存在之)实质。”但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哈贝马斯不愿赋予这些宗教应有的社会地位。确实,考虑到许多现代宗教扩张和推行自身理念的趋势,我也担忧这种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试图更多地关注宗教的实践作用。他的想法与认为宗教既无用且危险的观点截然相反。但最终,在许多民族国家中,世俗国家在实践上无法给予宗教更多的制度空间。宗教是用来滋养我们私人生活中的价值的,而后者将对公共领域产生一种有益的影响,但宗教却不能用它的实际规定来支配公共领域。道德与价值的危机依然存在。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为人类重新发现超越呢?正如哈贝马斯的讨论所示,我认为我们无法简单地回到宗教。首先,世界上许多领袖都已经吞食了世俗思想的禁果,我们不能期望他们会真心实意地接受宗教信仰。其次,当代宗教思想本身就已被竞争环境所腐蚀,这个环境完全与身份政治和竞争风气交织在一起,使得超越的目标本身就已发生了扭曲。尽管原教旨主义者批判当代社会缺乏伦理与道德,但他们也追求着消除非信徒或认为的敌人的激情。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论证的那样,亚伯拉罕宗教,尽管具有深刻的超越性,却同时也包含一种原始——民族国家(proto-national)共同体追求,在这种追求中,自我——他者的区分与“被救赎者与被责罚者”的二元对立相互重叠。我并不清楚,这些信仰强烈劝诱改宗的伦理是否能为我们既竞争又相互依赖的社会找到一条出路。
或许,宗教的历史也能告诉我们一些与超越的条件与类型相关的知识?首先,我们有宗教或近似于宗教的传统,在这些传统中,同情的理念要强于自我救赎、选民之救赎或有条件的救赎的理念。而且,在这里有必要重提哈贝马斯的原话:只有“指向纯粹人类领域之外的宗教传统才同时具有救赎人类实质的能力”。我们需要一种不仅触及选民或信仰之人的需求,更超越于人类自身之外的超越的概念。讽刺的是,一些宗教,包括一些亚伯拉罕宗教,有能力超越人类但同时又无法超越信徒。信仰是救赎的条件。亚洲的宗教,就其注定涉入身份政治而言,给了我们更多的希望。
儒家、道教、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思想资源中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尽管我们应当承认,每个宗教同时包括一些反人道的特征。这些宗教具有强烈的普世性和包容性的品性,尽管包容的伦理在历史上一直是等级化了的。与强烈的救赎主义、预言性的启示或圣典真理的本质相反,这些宗教的超越真理较为空洞,不够明确。在非亚伯拉罕宗教中,扩张的模式更多依赖于吸纳和包容,而不是对绝对真理的皈依。仪式的盲从性容易把参与者纳为信众,尽管其中不乏目的的真诚性。最后,一些上述提及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与道教,其宇宙论对于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有着清晰的表述。
我应当说明,我并不是暗示我们应当有选择地利用宗教来获取一种超越的可持续性。正如我在关于哈贝马斯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我认为,对宗教的有选择的、功能性的利用,是会产生相反效果而相当危险的。与此相反,我探索超越性的历史角色,为的是考察宗教对它来说有多重要或者有多必要。其次,我们会探索许多宗教在自我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关系(包括诸如中国西南地区的以万物有灵信仰为主、规模较小的许多宗教)——它们将个体、集体认同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这就引出了我们如何定义宗教的问题。篇幅所限,在此我简单地把宗教定义为一种人类与神或超自然主体互动的实践机制(这一机制并为我们在此世或彼世的存在提供了前提条件,并塑造了我们的存在)。按照这个定义,世界上存在着非超越的宗教,比如说,那些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类似儒家的学说,虽可能不具备超越的天堂观念,但依然可被合理地看作宗教。儒家和其他一些包括小乘佛教在内的学说一样,也或多或少具有宗教倾向。因此,比如说,汉儒天人感应的宇宙论中,有着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积极干预功能的上天。但其他儒家流派也有仅仅以在此世达成与天一致,或以尊崇上天为目标的修身之道,超自然的干预或决定的观念非常微弱。
而且,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宗教,我们会发现,在隶属于神圣秩序与非神圣秩序的领域之间有着积极的“交通”,尤其是在现代时期。宗教理念可转变为世俗实践,而世俗实践也能变为神圣的甚至超越性的理念。关于这种我所谓的“交通”,耳熟能详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向资本积累策略转变的讨论,以及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的概念。在后者的理论中,国家主权隐喻着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我探索了东亚历史的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宗教仪式后来也变成了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公民的义务。20世纪中国儒教历史的这个方面确实非常有趣。康有为之类的拥护者试图把它变成基督教化的宗教(“孔教”),而蒋介石则试图通过中华民国的新生活运动把儒家的道德戒令发展为一种公民伦理。换言之,神圣的行动者无需继续附着于超越的目标。
那么,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的到底是什么?尽管存在一些涉及这种交通的因素,根本的维度还是涉及被转移的概念、目标或实践的神圣性。它表达了一种能产生天然崇敬和自我规训——即使算不上自我牺牲的话——的道德权威,这种权威被转移到陌生或全新的领域。灵氛(aura)被一种在象征、仪式和神话中表达的神圣机制所支配,而这些象征、仪式和神话则向实践者传达了一种情感上的力量,并表现了共同体的德性或更高的善。这种转移在现时代的最好例子便是从宗教到民族主义的变迁。请读者注意国旗普遍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人们可以为这个象征物牺牲或杀戮。更复杂的例子则包括19、20世纪美国的天定命运的叙事,印度母亲(不仅以母亲形象示人,而且作为战神现身)或当代中国黄帝神话的复兴。确实,在民族主义的大部分历史中,它都一直为其自身的目的而转译了许多宗教叙事话语和象征。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讲,其神圣象征当然已被转移,但转移的理念或对象却是超越性的某种妥协形式。民族主义的超越性能够超越各种专一主义和利己主义,但也严重受限于自身的部落主义和严格的自我——他者二分结构。按照涂尔干的术语,这是一种共同自我崇拜的直接形式。[1]
我的目的是考察:能否切实地提升超越理念的可持续性。考察的初衷显而易见,而障碍也同样显而易见:民族领袖心中应有准绳,即绝不能牺牲民族利益。克服这种抵抗的过程既是理性的又是象征性的。从知识和学术上说,过去30年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对所谓“环境伦理”的普遍领域的大量关注。随舒马赫《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而来的运动,深层生态学、佛教经济学、动物伦理、生态女性主义等,已经建立了将自然或至少原始自然加以神圣化的可能性。从激进的“地球优先!”运动(Earth First!)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全世界的各种环境组织,生态旅游的兴起,以及环保运动越来越活跃。
回到亚洲的经验,由于我们痴迷于追求现代化对自然的控制与操纵,最近的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有益的案例。我在其他文章中考察了罗宾格拉纳特·泰戈尔提出的所谓“可持续发展”,泰格尔将其视为一种关于超越性世界的观念,1920年代时称之为“泛神性哲学”。泰戈尔批判民主主义和工具现代性,希望从亚洲传统中找到另一种世界主义,并在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Visva-Bharati,其座右铭是:一个窝巢中的世界)付诸实行。他被印度历史上另一种流行的传统所吸引,这种传统就是卡比尔(Kabir)、那纳克(Nanak)和达都(Dadu)古老的巴克提先知和预言家,他们是超越观念的推动者,打破了社会与宗教排斥的樊篱,将社群以精神改变的形式整合在了一起。
泰戈尔的独特性与价值在于他的方法将地方性与对超越终极目标的地方认同联系起来了。这是圣地尼克坦精神表达的基于本土的世界主义。教育让人们认识整个世界的同时,本土代表了认识的手段。圣地尼克坦的教育计划以不同的世界传统著称,但学生仍致力于他们自己的环境和传统。泰戈尔发明了庆祝当地不同季节的世俗节日,在丰收季节将城市与农村结合在一起。他发起了部落成员和农村人口的合作运动,试图对他们进行卫生、农业、储蓄和其他现代生存手段的教育,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他们的本土文化。
我相信,民国时期,由梁漱溟、陶行知开创的乡村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周作人、顾颉刚的民俗运动,以及费孝通的“走向人民的人类学”,等等,都属于异曲同工。我还没有机会对这些工作进行细致研究,但我们首先需要探究他们的思想方法。本土资源如何与民族或文明相联系?他们如何看待三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尤其是本土和文明两者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此外,他们要怎样将不同的文明传统整合到另一种全球性传统当中?
在今天的中国,环境运动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杨国斌提出,近来涌现的中国环保运动的NGO用为群体自我组织而设计的网络平台和推特来实现快速动员。这些公民组织形式正接近一个让他们的声音开始为政府甚至全球所倾听的阶段。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政府在环境教育方面作出的努力可能是最大的。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道,在2003年于公立学校中推行环保教育。这促使许多地方政府和群体为在校学生制定相关教科书与教育项目。
不过,在一个社会中把发展环境教育作为一种改革力量存在诸多困难。课程可能较为形式主义,而这种努力的严肃性,可能会因为政府对环境教育考核的某些空泛内容而削弱。更普遍的情况是,儿童以及很多成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都相对地逐渐远离了自然环境。他们已经看不到保护环境对他们未来生活的益处了。
这些情况促使一些草根环保NGO在环境教育方面作出重要的尝试,其中尤其以云南的NGO为代表,这个有着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也因此成为“NGO的摇篮”。罗伯特·埃尔菲德(Robert Erfi d)对丽江的纳西族(尤其是拉市海)地区的NGO的研究表明,一些小型、经费有限的NGO致力于环境教育,并不只是为了使环境研究符合当地情况,而是为了让孩子通过一种实践的、亲身体验的教育来接触环境。比如,云南生态网络(Yunnan Eco-Network,简称YEN)及其负责人陈永松带领在校学生参观森林、了解杂草对作物的入侵,修剪树枝,创造校园园林,以此保护当地环境。
埃尔菲德强调,不仅要在实践中学习环境管理和可持续行为,而且教育的目的还是要培养致力于可持续行为的推动机制。这类推动机制的作品强调,每个人对自然的理解,根植于人们对非人类世界的体验。纳西族的东巴地区有保护自然的历史。水和森林都是神圣的,这就促使人们以可持续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公共资源。村庄勒石铭刻乡约,并通过神灵和公共处罚来制止不必要的毁林和过度狩猎野生动物。一些NGO从中明确学到了培养环境认同的重要性。他们通过《乡土教材》之类的材料教导地方性——而不是抽象的环境,这些教材建立在当地或地区具体文化和生态特征的基础上,培养了年轻人的根基感和“精神家园”。[2]
我们看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并无太大不同。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正在涌现,这是一种推动、促进个人与群体行动的新的超越性与神圣性。然而,这种理念即便具有一种强烈的理念,却并没有一种制度性力量,无法在不久的将来提供一种最高权力。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当下可实现的是一种更为隐秘的、地下的文化操演过程,米歇尔·福柯称之为“真理的游戏”:个体凭借这个过程,想要把他或她个人的经验转化为真理,并把真理重新植入他们的个人体验。这个普遍的过程很好地体现为电影《阿凡达》中的蓝色外星人形象。
至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已经没有太多的神秘性可言。我们需要说服民族国家的政府机器,在他们的教育和授课计划中,地球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时间要与民族历史和国民身份教育的时间一样多。在我看来,这将是我们时代的超越的先知和奋斗者面临的挑战。
【注释】
[1]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之所以无法超越历史局限性这一最重要条件,是因为它排斥了逻辑与道德上的普遍主义,而正是这种普遍主义才能将民族主义从其内在形式中区分开来。可以这么说,既然它的权威来自神圣性,那么它的超越性即便在最普遍的表述上,也是一种有边界或局限的普遍主义,而我们对这种边界往往毫不自知。很少有生命哲学在关于“好”的观念上,能不受至高神圣象征的局限。但比较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同样告诉我们,与神圣性相关的真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局限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神圣的普遍性与象征性是一组不稳定的平衡;当代的政治实践者必须时刻警惕将神圣性掩盖终极目标的做法。
[2]Rob Efi rd,“Learning by Heart: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Learning in Lijiang” Chapter Draft for Kopnina and Oiumet,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Today(Eds.), New York:Routledge, 2011; see also Robert Erfi d, “Learning the Land beneath Our Feet:NGO”,“Local Learning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unpublished essay.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