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意义与解释
“意义”这个概念与“理解”和“解释”这两个概念紧密相连,因为在理解或解释任何一个表达式时,就是要理解或解释这个表达式的意义。在许多场合下,如果对一个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我们就说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我们此时不仅说这个词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而且还能说出这两种意义是什么。例如,德语中的“Bank”一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因为它一会儿意指一条长凳,另一会儿又意指银行。他说:“在这里,每种意义总是有一种对它的解释。这些解释按其种类而言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也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彼此相似。”(v.10,p.59,§285)
维特根斯坦试图通过对“什么是对一个词的意义的解释?”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来阐明什么是一个词的意义。他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拉到地面上。因为毫无疑问,为了理解“意义”这个词的意义,你也必须理解“对意义的解释”这个词组的意义。他说:“让我们问什么是对意义的解释,因为,凡是以这种方式被解释的东西,就是意义。”(v.6,p.3)通过研究“对意义的解释”这个词组的语法,我们就能弄清楚“意义”这个词的语法,而不必到处寻找一种你可以称之为“意义”的东西。
在他看来,“什么是意义?”这种提问方式,类似于“什么是长度?”、“什么是数?”等等提问方式。这种提问方式易于引起哲学混乱,因为它促使人们去寻找一个与名词相对应的东西,在这里,我就是寻找一个与“意义”、“长度”或者“数”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我们不能通过指出任何一个东西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把“什么是意义?”这种提问改变为“什么是对一个词的意义的解释?”正如把“什么是长度?”这种提问改变为“我们如何测量长度?”就能避免上述那种哲学混乱。
在一般场合下,对一个词的意义作出解释,这不外乎要给这个词作出界说或下一定义。他说:“我们用‘对符号意义的解释’指使用规则,而且首先指定义。文字定义和指物定义的区分大致区分了这些不同种类的解释。”(v.4,p.51,§24)文字定义把我们从一个语言表达式引向另一个语言表达式,在某种意义上不可能使我们再前进一步。就指物定义而言,我们似乎通过这种定义而在理解意义方面前进了一步。可是,维特根斯坦对指物定义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他看来,首先我们会碰到一个困难,这就是我们语言中有许多词,例如“一个”、“不”、“数”等等,似乎没有指任何具体事物,很难对它们下一个指物定义。而且,指物定义本身也可能被误解,例如,如果我想给“苹果”这个词下一个指物定义,于是指着五个红苹果,可是别人却不能确定我所指的究竟是“苹果”、还是“五个”,还是“红色的”。可见,无论用文字定义或者指物定义,都不可能对表达式的意义作出明确和圆满的说明。他说:“从这种意义上说,有许多词没有严格的意义。但这不是一种缺陷。如果认为这是一种缺陷,那就等于认为我们台灯的光亮不是真正的光亮,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界限。”(v.6,pp.37-38)
维特根斯坦强调:“词具有我们赋予它们的那种意义;我们通过解释赋予词以意义。”(v.6,p.37)有些哲学家经常谈论要对词的意义进行研究和分析,仿佛词具有一种由某种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赋予它以意义,以致人们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以便发现一个词真正意味着什么。维特根斯坦不赞同这种观点,而强调词只具有人们赋予它的那种意义。我们可以对一个词下一个定义,并按照这个定义加以使用,或者那些把这个词教给我的人对我作出解释,或者,在另一些场合下,我们可能用对一个词的解释意指当有人问我们时我们准备给出的解释。一般说来,一个词有好几种界限分明的意义,对这些意义进行解释或分类都是比较容易的。关于另一些词,我们可能说,它们具有上千种不同的用法,这些用法逐渐地相互融合。毫不奇怪,我们对这些词的用法提不出严格的规则。
维特根斯坦强调:“我们用‘意义’指出了对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东西,而且对意义的解释并不是一个经验命题,不是一种因果解释,而是一种规则,一种协议。”(v.4,p.60,§32)他认为语言是一种根据规则而进行的活动,我们按照规则去使用语词。他说,可以用下述方式来解释“意义是对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那种东西”这个命题:“让我们只关心被叫做对意义的解释的那种东西,而不理睬任何其他名义的意义。”(v.4,p.32)
对于我究竟是每次都看见不同的东西,还是每次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去解释所看见的东西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倾向于赞同头一种回答。他说:“因为解释便是思考,是在做某件事,而看是一种状态。”(v.8,p.298)他认为要识别出我们在进行解释时的那种情形,那是很容易的。在进行解释时,我们提出一些假设,然后对之进行证实。可是,对于“我把这个图形看成一个……”也如“我看见一种鲜红色”一样,是很难证实的。他说:“在这两种语境中,‘看’这个词的用法有一种相似性。只不过不要认为你事先就知道‘看的状态’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让用法把意义教给你。”(同上)
关于意义与解释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提出这样的看法:“每一个符号从原则上说都可以得到解释;可是意义不能得到解释。它是最后的解释。”(v.6,p.46)他用上下平行的箭头组成的行列画出一幅关于意指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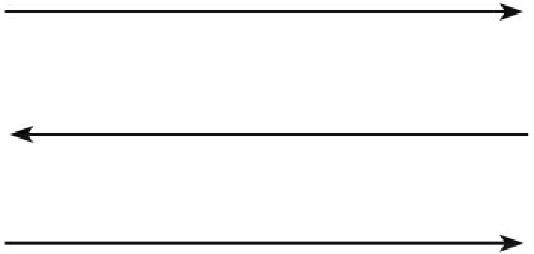
认为其中最低的那个层面始终是意义的层面。任何一个示意图都有一个最低的层面,而没有某种作为这个最低层面的解释的东西,这个最低层面就是意义。
维特根斯坦还认为,符号是从它所从属的符号系统中,从它所从属的语言中获得生命的,语句是作为语言系统的一部分获得生命的。他说:“符号(语句)从符号系统中,从它所属的语言中获得它的意义。简言之,理解一个语句就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v.6,p.8)
维特根斯坦在论证词的意义在于词的用法这个观点时,引证了弗雷格对形式主义的数学概念所作的嘲笑。他说,在弗雷格看来,形式主义者把符号这种不重要的东西与意义这种重要的东西混为一谈。他把弗雷格的观点表述如下:如果数学命题仅仅是线条的组合,那它们就是僵死的,不会引起任何兴趣,然而,它们显然具有生命。而且,对于任何一个命题,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命题没有意义或者没有思想,那它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生命、毫无价值的东西。仅仅给命题增补一些无机的符号,决不能使命题具有生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使僵死的符号变成有生命的命题,必须加诸僵死的符号之上的那种东西应是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就其特性而言它不同于一切纯粹的符号。维特根斯坦基本上赞同弗雷格的这种看法,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要给任何构成符号生命的东西命名,我们就必须说那种东西就是符号的用法。”(v.6,pp.7-8)在另一本著作中,维特根斯坦用不同的言语表述了这个观点:“我要说:一个词的语法位置就是它的意义。但是,我也可以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对它的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东西。……对意义的解释解释了词的用法。一个词在语言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v.4,p.51,§23)
维特根斯坦批驳了那种把符号的用法看做一个与符号并存的东西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符号的意义是那个当我们看见或听见符号时在我们心中形成的形象,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所看见的任何一个外在的形象,例如一个画出来的或者模拟的形象,去取代那个精神的形象。在那种场合下,为什么一个书写的符号在与一个画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时就是有生命的,而在单独只有书写的符号时它就是僵死的呢?一旦你想到的那个精神的形象被画出的形象所取代,一旦精神的形象由此失去它的那种神秘莫测的性质,那时这个形象事实上就不再是仿佛能够赋予语言以某种生命。他说:“可以把我们容易犯的那种错误表述如下:我们寻找符号的用法,可是我们在寻找用法时仿佛把用法看做一个与符号并存的事物(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之一反过来又是我们寻找一种与名词相对应的‘事物’)。”(v.6,p.8)
除承认意义与解释有关外,维特根斯坦也承认意义与意图有关。例如,当一个人说出“March”一词时,这个词究竟是指“三月”这个月份,还是意指“前进”这道命令,就需要我们对此作出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取决于说话者当时意图表达哪种意思,究竟他意图表达的是“三月”还是“前进”。但是,维特根斯坦否认这种解释是对这个人说出这个词时心中进行的活动所作的描述,或者对任何“内心事件”、“内在过程”所作的描述。他把这种错误观点称为“关于意义的神话”或者“关于内在过程的神话”。这种神话把意义误解为某种处于语言之外的东西,某种独立于语言的心理过程。他强调“意指不是一个与词相伴随的过程。因为任何过程都不可能有意指的结果”(v.8,p.307)。在他看来,意指并不是一种全部地或部分地说出某个表达式的活动,并不是存在于任何处于语言之外的心理过程之中。他说:“因此,把意指称做一种‘心理活动’是愚蠢的。因为这容易使人们对这个词的作用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v.11,p.127,§20)对于与意指有关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详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