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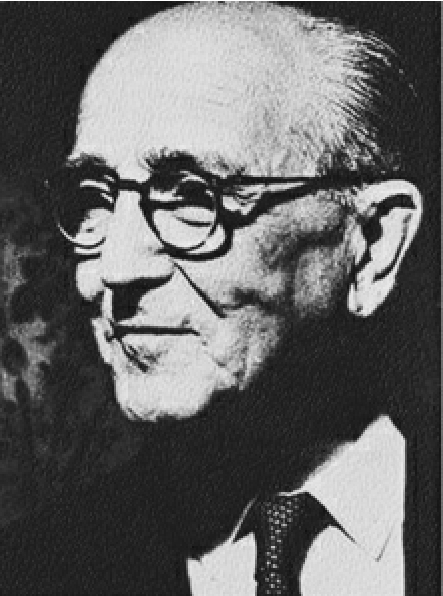
汉斯·凯尔森(1881~1973),美籍奥地利法学家
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原籍奥地利,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自1911年起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主讲国家法和行政法课程;1920年参加奥地利宪法起草工作;1920~1930年在奥地利最高宪法法院担任法官;1930~1933年任科隆大学法学教授、法律系主任;1936年任布拉格大学教授。1940年开始流亡美国,后加入美国国籍,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法学教授。作为纯粹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凯尔森一生著述颇丰,在西方法学界极具影响。在法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国家法学说的主要问题》(1911)、《国家法概论》(1925)、《国际法概论》《1928》、《纯粹法学》(1934)和《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1945)等。其中《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是其首创纯粹法学的集大成之作,通过“重新陈述以前用德文和法文已经表述过的思想和观念”,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法律、国家以及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确立了他的“纯粹法理论”(pure theory of law),将奥斯丁的分析主义法学推向了极致。
一、纯粹法学的含义及其研究对象和方法
首先,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理论,因为他认为纯粹法学研究的对象应严格限制在实在法(positive law)领域,即“共同体(community)的法”(如美国法、法国法、墨西哥法、国际法)。同时,研究的对象也应仅限于对法律一般理论的研究,也就是研究“法律规范(legal norm)及其要素和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法在多数实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1)研究法律的价值判断和目的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不是针对现实的科学研究对象;而对法律现实的研究是一种自然科学的任务,纯粹分析研究的是,法律秩序如何决定人们应当如何行为,是一种什么样的规范体系或规范性秩序。至于人们实际上应当如何行为,则是由自然法则根据因果关系原则来决定的,是一种自然现实,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凯尔森认为,纯粹法理论的方向在原则上是与分析法学一样的,只有将法学限于对实在法的结构分析上,才能将法律科学与正义哲学以及法律社会学区分开来,在这一点上,“分析法学和纯粹法理论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2)凯尔森将法理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共同体的实在法,严格区分法律科学和政治学及法律社会学,他通过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和“应当是这样的法”,拒绝将纯粹法理论变为这一种法的形而上学。因而,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属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其次,凯尔森的理论也是一种规范法学,因为他认为,“法的一般理论的主题就是法律规范及其要素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法在多数实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在其纯粹法理论中,“法律规范”是一个核心概念,而“法律规范”又是与“法律效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一理论的主题。“效力”是指“规范的特殊存在”,“法律规则如果有效力的话,便是规范”。(3)因此,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是在以“效力”与“规范”为核心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一种规范法学。
就研究方法而言,凯尔森的理论又是一种新康德主义法学,因为在方法论上他采取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方法。他认为,要建立理论一贯的纯粹法学,不能借助纯实证主义,因为纯粹法学需要一种超实证的前提和逻辑的假设。因为,只有具备这个有意义的同一秩序的假设,法律科学就超越了纯实证主义的境界;而放弃这一假设,就会同时造成法律科学的自我放弃。他认为,正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范畴不是经验的材料,而是一种经验的条件一样,纯粹法学的逻辑假设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而如果没有这个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我们就不能认识自然和法律。因此,“基础规范的理论可被视作信守康德的先验逻辑的一种自然法学说。”(4)
二、法的静态理论
(一)法的概念
法是人的行为的一种秩序,一个秩序是由许多规则组成的一个体系,人的行为是法律规则的内容。要对法律进行科学的定义,就要揭示出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如道德、宗教等)的独有特征,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而不是一个道德或政治问题。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必须同正义哲学区别开来”。然而,要将法的概念从正义的概念中分离出来是困难的,因为非科学的政治思想已经将它们混淆,从而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进行辩护。这是一种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倾向。凯尔森认为,“一个纯粹法理论——一门哲学——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根本不能科学地加以回答的。”(5)正义的问题是一种取决于情感因素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不能用理性的认识方法加以回答。凯尔森认为,唯有实在法才能成为科学的对象,只有这才是纯粹法学的研究对象,它是法律的科学而不是法律的形而上学,它专注于实在法,既不捍卫什么正义,也不谴责什么非正义,它所追求的是真实和可能的法律而不是正确的法律。如果我们要在实证主义的领域确立一种正义的概念,那么,它只能是一种“合法性”,即将一般规则实际运用到应该使用的一切场合,那便是正义的;把它适用于不应该适用的场合,那便是非正义的,“只有在合法性的意义上,正义概念才能进入法律科学中。”(6)
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技术,即“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秩序”,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从而区别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现象。(1)在社会对一种行为的反映方面,法律秩序本身规定了固定的认可和制裁,而其他一些秩序的认可和制裁是通过社会自发反映而表现出来的;(2)法律的认可和制裁是来自社会内在的性质,而其他认可和制裁则是先验的,如宗教制裁;(3)广义的制裁包括惩罚和奖赏,在现实社会里,前者比后者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法律的制裁则主要是惩罚;(4)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社会秩序,即法律制定强制措施来实现社会所希望的某种行为,也就是通过法律这种特殊的社会技术,在遇到相反行为时,以强制措施的威胁来促使人们按照社会所希望的方式去行为;(5)法律和道德、宗教的目的部分一样,但却使用了不同的社会技术,法律通过的是秩序指定的社会有组织的强制措施,道德则通过批判或者谴责这些无组织的反映来实现,宗教的教规依靠一种超人的权威来实现;(6)法律是一种有武力的组织,是一种使用武力的垄断;(7)法律可能使用的武力,保证了共同体的和平,但它剥夺了个人使用武力的权力,将其交给共同体,因而法律只提供相对的和平;(8)“精神强迫”不是法律所特有的特征,在这个问题上,法律与道德宗教并无区别,“一个法律秩序是‘有实效的’(efficacious),只严格地指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的秩序。其中丝毫不涉及关于这一行为的动机,尤其不涉及来自法律秩序的‘精神压迫’。”(7)
凯尔森认为,法律之所以具有强制力,是因为法律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对一定行为予以一定的制裁,这是法律的“效力”问题,而不是法律的“实效”问题。为此,凯尔森严格区分了法律的效力和实效,实际上也就是“应当”和“是”的区别。法律规范的本质在于“应当”,它表示某个人应当以一定方式行为。他认为,法律规范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尤其不同于自然法的规则。因为规则一词容易引起误解,从而将个别规范排除在法律之外,而个别规范同样也是一种法律规范。他认为,法律包含了个别规范,个别规范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其他法律概念
在静态法部分,凯尔森在论述法律规范这一核心概念后,又定义了法律的其他一些概念,其中包括制裁、不法行为、法律义务、法律权利和法律上的人。
制裁是一种由法律秩序所规定的活动,它的目的就是促使人们按照立法者所希望的那样去行为。法律制裁具有强制性,包括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两者有诸多不同,但其社会技术却是相同的。
不法行为是法律制裁所适用的对象,它是法律秩序认为有害的行为,是应当予以避免的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制裁的决定性要素在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立法者的意图。也就是说,只有法律规范规定了特定的惩罚条件后,某种行为才能被视为不法行为。
法律义务是法律规范中与制裁相联系的那个人的行为,这意味着,法律上的义务是指一个不法行为的潜在主体。法律义务也可以通过一个“应当”的形式表现出来,即行为人作出某种行为时,有关机关就“应当”对其予以制裁。
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的法律责任是指如果他作出与法律规范相反的行为时,他应当受到制裁。
法律权利是与法律义务相对的概念,它是相对于他人法律义务的一种权利,法律权利预定了某个他人的法律义务。针对在法语和德语中客观意义的法律和主观意义的权利的区分,凯尔森认为,“在有法律之前就不能有什么法律权利”,“法律权利就是法律”(8),只承认客观意义上的法律,不赞成主观意义上的权利概念。
法律能力是法律规范属人因素和属事因素之间的关系,它指一个人有资格为一定行为,即只有这个人作出这种行为时,才符合法律的条件和发生法律的后果,儿童和精神病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为不法行为。
归责是指不法行为的能力,意思是,如果具备制裁的某些属人的要求和条件,那么就要承担因此发生的责任。归责一词表达了这一或者那一事件被归给某一个人或者使它和他发生一种联系,是一种不法行为和制裁之间的联系。
法律上的人就是法律上的实体,法律上的质的义务和权利就属于这个实体。凯尔森认为,法律上的人是涉及权利和义务人格化的统一体。他区分了两种人的概念:一是生理上和生物上的人,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人;二是人格意义上的人,这是法学的、分析法律规范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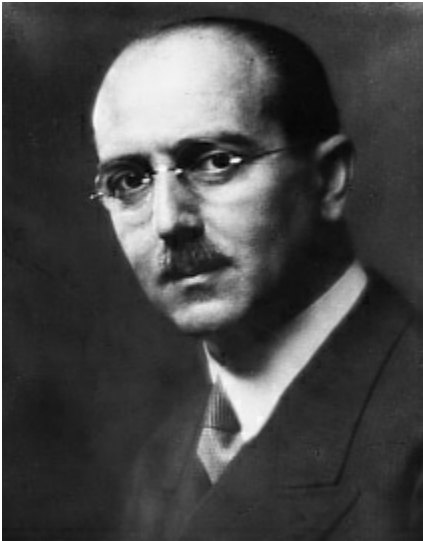
汉斯·凯尔森
三、法的动态理论
(一)法律秩序
凯尔森认为,法律秩序是一个规范体系。既然是一个体系,那么一个法律规范的效力就必定有一个特定的来源。因为一个规范效力的理由始终是一个规范,而不是一个事实,所以,探求一个规范效力的理由不是从现实中去寻找,而是去发现导致这个法律规范有效力的另外一个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每一个法律规范都从另外一个法律规范取得法律的效力,在凯尔森看来,
不能从一个更高规范中得来自己效力的规范,我们称之为“基础”规范。可以从同一个基础规范中追溯自己效力的所有规范,组成一个规范体系,或一个秩序。这一基础规范,就如同一个共同的源泉那样,构成了组成一个秩序的不同规范之间的纽带。(9)
法律秩序是一种委托创造规范的权力从一个权威被委托给另外一个权威,由此出现一个动态的规范体系。法律秩序之下的规范体系是一种动态的体系,规范之所以有效力是由于它根据特定的规则被创造出来。法律体系的基础规范是一个规范创造过程的出发点,法律秩序的特殊规范不是从基础规范中逻辑地推演出来的,而是从基础规范中,通过特殊的意志行为创造出来的。
凯尔森详细阐述了关于基础规范的理论。他认为,一个具体的法律行为,源于一个个别规范(即司法判决);这个个别规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源于一个一般规范(如刑事法律);一般规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依据一个宪法而被创立;宪法规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一个较老的宪法,按此推演,我们找到历史上第一部宪法。而这每一部宪法为什么有效力?这是我们的一种假设,一种假定,这是最后的预定,最终的假设,这就是那个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由这个基础规范产生了动态的法律规范体系,因此,基础规范具有特殊的功能。凯尔森认为,基础规范既不是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程序创造的,也不是通过具体法律行为创立的,“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是被预定为有效的;而它之所以被预定为有效力,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一预定,个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解释为一个法律行为,尤其是创造规范的行为。”(10)
一个法律规范是否有效,取决于各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决于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系统。处于一个有效的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规范永远具有效力,凯尔森称之为“合法性”,在法律秩序确定这个规范无效之前,它继续有效。
(二)规范等级体系
基于动态法律规范体系理论,一个法律规范决定另外一个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因而法律体系本身具有一个自我创造的系统。决定创造另外一个规范的那个规范是高级规范,根据这种调整而被创造出来的规范是低级规范。法律秩序就是这样一个由不同级的诸规范组成的等级体系。较高级的规范决定较低级的规范,高级的规范又为另外一个更高级的规范所决定,而最后一个最高级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为整个法律秩序效力的最高理由,由此而形成一个法律秩序的统一体。
法律秩序有不同的层次。宪法规范是国内法中最高一级规范。在宪法之下有一般规范,它在规范等级体系中构成次于宪法的那一级,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一般规范之下有个别规范,它是由法官针对一定的人执行的一定的制裁,即法院的司法判决。司法判决如同立法一样,它既是法律的创造又是法律的适用。司法行为是法律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层次,制定法和习惯法只是法律的半制成品,只有通过司法判决和执行,这个过程才趋于结束。
凯尔森认为,自治的个人行为可以是一种创造和适用法律的行为,这种个人行为可以设立个别规范,也可以设立一般规范。法院不仅是法律的适用机关,也是一个立法者。通常情况下,法律秩序存在一种空缺,即“间隙”,它意味着现行法不能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因为不存在一个涉及具体案件的任何一般规范,这决定了法院自由裁量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凯尔森认为,从法律规范效力体系的角度看,法律秩序不能有任何的空缺,与其说法院的作用是弥补这个空缺,还不如说法官的司法活动是在实际有效力的法律中加入了一个不与任何一般规范相当的个别规范。法律的“间隙”是一种虚构,这个虚构在两个方面限制了法官的活动:(1)法官的权力仅仅限于一般规范所没有规定的那些情况;(2)法律间隙具有一种心理学上的性质,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性质。司法判决除了先例对于以后所有类似案件的判决都有约束力,当司法判决具有先例的性质时,法院创造法律的功能也就尤其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法院实际上就是与作为立法者的机关完全一样意义的立法机关,法院也就是一般法律规范的创造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