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民出场”的“转型正义”,可以通过“群众路线”这个制度性实践而让人民出场,进而由人民之“无限循环”的确证性实践来不断地重新构建社会正义之向度。那么下面的问题便是:如何在共同体价值体系中安顿“转型正义”?
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往往很多价值会被置放在一起,作为社会变革之目标提出——似乎,它们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和谐自洽的价值系统。在当代中国,正义与民主,乃是两项经常被放在一起提出的价值,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26],正义当然也是个“好东西”,即,值得捍卫的价值。然而问题是:“好东西”们能否放在一起?如何放在一起?在作为“转型社会”之中国,这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规范性层面上(即价值建构层面上)的重视。
正义是一个硬价值(hard value);而民主也是一个硬价值。换言之,两者都内含“普遍性宣称”(universality claim)。半吊子正义的社会,就是不正义之社会;同理,半吊子民主的社会,也恰恰正是不民主之社会。汉语学界的政治哲学研究者们在研读施特劳斯(Leo Strauss)之作品时,往往不解或惊讶于为什么施氏会如此激进地反对民主。答案其实就在此处:施特劳斯捍卫的,正是正义的完整性与优先性。就共同体秩序而言,正义在一个“你鼓吹你的正义,我坚持我的正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成立的;而民主恰恰建立在“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见”之多元主义基础之上。民主主张用投票(人数)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正义。而反过来,真正有规范性力量的正义,则绝不会向人数妥协,正如施特劳斯对卢梭信徒们的质问——“普遍意志难道就不会出错?”[27]民主的结果,往往并不正义(多数之暴政)。[28]
“转型社会”往往无视民主与正义这两者之间的规范性紧张,从而忽视在促进民主时可能造成正义被伤害的状况(民粹主义的危机),或相反,在确立某种定于一尊的正义时,忽视社会中诸种群体的反抗性潜力(精英主义的危机)。此两者,都会激起“抗争性政治”,诱发大面积的社会动荡。而这便是许多“转型社会”在进行到中途时所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它的“表象”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往“左”一步也不是(激起动荡),往“右”一步也不是(同样可能引起民变);往“回”走业已不可能,往“前”走则一片漆黑……在我看来,处在“深水区”的转型社会,并不应急于确定“方向”,以求快步走出危险区,而应如齐泽克(Slavoj Zizek)所建议的,“Don't act,think!”(不要行动,要的是思考!)——急于确定一个方向行进很可能导致“转型社会”整体性崩盘、改革成果尽皆付诸东流;必须先深透地去反思转型目标中的规范性紧张、缺失乃至剧烈断层。
那么,如何安顿“转型社会”的正义?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现代中国之一大核心思想遗产的“群众路线”,同样具有着可资调用的规范性资源。如前所述,按照巴迪欧的看法,以构建人民为目标的“群众路线”实践,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并非只是基于个体主义之上的“投票”实践,它首先以形成一个共同体之“共同的表面”为旨归,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现代社会中避免民主仅仅沦为“代议民主”。一个共同体内通过“群众路线”确立起来的正义向度,便不再是基于“人数”多少的博弈游戏,而是真正接近“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政治过程。
而“群众路线”的“无限循环性”,使其拒绝将任何一种当下正义等同于绝对正确:正是因为“普遍意志仍然会出错”,所以才需要“无限循环”,使之“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作为一个“反复逼近的方案”,“群众路线”恰恰能够使得正义与民主得到共同安顿:正义是一个绝对的硬价值,但它并不直接等同于那现实社会(“转型社会”)中的实定性正义,而是需要通过真正的民主实践(“群众路线”)不断地去反复逼近。
如何在“转型社会”中安顿正义这个问题,不仅关涉“民主vs.正义”这一规范性紧张,还涉及“普遍性vs.特殊性”这个政治哲学上的根本性问题。“转型社会”当然是一个特殊社会,譬如当下的中国——不管以哪种标签来形容它(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须认可其当下的特殊性。但是,“转型社会之正义”是否也是特殊的呢?换言之,让我们接续上一节已论及的话题来提出如下追问:正义是否有地域与时效限制?晚近五六年,汉语思想界最大的争论,实乃围绕着“中国特殊论”展开。如果把问题切换到“正义”视角,那么,争论之焦点便是:中国道路——甚至晚近被称作“中国模式”——所蕴含的社会正义及相关价值体系,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
如前所述,和“善好”“美”不同,“正义”作为一个“硬价值”,必须内在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适用性,否则自身便不能成立:一个人人都有自己一套“正义”、彼此并不兼容的社会,实质上等同于一个没有“正义”之社会。但是,“转型社会”本身预设了时间性限制与空间性限制:“转型社会的正义”势必在根本上会是特殊性的(并不能被普遍应用)。那么,如何来处理规范层面上这一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紧张?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讨论的、倚赖中国政治与思想资源的这种“人民出场的重构性转型正义”理念,是否只是一个区域性价值?[29]
在学理层面上,这便涉及“普遍”(the universal)与“特殊”(the particular)的辩证。通过引入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框架,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如下处理:在政治领域中,从来没有不经从“特殊”之提升而直接生成的“普遍”。任何有力量的政治价值与政治方案,总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诞生,而上升出“普遍性”的向度,去应对或回应其他语境下的特殊问题。这就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zation)与“再地域化”(re-territorization)。在作为“转型社会”的当代中国中,任何被确立起来的当下价值,既是历史之必需,也必然会在未来(社会完成全面转型后)被否定(negated),或者说,被扬弃(sublated)。
然而,在当代中国,“老套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似乎已不再具有理论之规范性力量。故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一黑格尔主义话语作更精细的处理。针对社会正义问题,黑格尔主义的辩证立场是:(1)任何一种关于“正义”的论述,就规范性向度而言,总是具有着普遍性的内在指向;然而与此同时,(2)任何一种“正义”论述,亦总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诞生,而上升出“普遍性”的向度。从思想史上来看,欧洲启蒙运动的诸种理念(在今天往往被视作“普遍理念”),便正是诞生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刻,而随后逐步冲出地域的界限。同样地,最初产生于齐鲁之地的儒家思想,亦正是逐步地“去地域化”,而在历史中生成“普遍”的影响(在历史中中国自身系一个“天下”)。这种“地方性知识”与“普世性知识”的历史转化,便是黑格尔所说的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张旭东曾把启蒙理念说成特殊主义冒充的普遍主义、是“假‘普遍’之名的特殊价值观”[30]。任何普遍主义都恰恰是从特殊主义上升而来,没有不经历自身作为特殊主义之阶段的普遍主义。正如拉克劳所分析的,普遍主义只是一个“空无的位置”,从来是由某种(或某几种)特殊主义的内容所占据,并时时刻刻面对其他特殊主义话语的挑战——而这些话语能不断地“去地域化”,向普遍主义这个“位置”迈升。拉克劳将这些内在具有“普遍性”指向的特殊主义话语之内容,称作“政治阐述”(political articulation)。[3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转型社会的正义”具有成为一种“政治阐述”的潜力:作为某一种特殊论述的“转型社会的正义”,可能会有力量冲出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限制,而将自身普遍化。张旭东的“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致力于把所有普遍重新还原为特殊,然而他恰恰没有看到,任何具有规范性价值的政治理念,皆必须使自己向普遍这个位置攀升,必须努力证成自身能够成为一个普遍价值,那是因为,任何仅仅满足于恪守特殊的政治理念,在领导权斗争中都将最终无法守住自身。[32]
在一篇题为《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之路》的文章中,陈赟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的提法,乃是“一个临时性的自我表述方式”。“在‘中国特色’中,‘中国’这个词语其实更多地是限定语、是修辞语,而不是主词或中心语词。与‘中国特色’相关联的并不即是原始意义上的‘中国道路’,而是一条在中国发现的普遍道路。”[33]陈赟关于“中国特色”的这个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一个(准)拉克劳主义的阐述。就政治理念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存在论层面上的“主体”[34],而是一个发生学层面上的地点、一个场所,就如雅典(诞生了哲学与政治哲学)与耶路撒冷(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神学)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套用陈赟的语式,“中国价值”不应是“‘中国的’价值”,而是“在中国发现的普世价值”。反观思想史,儒家思想最初起自齐、鲁之地,但它并没有成为“齐鲁价值”;孔子当年针对周文疲弊而奔走于各国,他也没有在捍卫“齐鲁特色”的道路。就作为伦理—政治价值的理念而言,儒家的“仁”或者说墨家的“兼爱”,从来没有旨在成为一种“区域性价值”:它们都是包含普遍性规范方案的古典智慧,并在从特殊向普遍迈升之进程中构成互为挑战之关系。[35]
美国之霸权性地位能在大半个世纪里始终牢不可破,归根结底便在于它成功地将一套特殊理念上升为了普遍理念,将其所宣扬的那套生活方式(way of life),上升成为值得追求与捍卫的普世性生活方式。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将这个能力称作一个国家的“软权力”(soft power)。在奈看来,一个国家的软权力包括三层资源:“它的文化(它对于他人能产生吸引力的那些地方);它的政治价值(当它能在本土与海外都秉持贯彻这些价值时);以及,它的对外政策(当他人将这些政策是作为正当与具有道德权威时)”。[36]当然,奈的根本性局限,就在于他完全从国际关系视角立论,着重于“软权力”的策略性功能,即一个国家依靠其政治价值观、文化与外交政策上的吸引力,来对他国施以影响(而不是通过金钱或武力等“硬权力”进行收买或胁迫)。也正因此,他完全忽视了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软权力”——将自身价值从特殊提升到普遍的力量——的构成性(政治性)功能:它构建起一个共同体真正赖以持存的共同的表面。
基于前文所做出的学理考析,我在此处旨在提出如下论点:建立在“群众路线”之制度性实践上的“人民出场的重构性转型正义”这个理念,可以成为中国思想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一个真正的重要贡献——它具有着使自身从特殊上升为普遍的规范性力量(“软权力”)。[37]也正因此,我们绝不应把这一“转型正义”理念阐述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正义”。诚如陈赟所言:“这个普遍性层次是不需要用某种特色的限定加以理解的。譬如说,西方的哲学不会将自身表述为西方特色的哲学。”[38]返回到思想史中,我们看到:毛泽东等“群众路线”思想的原初缔造者们,恰恰已彻底超越这种“地方性知识”(“中国特色”“东亚特色”)视角——他们将中国的革命经验看作是在中国实践出来的普遍经验。“延安道路”不是一条只适合延安走的道路(特殊道路),而是一条从延安走出来的道路(普世道路)。延安绝不是存在论上的“主体”,而是一个发生学上的地点。
因此,“人民出场的重构性转型正义”,具有着使自身上升成为一个普世性政治价值的规范性力量,成为一个从中国走出来的政治理念(基于从《尚书》到“群众路线”的中国思想传统);换言之,成为一个在中国发现的普世政治价值(更精确地说,一个在中国发现的能够普世化的政治价值)。“人民出场的重构性转型正义”绝不能仅仅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而是在从特殊朝向普遍的迈升进程中,努力使自身冲破既有的政治视野与话语矩阵(existing political vision and discursivematrix),激进地提供出一个全新的规范性愿景。就这点而言,当下中国对“转型正义”的理论探索与政治实践意义深远:对内,它能够收获在共同体内构建起“共同的表面”这个关键性的政治任务;而与此同时,它亦能在其从特殊向普遍上升之进程中,对规范性政治哲学本身做出真正的贡献。
【注释】
[1]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4年度驻院研究员。
[2]关于作为“转型社会”的当代中国诸面向的海内外部分代表性研究,请参见[美]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董一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比]约翰·思文、[美]罗思高:《发展转型之路:中国与东欧的不同历程》,田士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美]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袁伟时:《文化与中国转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强、刘强《:互联网与转型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欧阳肃通,《转型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宗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颖:《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利益研究》,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马海军:《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陈春常:《转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罗卫东、姚中秋:《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何迪、鲁利玲编:《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韦森:《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闫健:《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海外学者视角评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3]一个晚近的研究可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4]这一脉思想在后来的墨家论述那里被保存了下来,并成为了儒墨之争的一个核心面向。
[5]从该角度观之,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所主张的复兴“王道三纲”,恰恰是人民不出场的正义。蒋庆等人直承自己接续的是董仲舒传统(公羊学传统),而我们知道,“民贵君轻”的先后关系,在董子这里被变成“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我们看到,“天命”论在董仲舒这里,被完全结合进了《春秋》公羊学之中:“《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王道三纲”彻底没有人民在场,君臣父子夫妇,是直接的“正义”(天道、王道),夫为妻纲不可能不正义。也正是“君臣大义”的框架下,今日许多新儒家学者毫不讳言以“做国师”为其立言与实践之方向。
[6]在毛泽东这里,“人民”与“群众”彼此可互相替换(“为人民服务”就经常也表述为“为群众服务”),乃至经常联起来作为一个词用——“人民群众”。
[7]参见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8]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p.122,emphasis in original.
[9]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p.122,emphasis in original.
[10]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5页。
[11]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12]在今天谈论毛主义的传统(尤其是“群众路线”),我们能够——也必须——将它同“文革”实践区分开来。具体论述请参见吴冠军:《“群众路线”的政治学》,载《同济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13]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4][英]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吴海针、王今一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15]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16]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p.122.
[17]Giorgio Agamben,Means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trans.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32.
[18]更进一步的论述,请参见吴冠军:《“群众路线”的政治学》。
[19]Alain Badiou,“The Communist Idea and the Question of Terror,”i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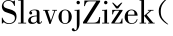 ed.),The Idea of Communism 2:The New York Conference,London:Verso,2013,p.9.
ed.),The Idea of Communism 2:The New York Conference,London:Verso,2013,p.9.
[20]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p.122.
[21]许一飞:《群众路线:中国特色参与式民主及其网络实现策略》,载《理论导刊》2014年第2期,第11页。
[22]譬如,郎咸平、孙晋:《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23]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进一步具体展开。
[24]Hannah Arendt,“The Perplexities of the Rights of Man,”i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3,pp.290—302.
[25]Giorgio Agamben,“Beyond Human Rights,”Cesare Casarino trans.,in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eds.),Radical Thought in Italy:A Potential Poli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p.162,163.See 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26—127.
[26]参见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 49152/5224247.htm l访问时间:2014年4月8日。
[27]Leo Strauss,“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in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Hilail Gildin(ed.),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91.
[28]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确实可以被当之无愧地称为“民主的敌人”,或者说,他是卢梭以降那种现代民主的敌人。显然,这位敌人并非空手上阵,他手里恰恰掐着民主制的“七寸”:在现代的情境下,整全性的形而上学已彻底倒塌,上帝之城也不再高于民主的公民社会,但在没有形而上学与神学的终极担保下,全民范围的“民主共识”如何形成?凭什么少数人就要对多数人的决议进行服从?在现代生活中,当各种不同的生活传统、价值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处理,仅仅凭人数多少么?在施特劳斯看来,唯一解决这种现代性困境的办法,就是重新确立起正义之向度,即确立正确与至善的坐标。“民主,或者说多数人之治,就是未受教育之徒的统治。没有人,若未丧失理智,会希望生活在这样的统治之下。”(Strauss,“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in hi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p.35.)更具体的论述,参见吴冠军:《民主vs.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9月(总第36期)。
[29]贝淡宁(Daniel A.Bell)等所谓的“社群主义儒家”就坚持声称,所有利用中国思想资源讨论而发展出来的理念,都只是中国的或亚洲的。参见贝淡宁:《超越自由民主——东亚语境的政治思维》,李万全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Daniel A.Bell,China's New Confucianism: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我对该论点的批评,请参见吴冠军:《贝淡宁的“缩胸手术”》,载拙著《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30]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
[31]参见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London;New York:Verso,1996。
[32]进一步的学理论述请参见吴冠军:《“当下性”与历史主义之双重面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33]陈赟:《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之路》,载《思想与文化》(第八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34]晚近甘阳等学者皆把中国阐述为一个“主体”,即所谓“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参见甘阳:《文明·国家·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35]参见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308页。
[36]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p.84.
[37]陈赟甚至将群众路线从毛泽东上推至儒家思想:“所谓群众路线,在骨子里传达了一个古老思想传统的久远回声,而儒家思想曾经是这个传统的最有力的表达者。”通过这个方式,陈赟尝试将群众路线确定为中国思想的内核之一。陈赟《: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之路》,第55页。
[38]陈赟:《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之路》,第3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