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艺术及其他学科的知识生产

艺术这一实验体制及艺术本身都在不断变化。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达维德(Jacques-Louis David),这名皇家艺术学院的领袖,把整个艺术学院激进地转换成艺术家的公社,由此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使得人人都能加入艺术学院。但是这个激进的举措仅持续三年,而且达维德本人也因其激进变革而差一点被送上断头台。
达维德的实验对于欧洲艺术学院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个时候,艺术学院被目为独立自主的区域,学院里的思考和艺术实践都是独立自主的,这与学术科目被非常清楚地分割化了的综合性大学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在独立的学院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实践都可被接受;而在大学,思考是一种被管制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欧洲的学院在做法上跟大学不一样,学院并不是在学期结束以后给学生颁发一个学位,因为它并不是要给你评价,然后给你一个课程化的学位。学院授予的证书只是证明在这段时间你参与了学术和艺术的实践。所以,对这两者进行区分很重要,一个是艺术学院的知识空间,一个是大学的知识空间。
今天的欧洲艺术学院正在进行着不亚于达维德1790——1793年之间的激进实验。现在我们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不是要建立相对于大学体制的独立性,而是要拓宽反思的范围,比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知识,对整个艺术实践的批判和质疑,开拓研究手段。当下的实践其实是把大学和学院放在一起来共同探讨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艺术知识”,它们是相同的,还是有区别之物?
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印度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话(她将英语文学的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学科),她曾谈到过一个学科的“死亡”,但我想谈的是学科的“新生”,因为很多事物一旦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英美文学在英语大学中的地位,不仅被看作美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还被看作为对社会生活的探索——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思想的研究。比如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我们研究她的小说句子中运用的非常精细的反讽,其实也是在研究英国的整个阶级状况。谈到英语文学研究,不仅仅是美学,而是研究整个英语语言,或者说其表达方式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和反映,同时也显示出英国乃至英语大学系统对于社会的看法。因为社会学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作为一门学科在英国逐渐确立。英国人认为社会学是从英语文学研究中间脱离出来的,它并非一门特别独立的学科。
大家可以就斯皮瓦克的《一个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展开一堂研讨课。重读这部著作有助于我们深入这次跨文化、跨学科的讨论。我的兴趣不是讨论一门学科的产生,因为这个太正式,已被体制化;我更想强调的是一个分散的、开放的结构,一个不确定的场域。我更愿意将它构想为一些地块,一些区域,而不是单向度的独木桥或不可掉头的单行道。我希望在很长时间内它都一直保持开放、分散或断裂,不让它凝聚沉淀成为一种教条或信条。
学科具有新陈代谢的特点。研究领域、方向也是有新陈代谢的。理解任何机构或者体制的计划时,我们都要把这一点记在心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上所有知识产物的来龙去脉。19世纪,哲学可以被看作主宰性的学科,包括科学在内,诸多学科都是哲学的附属,到最后都要经过哲学的判断和检验才算具有合法性。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讨论过新科学的精神,他质疑哲学作为一种主宰的角色,巴什拉提出,科学为什么是一种附属,为什么需要哲学的判断?艺术,包括艺术研究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认识论和获取知识的方式,有自己的工具或技术。我们要提出疑问的是,艺术实践,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手段是不是具有独立的、自我规定的价值?它有它自己的探索方法,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转换是一种变革呢?从生到死这种状态的转换,我要把这整个过程用电报一般简洁的语言来描述,这是热动力学家奥斯鲍恩·雷诺兹(Osborne Reynolds)的公式,他谈到水的黏度、水的阻力,比如我们在想像水流的时候,我们如何理解从A到B的流动,它是一种自然的、顺利的、光滑的流动,还是到了一定时刻会变得非常疯狂?我们想像一条河流,这是一种非常直截了当的想像,它可能是直线的路径,可能会有一些波浪、波动,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作线性周期运动。我们看到一个瀑布,我们如何去想像漩涡,如何想像这些被激起的浪花呢?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 做了很多探索,他关注事物发展的每一个时刻,研究事物成型的特定时刻,直到它达到一种令人战栗的均衡度(均质度),然后再完全张开,让它消失,造成一种新的细分。他的作品叫《疯狂铺砖》(Crazy Paving),其中还探究了各种各样的感情、感觉和思想的方式,探讨何为秩序和混乱。这些思考是我们在经历任何转型或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从秩序的状态再经过更迭的变化到达一种波动,就是所谓的紊乱,然后到整个全然的混乱,直到产生新的秩序。
做了很多探索,他关注事物发展的每一个时刻,研究事物成型的特定时刻,直到它达到一种令人战栗的均衡度(均质度),然后再完全张开,让它消失,造成一种新的细分。他的作品叫《疯狂铺砖》(Crazy Paving),其中还探究了各种各样的感情、感觉和思想的方式,探讨何为秩序和混乱。这些思考是我们在经历任何转型或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从秩序的状态再经过更迭的变化到达一种波动,就是所谓的紊乱,然后到整个全然的混乱,直到产生新的秩序。
艺术家是不是都是研究者呢?一些艺术家说我们一直都是研究者,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从某种方式来说这话没错,因为艺术家总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学院里的学科——例如社会学也好,人类学也好——来探究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区别一种即兴的、即时的研究。比如艺术家通过他的写生本、笔记本即时记录的想法的研究,和现在已经被纳入体制化的研究,和大学以及学院里的研究有什么不同。这些区分是十分必要的。
瑞典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欧盟对艺术研究进行了重组,现在是坡罗尼亚体系(在欧洲叫作Polinia Process,代表的是欧洲统一体系):从BA(bachelor of art,文科学士)、MA(master of art,文学硕士),然后再到PhD哲学博士,PhD其实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理学”,一种“探究”。在这个体制化的学术框架中,它的这种特定的探究,同时要受到体制的监察和审查,这是现在我们谈到的艺术研究。刚才也提到了在学院体制之外还有一种研究,更加即兴,更加自然,具有同等的有效性。在这里我更倾向聚焦于学院的发展。瑞典率先培养出了三位视觉艺术博士,欧洲开始改变艺术教育的规则,尤其是在一个已经扩大了的欧盟的大环境下,所谓“扩大的欧盟”(Expanded Europe)是指在丘吉尔所谓的横在东欧和西欧之间“铁幕”倒塌之后扩大的欧盟,它包含了整个过去的东欧,所以欧盟对艺术教育的改变也影响了东欧艺术学院体制。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非常新的机制。在冷战后和柏林墙倒塌后的大环境下,政治的变动也塑造了艺术学院的形成。
隆德大学培养了三位视觉艺术的博士。虽然其中有一门学科叫作艺术考古学,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说的是在欧洲的新机制下所做的有关视觉艺术的博士研究工作。在其历史成型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驱者,北爱尔兰艺术家苏珊·席勒(Susan Hiller)。我们来看一下这项工作在实践当中是如何操作的,如何在坡罗尼亚体系内、在欧洲范围内、在学院体制内实施的。欧洲的城市是自由体制,各自具有很大的自治特权,在市政厅中有一个市民箴言(city motto),在市政厅中,博士要面向市民进行公开答辩。这也是欧洲的习惯,而且旁边的展览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作品,在市政厅里的市民可以直接对这三名博士候选人进行拷问,可以直接去跟这些答辩者交流。博士论文打印出来500本分发给公众,然后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问题和博士候选人进行交流。这即是说,只有在公共场合经历过讨论、拷问的知识才算是知识,才算是合章法的知识,这也是欧洲机制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第一排坐着从世界各地来的考官,看起来非常吓人。如果要在体制的框架内理解的话,就要看整个的过程,就是我们要知道,知识只有在经历过审视,经历过公开的讨论、公开的辩论,甚至评估才算是“知识”。在最后我们再拐个弯,为什么是在瑞典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在这里我们要谈到宜家(IKEA),宜家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我们都很喜欢宜家。第一,它不是很贵,第二,其家具组装简易,虽然在组装过程中会感到不同程度的沮丧。我们访问了宜家在广州的分店,店里有隆德这座城市的标记,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适用性,作为一名从英国来的人,我非常感谢宜家帮我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家具的恶趣味,那么多累赘与复杂的东西。宜家的这种适用性非常清楚,也很实际。我们把它放在知识的实践中进行检验,而瑞典人也愿意把艺术研究、知识生产放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举一个例子,英文中,research这个词有两种发音,在美国念成[5rI7sEtF],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在英国一般念成[rI5sE:tF],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而在欧洲大陆,两种发音都有。我想知道这个词在中国的发音是怎么样的。这里不是要说明哪一种发音正确,哪一种发音错误,这并不是讨论要点。而是说它给我们显示了什么。英国人常常抱怨美国人念词的时候出错,但是我们在探究这个词的两个不同读音时给我们透露了什么信息呢?如果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一般它的定义就是在这块领域“重新复习一遍”或者“重新再查找一遍”,“重新再梳理一遍”或者“重新播放一遍”,等等,这是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的情况。那重音如果落在第二个音节上,在经典的英式英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设置一种学术的研究,而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研究者所未知的”。我们想像一下,一门学科有清晰的边界,有它的边缘和中心。另外一门学科是不确定的,是未知的,甚至是不可知的,比如说艺术。我们总是设想艺术是怎么样的,但是艺术家创作的东西完全落在我们想像之外,所以艺术永远不可能通过一种边界的界定来固化,它具有的这种非常狂野的、左右摇摆的特点跟我们说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的有条不紊、在一个原定地块上站定了之后再来一次有鲜明的不同,这种反差我们要注意到。
2008年我来杭州的时候,张颂仁老师和高士明老师带我参观了像是工厂或者是仓库的地方,这是一个艺术预科学校,里面都是备考艺术学院的学生。我们可以拿这样的情况和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的research进行对比,即我们进入一个已知的领域去进行排演、去比对,或者说去学习,去描摹某一个教授的画风,在模仿的过程中这其实也是向这位教授致敬。在预科学校里的学生学习如何准备画册,他们可能年复一年地尝试,但是有的没考进。没考进的学生可能还要继续作为预科学校的老师去教导下一辈的学生以备考艺术院校,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在这里要探讨一下“模仿的逻辑”、“相似性的逻辑”和“重复的逻辑”,在艺术院校中,现在的观点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的研究对象,也不知道其观点,我们现在进入艺术院校不再去学习某一种外语,不再去跟随某一个教授学习他的画法,而是要培养或参与一种思考的方式,然后画出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不再有一个已知的研究对象了,这就叫作“不同的逻辑”或者“异的逻辑”。在当代的艺术学校中,我们研究的对象常常是不可知的,或者说是模糊不清的。艺术教育应该就是要这样。我们只有在理解、或对比了相似的逻辑或相异的逻辑后,才能够对当今的艺术学校的体制进行清楚的解剖。
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新鲜,这是对于体制的剖析和反思,我们一定要问“体制在干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利用学院这个体制来进行创作,它作为一种体制已经成为创作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1960、1970年代出现了“反大学”(anti-university),由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创立。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就表明了反大学,一边是伦敦东区,从地理来讲也是与更富裕的、已经建制的资产阶级的西区成为一种对立,更平民、更激进。南边是金融城,西边是很富裕的城市。这些思想者和艺术家其实一开始就在质问、思考、剖析这个体制的框架,他们不把它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或既定的、用砖头砌起来的墙。例如,从美国的历史来看,例如布鲁斯·纽曼(Bruce Newman)、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约翰·凯奇(John Cage)等人,都曾非常详尽地对学院体制进行过解剖。为了什么目的呢?其实就是要重构,并给出一个清晰的结构,知识生产和艺术创造的结构到底是什么?相对于以前传统的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两者究竟有何差异?
我提到抽象的观念主义艺术传统,在绘画艺术中,这些实践者都开始探究对艺术实践中产生的知识总体的本质。是否存在这么一种特定的知识,其研究对象与大学学科体制的研究规定构成冲突。以杜尚的作品为例,其实他的作品也是研究性质的作品。他很谦虚,虽然作品暗含了普遍性原则,但他认为不应该普世化,不应该扩展应用到其他的艺术家或者整个艺术教育体制中去。杜尚的作品《大玻璃》(The Large Glass),以及同汉密尔顿1969年合作的《不完全的作品》(Almost Complete Works)在泰特美术馆展出,这件作品在当时可以说提出了全新的知识,但泰特还是比较传统的艺术博物馆,没有准备好迎接新的艺术探究的课题,于是拒绝了这个展览。但30多年后,泰特又花了上千万英镑买赝品匆忙拼凑起一个杜尚的展览,所以说体制并不能立即认识到艺术实践当中产生的知识的实体,这中间有一个时差,这个时差是需要我们尽量避免的。怎样避免?就是在学术体制的空间内要保持一种开放、倾听的姿态。只有保证多元化才能避免时差。
我要提到的第四和第五点,可以给大家轮廓性的地图来进行思考。作为知识生产的视觉艺术实践场域——这听起来口气很大——但是我们要问,它是什么样的知识?是社会学的知识、人类学的知识还是历史学的知识?我们来看看当今的艺术作品,比方说今年的上海双年展,在“巡回排演”中的很多作品看起来都像是用别的方式来重构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是民族志等,我认为这都是不错的尝试。我们不能把当代艺术形式局限住,它总是会同其他领域进行互动,甚至别的学科也认为在它们的研究项目中有必要吸纳个别艺术家。例如物理学,物理学家都希望将艺术家包括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是,他们如此急切地想在研究计划里包括艺术家,即使他们不怎么理解如何把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同社会学、气象学的研究进行联系,只是当作一种摆设或装饰。还有一种可能,他们认为学科并不是完善的,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希望艺术家在实践中给出他们学科整个规范尚未涉及的一些东西。
当然,艺术家也不是没做过糟糕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以我们这些艺术学院内的人也应该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艺术作为知识生产的方式,这种研究其实是通过视觉去思考,它不同于一般的在媒体中提到的视觉语言、设计语言。所谓的视觉艺术实践,它其实有自身探究世界的方式,有自身组织知识的方法,这些必须得到肯定。它不是要把自己置于其他的认知模式,比方说从智力上、从语言上或者概念上去看世界,不是要变成这些模式的附庸。这句话从一位杜尚迷口中说出来会有一点令人费解,杜尚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反视网膜”(anti-retina),但是我认为可视性(retinality)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学科产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场域。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有特别的反响,比方说中国的书法同认识之间的相对关系,与人的大脑、心灵当中概念化的能力,都有关系。我认为中国的语言有助于我们来认识这么一个非常鲜活的事实,即通过视觉来思考。我们为此还要感谢庞德,除了他非常恶劣的、有害的政治观点,他促使我们对中日的书法进行一种思考,对西方人来说,尤其需要仔细地探索。而对于西方来说,一种视觉的复杂性,比如隆德大学重要的生理学家,也是视网膜研究的领先人物尼尔森(Dan-Eric Nillson)所在的机构有一个成果叫《动物的眼》(Animal Eye),其中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视觉,什么叫做视野。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了视觉以后,才能够说我们到底是支持视觉的艺术还是反对它,或者是我们是偏向视网膜艺术这一块还是偏向观念艺术这一块。视觉、观念、图像、认知,理清这些关系非常重要。回过头来谈一下杜尚的想法,它其实是很微妙的,不是简单的一刀切,我下一项研究就会讨论,他对于视网膜的论述其实是受到了印度学家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的深刻影响。
因为它彻底的方法论也好,它的命题处理方法也好,可以说,科学有着优先于其他学科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崇高地位。艺术是不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是不是能够具有像科学一样的崇高地位?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艺术会不会有自己的方法论,还是说我们如此地设定了艺术的研究,使得它仅仅是从A到B线性的旅程?其实艺术作为一种旅程永远是有开放的结果的,是不可预知的,直到我们结束以后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伟大的科学哲学史家,或者说自然哲学史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有“反方法”(anti-method)的存在,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才能研究所谓艺术研究和科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费耶阿本德给了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这个题目,其实是借用了我当年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的一个讲座题目“告别理性”(Farewell to Reason),这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引起了一场非常大的骚动,甚至说是“丑闻”。
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检验真知的方法。他认为存在全面、严格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知识,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不是知识,但是费耶阿本德他没有说这些东西就不是知识,在梵语中是“vidya”,它是介于知识和非知识当中的某种中间体。费耶阿本德还提出其实巫术也是一种“元科学”,所谓元科学就是科学的母体,科学之前的科学。他还提出这种土著人本土的知识其实也是了解自然、医学乃至整个世界的知识,不能通过理性主义这样的有色眼镜来定义这个框架,或拒绝本土知识。我们很惊讶地看到,费耶阿本德作为一个科学家,转向了艺术家,把艺术达达主义作为知识的概念,扩大了知识的定义。我提出一个新词,叫作“达达主义认识论”,尤其是美院的两位教授邱志杰和卢杰,他们的实践就是受达达认识论启发的。这种知识论不直接给我们一种教义,而是给我们挑起一种思维方式,它破除了日常行为和实践过程中的逻辑,所以我叫它“达达的锻炼”。这种锻炼是对惯常现象的锻炼,对我们重新定义知识生产的场域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伟大的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也对知识生产的概念有所贡献,例如间离效果。在这两位学者艺术家和学生一道进行的讨论课上,我感觉到我们已经接近了达达主义认识论,但是我不想给予一种全然的定义,因为这是一个正在产生的过程。我想惟一的方法就是紧扣住达达主义认识论对于理性主义的质疑。我想引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面的人物波洛纽斯(Polonius)的一句话,波洛纽斯是奥菲莉亚的父亲。波洛纽斯的观察很细致,他注意到了情绪非常波动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父亲被毒死,母亲下嫁给了他的叔叔,他说了一句话:“在丹麦这个国家有什么东西好像腐化了。”(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这句话确实一语双关,“state”也指丹麦的状态。哈姆雷特一方面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看起来非常焦躁,这个焦躁有其真实的一面,因为他确实在面对这一局面;另一方面他还有装疯卖傻的一面,因为这样才能逃过别人的眼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长期的侍臣,经验老到的波洛纽斯说,这是哈姆雷特惯常的傻里傻气的性情(antic disposition),这其实是一种人的性格自制,antic可以表示胡乱搞的行为(胡搞、恶搞即是antics),也可以表示他的过往历史。所以他说:me think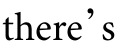 ?a method of madness。这是他很透彻的理解,波洛纽斯说:“我觉得在他的疯疯癫癫里面有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故意的成分在。”所以我想今天的演讲,我要牢牢紧扣住这种方法,在达达主义的元素中找到这种方法,各种各样的伪装、欺骗、犹豫都是艺术的方法,他们将惯常的审视给挡在了区域之外。哈姆雷特用他的装疯卖傻很容易把这些惯常的监控——周围的即时监控,很可能随时随地关闭他产生新知识过程的监控——给拒之门外,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疯疯癫癫的方法。
?a method of madness。这是他很透彻的理解,波洛纽斯说:“我觉得在他的疯疯癫癫里面有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故意的成分在。”所以我想今天的演讲,我要牢牢紧扣住这种方法,在达达主义的元素中找到这种方法,各种各样的伪装、欺骗、犹豫都是艺术的方法,他们将惯常的审视给挡在了区域之外。哈姆雷特用他的装疯卖傻很容易把这些惯常的监控——周围的即时监控,很可能随时随地关闭他产生新知识过程的监控——给拒之门外,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疯疯癫癫的方法。
所以,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中出现这么一种知识的场域?我要借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部著名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所谓Know-How是知所以然,而No-How是不知所以然(即“有章法的知识”和“无章法的知识”)。我们这个时代是一种创造狂热的时代,所有的行为都被重新包装为创造性。比如旅游,过去是乘飞机到了西班牙南部,享受着美利奴羊毛,每天早上吃英式早餐,然后过两个礼拜回来了,说我去过西班牙。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西班牙成为一种过时的东西。我们现在旅游要讲究一种符合伦理、符合美学的,还要是一种比较冒险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都说要去秘鲁、中国这些旅游地。英国电视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厨师詹姆士·奥利佛(Jame Oliver),他提出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具有创造力的厨师。当然这个跟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具有创造力的会计是另外一回事情。所谓创造性的会计是指对于账本的创造,用“创造性”这个词对账本动手脚,是不一样的。经过1980年代的变革,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说的“资本的创造性”时代,所以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在我们现在泛创造性的年代,每一个东西都会被改头换面地变为一个创造性的行为,我们不再是被动消费的消费者——我们被要求扮演这么一个角色——不再是古典资本主义时代消息灵通的知其所以然的消费者,我们现在是创造性的消费者。
伟大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这两位非常悲观的学者当时提到文化工业,提出了“否定辩证法”。(二战时期的“文化工业”演变为现在的“创意产业”。)跟文化工业这个字眼联系起来的这种负面性在今天的创意产业中已经全然消失了,好像它们本身是好的事情,艺术也是其中一部分,就是所谓创造性的活动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活动有价值的一部分。我们所谓创造性的概念,各个学科都曾经忙不迭地要取消要消灭的,尤其是艺术领域花了30年的时间取消所谓的“创作天才”、“真正的创造性”这些比较过时的字眼。现在这些又大张旗鼓地从后门进入我们的视野,所以现在提到新媒体、设计、视觉研究,其实需要对所谓创造性的概念有一种新的理解。曾几何时,艺术家是仅存的具有创造力的人,多愁善感,因而才会创造。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具有创造性的个人,这样的话又要跟艺术、实践和研究相联系起来,这种创造性又把它置于何地呢?它是不是会在整个泛创造力(pancreativity)中间被消解呢?还是说如果我们执著于艺术实践,便可以给世界带来积极的创造力?说得不客气一点,今天的这种狂热,泛创造力会不会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祸乱或者一种传染病呢?
下面我有一个需要以更严格意义上的术语来进行分析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早期笔记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谁是真正的生产者,是制作钢琴的匠人,还是钢琴的琴师?哪一个是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剥削的?”人们为此争论良久。这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客观设置剩余价值的标志的。这是马克思区分工人阶级和无产者的重要标签。而我们如何去评估这个现象,怎么样去寻找剥削的点呢?我们所说的剥削不是“老板剥削我以致我很不开心”的这种剥削,而是说这种剩余价值的抽取。当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听大家辩论的时候,有各种各样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刚开始是说可能制作钢琴的匠人是被剥削的,现在看来可能是弹钢琴的人是被剥削的。因为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在“创造性”这个概念下的工作模式下,工作、劳动、创造性都已经有了新的意义。所谓的“工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传统意义上的苦力,而是整个工作场地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印度以及非洲国家,这些地方是真正制造、转移苦力的地方。而西方主要是作为一名创造者,实现创造性劳务,他们的创造是一种概念化的东西。比如计算机里的耦合序列,他们将其卖给发展中国家,然后发展中国家再进行具体的生产和劳作。丹麦是世界上领先的生产概念型产品的国家,不再是以前的传统模式,它已经在一个新的生产领域中。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艺术的劳作已经跟过去用脏手实际造出什么东西的劳作有了巨大区别。在丹麦,我们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系科,就是创造、创新和发明,等等,这些系科等于说什么都不遗漏,所有东西都涵盖了。那么我们所谓的聚集的概念性创造或观念性创造的劳工,典型的形象就是在星巴克里面拿着手提电脑敲来敲去、手捧咖啡的工作者形象,但这样其实也是一个24小时的工作,因为你随时随地可能被公司或客户所联系,不再是在以前管制非常严密的装配线上的劳动,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分工,标记着当代政治的一种新的情况。如果我们现在要问“知识”是什么,艺术在新的社会分工的背景下,作为知识生产场域的时候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关于社会分工我们有另外一个研讨课去解决,现在工厂在西欧发达国家、美国已经开始消失了,他们已经大幅度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就是排外、种族主义、对于外包工作的愤怒和反抗以及对于新移民的排斥等,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仔细地去展开去论述。
陈界仁的优秀影片《加工厂》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纪录片。他在片中分析了劳工、创造性,以及管制严格的工厂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一种把你捆绑起来的逻辑。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制作,用哈姆雷特的方法进行了伪装,其真实性即不真实性,但又非常强有力地向现实世界敞开一种述说,它有自己的美学,有各种各样欺骗性的质素。一般来说,艺术家是非常关注工厂体制的。比方说查琳娜·宾吉(Zarina Bhimji),她曾经是歌德史密斯学院的老师,现在是独立艺术家。她对东非的工厂进行了非常精细的描述,围绕着这个工厂周围,以一种非常细致的方式展开,这些破破烂烂的工厂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震撼。荷兰艺术家温德林·凡·欧登伯格(Wendelien Van Oldenborgh)正在圣保罗双年展展出一件关于工厂的作品。所以我很关心我们现在的艺术学院是不是创造性生产的工厂,还是说,它只是所谓观念生产的一种扩张。如何将艺术学院与发展中国家中的苦力和劳动相联系,如何把艺术创造跟艺术知识相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访问过瑞典的几个工厂,例如乌德瓦拉(Uddevalla)的汽车厂,在这里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创造性?它是不是一种对全新的未知事物的生产,不同于所谓的创新(对已知东西的改造),比如说电视屏?我们还可以问的是:什么是发明?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尚未被人所认知,比如杜尚的《大玻璃》,在当时出现的情景中并没有人对它有多大兴趣,但今天却成了经典作品。这件作品在从纽约到费城的运送过程中,玻璃出现了裂缝,杜尚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偶然造成的产品,让里面的新娘焕发出一种生机。”所以我们要从实践和词汇方面来区分这四个名词,就是“发明”、“创新”、“创造力”和“发现”。如果我们不进行仔细的区分,很有可能会退回到寻常的宣传词藻,或意识形态,仿佛人人都可以创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艺术相对于新媒体等其他领域,具有自己的创造潜质。比如在印度的工厂,就存在这种创造力的管理,印度有一个电话服务中心,接线员都学习了澳大利亚或者美国的口音,这个口音的变化也反映了他们观念生产的一个方面。
建议我们学院的成员也去访问一番汽车制造厂,这个特定的研究其实会关系到分析和阐释劳工以及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印度的塔塔汽车厂是众所周知的制造廉价汽车的工厂,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创造性标记的广泛的标准。1970年代,瑞典所作的最大的一个努力就是不要让工人“异化”(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让劳工他们异化。以前我们说制作钢琴的人是受到最严重剥削的,最受到非人化的待遇的,现在这种工厂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的模式了,这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政治经济学话题,而是当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全球艺术产业的这种关系。比如我作为一名艺术家会经常变更居住地,这段时间会在这所学校当一名驻校艺术家等,我们其实身处在这个体系当中,是大工厂这个大体制中完全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在序列的流程上,把它变成一个平行流程,其实只是对整个资产阶级生产机制的小修小补,没有挑战其功能化的严密逻辑。20世纪,一位名叫泰勒的美国人为此提供了一种科学创造的依据,因为瑞典的这种企图在美国引起了深深的怀疑,他们委托麻省理工学院去研究一下所谓的“反异化”的实验。他们得出了一个报告,有一个非常负面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无异于把我们的工业倒退到手工业的年代,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这些工厂看一下,了解一下工人的早中晚班,他们是怎么样运作的。现在的这种制作基本上被推到了旧欧洲的边界,即欧洲扩展之前的东欧,甚至是边界之外亚非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这和艺术生产、跟创意生产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而且是不容忽视的。
先看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单词,我们刚才对不同种类创造力的区分,其实都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种Know-How(有章法的知识),即一种技术经验,这是相对于第二种No-How(无章法的知识)说的。我其实想让每一个单词都以字母K打头,但是英语的拼写规则不允许我这么做,我们如果从上往下看,nut的意思是一种天才,或者说一种具体的方法或某种特定的才能。ken是一个很古老的日耳曼词,可能是一种隐秘的不为人所知的知识,它现在的意思比较隐匿,但在苏格兰仍然被广泛地使用。knee是膝盖,是身体的部位,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要鞠躬、行屈膝礼的时候,都是要牵扯到膝盖这一块,意思就是说你会在知识面前屈服,你会屈膝。比如说在印度教中尊称的大师还有学徒或者弟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姿态。最后一个词cunning,狡猾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中也是以K拼写的。整个这个体系是想要区分了解做法的Know-How是一种外在的知识,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和佛教徒瓦雷拉提出了内在的观看方法,从内省的思维方式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的内容。七百多年来的佛教,为人类意识的实验产生了一大批的文献,他对这些文献非常尊重,并认为这与科学的文献一样重要。所谓的sutra,也就是心经,是一种内省的意识对于自然的报告,从人的身体内部的一种看法和经验,这跟我们所说的外在的、抽象的、数学的、给定的知识,一种偶合的知识是成对比的。而第二个No-How来自爱尔兰著名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诗歌,它显示了这样一个领域,我们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去学习的一个领域。艺术的生产,一方面是有普世性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拒绝普世应用到一切环境之中。第一个K打头的Know-How是一种可以应用的法则,并且随时随地有效,具有一贯性。以飞机为例,某种工程原则今天适用于它,明天依然适用。因为如果明天就失效的话,飞机便会坠毁。而No-How对于艺术来说,我们就说它不是可以预知的,不是具象化的知识经验。
当今艺术越来越观念化,成为语言的表征,书面、概念的形式已经成为艺术重要的维度的时候,我们也特别需要谨记。但我们要知道,语言不仅仅是言说、主张或经验,我们所知道的语言体系对于我们身体的经验来说是第二性的,而不是第一性的,我们可以借用乔伊斯一个非常好的词ur-oration,ur在印欧语系中的意思是“元”、“……之前”,所以这里指的是演说之前的,其实指的就是身体的演说,是巴比伦式的演说。回到荷兰的艺术史家安克·施密特,他说,“语言就是艺术所不是的那个东西”,“语言就是经验所不是的东西”,他的实际意思是语言和经验是不兼容的,反之亦然。语言和经验之间有一个断层,这个断裂带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领域。No-How的第二种表达没有了K,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艺术的方面,我们必须同语言进行搏斗,我们要了解它代表的一种资源,我们同时要对它设下的陷阱、它设下的牢笼有所了解,这个伟大的牢笼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一个说法——语言有解放的一面,也有囚笼的一面——所以我们在用文本表达的时候,还必须要记住在经验和指代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场域。
再补充一点,knee(膝盖),带有非常深刻的北欧语言的印记,往更古老的语言追溯的话,这个是历史语言学的领域。最近产生了一个转向,就是把学院叫作实验室,把设计师行业叫作实验室,把工作室也叫作实验室。它反映出的是何种变化?这其实是突出了实验室的首要性,它重新建构了实验室,思想在进行实验之前,首先要重建实验室,因为以前化学家是不和物理学家交谈的,矿物学家又不跟化学家交谈,所以他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创造一个所谓克里奥尔语——在法国殖民地,法语和当地的土著语言混合的语言——混搭的空间。我们所说的实验性不是科学的实验性,因为科学的实验性有很多严格的规则存在。而艺术学院的实验性是一个自由的空间,没有任何的管制,也没有任何的规则。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伊斯兰学校叫作Madrasah,我们很想了解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禁止了什么?什么是宗教的信条,或者什么是宗教的教条?教条式从上垂直地往下给被接受者是一种很被动的关系,它并没有区分的逻辑,只有一种相似的逻辑,比如说《古兰经》中的一个祷文,它不允许有任何阿拉伯语发音上的偏差,如果你能听到各个伊斯兰国家念这段祷文的发音,会发现这个只有声音的区别而不是发音的区别。我们现在需要研究一下在区分的情况下的原则,区分的逻辑,还要重复一个神圣的经文,这种知识的产域的重要性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位艺术家有所贡献,一位是刚刚提到的宾吉,她研究了一间很多学者、艺术家、文化人都参加的宗教学校马特雷莎。他们在其中不仅要学习《古兰经》,还要读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夫的作品,包括她研究乔伊斯的评论,其实二者很自然地融合到了知识生产的场域中。所以宾吉就研究了这所宗教学校,作为一个产生知识的场域,它是不是恐怖分子训练营,还是因为我们太盲目,没有办法认识到它的本质是什么?另外,巴基斯坦艺术家哈姆拉·阿巴斯(Hamra Abbas)也用微妙的、很复杂的观察来研究探索知识生产的空间。从宗教学校,到实验室,再到艺术学院,我们现在可以建立起一种联系。
我们刚才谈了知识生产,还有生产体系,以及其中的逻辑。我感觉大家在艺术院校里面的几年有无所事事的情况,这跟哈姆雷特的搞怪、装疯卖傻有点像,表面上看不出来,假装什么都不做,假装无所事事实际上跟我们解释知识生产一样,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这种怠惰也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般被要求在任何时间都要保持很旺盛的创作和生产,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于向所谓的效率原则投降了。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发明的术语“negative capability”,意思是相对于我们企图来成就什么的能力,我们还有一种负面的能力。这种能力用我们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满不在乎”。我再引用一个济慈的诗句“honey’d indolence”,就是“浸在蜜里面的怠惰”,一种非常甜美的怠惰。可以想像一下,用蜂蜜洗浴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方式,也可以想像一下很典型的懒洋洋的、什么都不做的一天,它是颇具重要性的。冰岛艺术家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的装置作品《睡眠高地》,里面描述了睡眠具有的特殊的意识状态,其实是一种没有意识存在的状态,它和创作的关系;在古印度传统中,要培育三种意识的状态,一种叫作行,一种叫作梦,一种叫作眠,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怠惰。在被迫要有百分之一百的生产的驱动力之下,我们不要忘记了怠惰这件事。
我用哲学家德勒兹的问题来结尾:谁是真正的生产者?是公共专家,是技师,还是白痴?这个我们要转向更早一辈的哲学家笛卡儿,由此上升到枯燥的尼古拉。有三种人,一种是公共专家,他是一个传播媒介,他熟悉怎样传播知识,建立沟通;往上是技师,安安静静地组织整个实施过程,是带来创新的人物;在另一边是一个傻瓜,白痴,虽然这个词有很多不好的联想,但是是在一个很友善的亲昵的环境下,我们常说:别傻了。idiot在爱尔兰口音中念作[5IdVIt],这里的[5IdVIt]指的是一种Know-How,如何去做的知识,还有另一种是No-How,两种对比的知识。再者,我们更需要一种装疯卖傻的能力,就是哈姆雷特的语境下,就是能够搞怪的这些人,我们知道具备这些能力的集大成者,就应该是geek这个词。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交往方面不是很好,不善于通过沟通融入大家的环境,而他却非常精于技术,他时常创新。其创新就像邱志杰老师的贫困设计,被称为geek,他可以乱穿衣服,不一定能融入社会。我们要把这个词从日常语境中夺回来,这种类型的人不是腰间的牛仔裤随便往下掉的人;但也不能退回到疯狂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我们需要一种正在成型的、胚胎型的人物,他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生产者,这也是我们需要进行展开阐述和探究的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